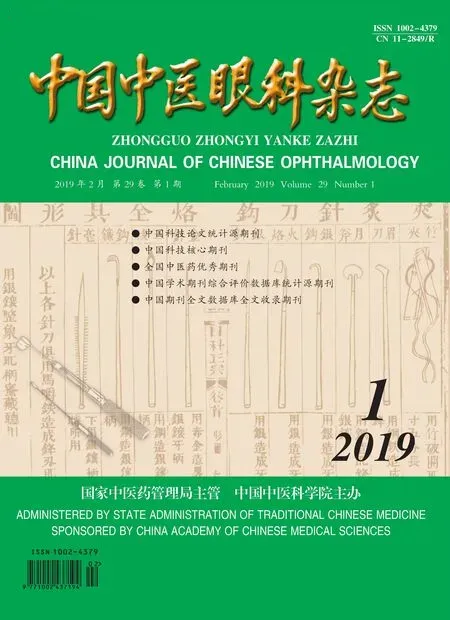重视阴火理论在眼科的应用
宋宙光
明·王纶《明医杂著》云:“外感宗仲景,内伤法东垣”[1]。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序》云:“夫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著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2]。李东垣在构建脾胃内伤学说时,独创性地提出了 “阴火”理论,并立法制方,首创了“甘温除大热”之大法及其代表方补中益气汤,被后世众多医家推崇并继承和发展。在眼科,自古就有“目病多火”的说法,但临床医师要区分“阳火”和“阴火”,才能不犯“虚虚实实”之戒。
1 阴火的慨念
“阴火”一词,语出东垣,而阴火理论,源于《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篇》曰:“帝曰:阴虚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者,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于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3]。李东垣将内伤病和外感病引起的发热,区别为生于阴者为阴火,生于阳者为阳火,这便于把因外感六淫之邪的发热和内伤饮食劳倦的发热鲜明的区别开来,“阴火”概念自然产生。
2 阴火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机制
《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云:“既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气皆绝于外,故经言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是六腑之元气病也。气伤脏乃病,脏病则形乃应,是五脏六腑真气皆不足也。惟阴火独旺,上乘阳分,故荣卫失守,诸病生焉。其中变化,皆由中气不足,乃能生发耳”[4]。由此可见,中气不足是阴火产生的根本原因。
《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曰:“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5]。由此可见,“脾胃之气下流”和阴火上冲,是阴火形成的主要机制。
阴火的特征是:内伤之火;下焦之火,元气之贼;因脾胃虚弱、元气不足。阴火的诊断要点有三:饮食不节,劳倦所伤或思虑过度,损伤脾胃元气为常见病因;病程较长,反复发作;“阴火上冲”的主症与脾胃气虚之兼症相兼互见。
3 阴火的治法和主方
对于阴火的治疗,李东垣首创性的提出了甘温除大热法。《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然则奈何?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云: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5]。主方补中益气汤:黄芪、炙甘草、人参、当归身、橘皮、升麻、柴胡、白术。李氏指出,芪、草、参、术除热,当归和血脉,橘皮益气行气,升麻、柴胡升气。“甘温除大热”之“大热”有特定的含义,即指气虚抑或阳虚所致之发热。笔者结合补中益气汤及其方后的加减法,可以得出李东垣内伤学说的治疗总则为:补中、升清、泻阴火,皆补肺气,滋荣血。
4 后世对阴火理论的发展
在后世医家中,郑钦安的“阴火”理论是对李东垣的阴火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医理真传·坎卦解》云:“真阳二字,一名相火,一名命门火,一名龙雷火,一名无根火,一名阴火,一名虚火。发而为病,一名元气不纳,一名元阳外越,一名真火沸腾,一名肾气不纳,一名气不归源,一名孤阳上浮,一名虚火上冲”[6]。郑氏所谓“阴火”即阴证所生之火,本质其实是真阳,是离位之相火,又称“假火”,常见的如咽痛、牙痛、舌疮、眩晕、头痛、耳鸣(俗话所谓“上火”),看似火热之象,但色、饮、便、舌、脉全是阴证表现,实为阴寒偏盛所致虚阳上浮、外越所引起的种种假热之象,极易被误认作实火或阴虚火旺,治之当以温阳潜阳为根本大法,切忌苦寒直折,也忌滋阴降火。
李东垣的阴火理论与郑钦安在阴火理论在侧重点不同,李氏专论后天之本—脾,郑氏专论先天之本—肾,但对于阴火根于下焦,出于中焦,系于上焦,在本质上又不谋而合。当代成都火神派代表卢崇汉在《扶阳讲记》中指出:“中阳不振导致的发热,用补中益气法就能解决;这种情况不仅要补脾,还要固肾,所以如果在补中益气汤中加上附子,效果就更好,这样收功就更快,治疗就更彻底”[7]。卢氏认为郑钦安之“阴火”论与李东恒之“阴火”论本质皆为肾中之真阳,为坎中离位之“阴火”。
李氏和郑氏的阴火理论均可以黄元御的 “一气周流,土疏四维”理论来解释。黄元御在《四圣心源》论道:“升降之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中气”“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平人下温而上清者,以中气之善运也”“胃土不降,金水失收藏之政,君相二火泄露而升炎,心液消耗,则上热而病阳亢”“至于上热者,此相火之逆也,而方其上热必有下寒,以水火分离而不交也,见心家之热,当顾及肾家之寒也”[8]。
综上,笔者可以将阴火分为狭义阴火和广义阴火,狭义阴火及李东垣之主要与中气不足相关的阴火,而广义之阴火为一切离位之相火。
5 鉴别
5.1 阴火与阴虚火旺的鉴别
“阴火”易与“阴虚火旺”相混淆,阴虚火旺为阴液亏虚,虚火亢旺,阴虚则阳亢并生热化为虚火。阴虚火旺和实火亢盛都可以包含于“阳火”之中,而“阴火”根本在于气虚阳虚。
郑钦安认为:“阳气过衰,阴气过盛,势必上干,而阴中一线之元阳,势必随阴气而上行,便有牙疼、腮肿、耳肿、喉痛之症,粗工不识,鲜不以为阴虚火旺也”[9]。从伤寒六经辨证大概区分的话,那么阴虚火旺可归于少阴火化证,实火亢盛可归于阳明经证或腑证,而阴火则可归于太阴证,或少阴寒化证或厥阴上热下寒证范畴。
5.2 阴火和阳火的鉴别
“阴火”是相对于“阳火”而存在的,如无阳火,则阴火则无从谈起。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阴火和阳火做了鉴别,谓:“诸阳火遇草而炳,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9]。并指出治阴火需用“补土伏火”之法。《慎柔五书》中也说:“凡内伤,清气下陷,阴火在上者,若用寒药则阳愈陷,火愈炽。火寻窍出,虚者受之,或目痛,或耳聋,或齿痛,从其虚而攻之也”[10]。
因此,临床上治火时必须分清实火、虚火、阳火、阴火的不同。实火、阳火当泻,泻火法以苦寒泻热,易于掌握,而虚火、阴火却不仅不能通过直接的泻火法取得疗效,反而会使火邪更旺。程杏轩在《医述》引用汪寅谷多年临床体悟:“阳火一清便退,阴火愈清愈起”“治火须分有余、不足。有余之火,其势猖狂,周流不滞,只以济火之药正治之,其火自退,故其治多易;不足之火,其势缓涩,凝滞一处,或滞于此,或滞于彼,既不能升,又不能降,须用补剂,使其元气周流,则火因之自散矣。故其治多难。世俗不知有余、不足,一遇火证,概用寒凉正治,火愈拒逆而不能退。因而致死者多矣!”[11]
6 阴火理论在眼科的应用
“火性炎上”,虽然临床常见头面五官诸疾如红肿热痛和发热、发斑、肿块、充血、出血等症,但是临床工作者不要轻易便断为实热阳火或阴虚火旺,还要根据阴阳辨诀加以判分。如有阴象为凭,这是阴火,若无阴象可验,便是实火。
古有 “目无寒证”“目为火户”“目病属火”之弊论。刘河间有“目病专火”的理论,张景岳有“凡目之病,非火有余,则阴不足”的说法,《证治准绳》云:“岂知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凡病目者十之六七皆有此患,病源在心肝脾三经,总而言之不过一火”[12]。纵观古今中医眼科医籍、医案、医方中,寒凉滋腻药占十之八九,而温热宣通药不及十之一二。当今眼科医生宁可“雪上加霜”,不敢“火上浇油”,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所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有死焉;水懦弱,民狎之而玩之,则多死焉”[13]。
傅仁宇《审视瑶函·用药寒热论》曰:“今之庸者,但见目病,不识症之虚实寒热,辨别气血,惟用寒凉治之,殊不知寒药伤胃损血,是标未退而本先伤”[14]。张三锡《医学六要》云:“目病多用凉药,世俗之见也”“苦寒伤胃,四物泥膈,中气受亏,饮食少而运化迟,气血不生,精华俱耗而目病转甚矣”[15]。黄元御《四圣心源·七窍解》云:“后世庸工,无知妄作,补阴泻阳,避明趋暗,其轻者遂为盲瞽之子,其重者竟成夭枉之民”“后人不解经义,眼科书数千百部,悉以滋阴凉血,泻火伐阳,败其神明”[8]。《冯氏锦囊·方脉目病合参篇》云:“不知外治忌寒凉,而妄将冷水冷药挹洗,尝致昏瞎者有之”[16]。
笔者在临床中发现,表现为“阴火”的眼科疾病并不少见,无论是外障还是内障,均可见标“火”而本虚,上热下寒的病机。《景岳全书》曰:“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17]。此确是阅历有得之谈,十分有助于指导眼科临床实践。
临床上见眼病之“火”,无论局部用药还是全身用药,既要知不可一味恣用寒凉以清火,又需要分清阳火、阴火,既要有“甘温除大热”或者“升阳散火”之思维,也要有温阳潜阳或者引火下行的思维,方不至于“以生人之道,为杀人之具”。
为医者,应摒弃温补派,火神派,温病派,寒凉派等派系理念之争,正如郑钦安所云:“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18]。当代中医眼科名家陈达夫在《中医眼科六经法要》中道:“治疗眼科疾病,应该不离四诊,不越六经,用药不可偏寒、偏热、偏补、偏泻,认症不得拘泥前代有无症名,必须辨明病理,随证施治即可”[19]。
7 阴火理论病案举隅
[病案1]益气聪明汤案
张某,女,42岁,工人。因“右眼异物感,视力下降1个月”就诊。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眼异物感,发红,视力渐渐下降,伴少许脓性分泌物。于当地医院诊为“右眼角膜炎”,予抗生素及营养眼表的滴眼液治疗,症状未得到明显控制,遂来我科就诊。
专科检查:右眼视力0.1,左眼视力1.0。双眼眼压Tn。右眼轻度角、结充血,角膜中央及其上方浅层溃疡,大小约3 mm×4 mm,色泽淡灰,边界较清,表面无脓性分泌物,有浅层新生血管从上方侵入溃疡表面,前房未见明显异常。左眼未见明显异常。中医四诊:身材瘦弱矮小,面无血色,言语低微,脉三部微迟,舌淡白瘦,苔薄白。平素乏力畏寒,纳差,腹胀,便秘。不喜饮水,饮则畏凉水。西医诊断为“右眼角膜溃疡”;中医诊断为“右眼花翳白陷(中气不足)”。治疗则用停抗生素眼水,仅用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眼用凝胶,点右眼,每日3次。方用益气聪明汤加减:黄芪 30 g、党参30 g、炙甘草 10 g、葛根 30 g、升麻 10 g、蔓荆子 15 g、白芍 10 g、黄柏 10 g、生白术30 g、乌贼骨15 g,6剂,水煎服。1周后复诊,右眼视力0.6,角、结膜充血消失,角膜溃疡面平复,上皮修复完整,面积缩小,色泽淡灰。患者自述精神状况明显改善,眼部异物感消失。脉象同前,因角膜溃疡修复良好,角膜上皮完全修复,故在上方基础上减去具有收涩作用的乌贼骨,10剂。15 d后再诊,右眼症状完全消失,视力1.0,角膜表面仅残余小面积云翳,新生血管大部分消退。嘱服补中益气丸15 d以善后。
按:益气聪明汤出自《东垣试效方》,由补中益气汤变化而来,《医方集解》云:“五脏皆禀气于脾胃,以达于九窍;烦劳伤中,使冲和之气不能上升,故目昏而耳聋也。李东垣曰:医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理也”[20]。
当代中医前辈何绍奇先生在 《读书临证与析疑》[21]中提到自己曾治一女患,左眼珠上有一芝麻大小之凹陷,乃角膜溃疡,然而素无经验,勉强开出一清热解毒方,参以菊花、密蒙花之类的眼科套药,服用几剂,毫无寸效。之后患者另请眼科王汝顺医生诊治,开以补中益气汤10剂,患者服药不到10剂时,溃疡已经愈合。何老暗想,溃疡乃炎症所致,安可用补?故俯首心折求教于王,王说:“溃疡云云,我所不知,我但知‘陷者升之’四字而已”。
[病案2]潜阳封髓丹案
梁某,女,55岁,退休工人。双眼干涩异常5年。患者自述年轻时生第2胎之后,全身状况一直不佳。5年以来,双眼干涩异常难忍,晚上明显加重,伴异物感,结膜轻度充血,畏光难以睁眼,不能久视,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曾多次辗转于北京、上海、太原等地就诊,局部点药,口服中、西药物,针灸、理疗、按摩、眼贴等治疗,均无明显改善。曾有医生建议其行泪小点栓塞手术,患者未予采纳。平素畏寒,无汗,轻度乏力,脱发严重,头重头闷如裹,纳可,口干唇干,但不喜饮水,不能吃凉食及水果,半夜因口干甚,必须起夜饮少许水才能再次入睡,眠差易醒,颈部不适,右侧上肢及下肢发麻,双膝关节以下寒至骨髓,穿厚裤袜亦不能缓解。双脉沉细缓,上鱼际,尺微欲绝,舌暗,苔薄而糙。西医诊断为“干眼症”;中医诊断为“白涩症(上热下寒)”。方选潜阳封髓丹加减:制附子 15 g、砂仁 10 g、生龟甲 10 g、炙甘草 10 g、黄柏10 g、肉桂粉(冲服)3 g,7剂,水煎服。 患者诉从前也有中医大夫嘱服热性汤药,可一旦服用热性汤药即出现严重口干、口苦,结膜充血明显,故认为“虚不受补”,特别叮嘱笔者不能开热药。经笔者认真解释,此方作用正是引火下行,患者才同意服药。1周后复诊,症状无明显变化,也无“上火”症状出现。四诊同前,考虑为病重药轻,故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大诸药用量继续温阳潜阳,又考虑本病为上热下寒之厥阴病,故加用厥阴头痛的引经药吴茱萸,全方如下:制附子30 g、砂仁 15 g、生龟甲 15 g、炙甘草15 g、黄柏 10 g、肉桂粉(冲服)3 g、吴茱萸 5 g,10 剂,水煎服。患者头重头闷如裹,为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之故,所以取百会穴刺络放血数毫升。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之“其高者,因而越之”[3],于百会穴刺络放血,泻其浊阴,有利于清阳重布。再诊,患者自述放血后,顿时感觉头闷头重症状大为缓解,眼睛明显清亮,服药后眼部干涩症状及全身症状均有不同程度减轻。之后,患者多次复诊服药,均以潜阳封髓丹加减治疗2个月,眼部症状改善,已经不影响日常生活,全身状况好转,尤其膝关节以下畏寒明显缓解,睡觉亦无需穿裤袜。
按:此为温潜法[22]。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引火归源,导龙入海,不可滥与清滋之药。在临床中,眼科医师容易辨别出“上热下寒证”,但却对如何清上温下或引火下行不知所措,不敢处以“甘温”之药,实际上,此为对温阳药与清热药和潜镇药的结合应用不够熟练。《医理真传》云:“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矣”[5]。笔者认为,“虚不受补”的原因,实为医者对表、里、虚、实、寒、热之错杂的病情认识不够深刻,治疗时毫无头绪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