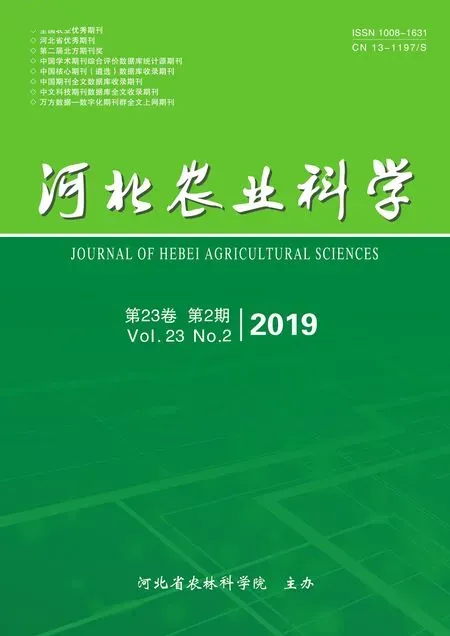精准扶贫实践中政府政策逻辑与农民乡土逻辑的偏差分析
——以少数民族地区凌云县为例
周万献,邱丽花,肖阳萍
(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县全部脱帽的总体目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要坚持精准帮扶与区域性开发有机结合,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对于该类地区的精准扶贫状况,学术界进行了诸多探索。汪三贵等[1]深入调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发现政府在精准识别时出现识别偏差,所支助的对象中有近一半是非贫困户,而有一半的真正贫困户未得到资助;杜春林等[2]从项目制运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在扶贫项目落实过程中,政府的制度运行逻辑与基层农民的乡土逻辑有偏差;李博等[3]指出精准扶贫在落实过程中出现精英俘获现象,主要表现为村庄的精英对村庄内的扶贫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的占有或合伙占有,造成贫困资源分配扭曲;朱天义等[4]认为导致出现精英俘获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政府在高压力的扶贫体制下,要想更快地实现地区脱贫,往往更有可能把扶贫资源向村庄的精英倾斜;任超等[5]认为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目的正是针对在先前扶贫经验中出现扶贫资源的错位而开出的新药方,而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由于贫困户的识别和锁定没有客观、准确的标准,仍然存在大量的瞄准偏差。
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在实施扶贫政策过程中出现瞄准偏差,造成精英俘获现象,对于从政府政策逻辑和基层农民乡土逻辑两方面分析扶贫资源的实施困境缺乏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集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事实上,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集中连片地区的脱贫重视力度加大,分配到这些地区的扶贫资源也大量增加,且这类地区在落实扶贫政策时更加容易出现有别于其他贫困地区的困境。因此,作者以少数民族集中连片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凌云县为研究对象,从政府和农民2个角度去探讨凌云县精准扶贫资源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并阐明该类地区扶贫资源落实时与扶贫初衷相背离的原因,试图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精准扶贫提供实质性的价值参考。
2 凌云县扶贫工作成效
2.1 凌云县概况
凌云县位于广西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南麓,隶属于壮乡红城百色市,县城所在地泗城镇距百色市83km,距南宁市257 km;县域总面积2 053 km2,辖4镇4乡110个村(居)委会,聚居着壮、汉、瑶3个主体民族,总人口22万人,2018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 923元。该县1984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1992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享受民族自治县待遇,2002年被划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被列为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14个重点片区之一的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域项目县。其中,泗城镇、下甲镇、伶站乡、朝里乡、沙里乡、逻楼镇、加尤镇、玉洪乡等8个镇53个村属于“十三五”期间的贫困村,全县“十三五”期间建立档卡的贫困户数为11 325户,贫困人口为48 078人[6]。
2.2 工作成效
近年来在基础建设方面,该县建成安置新村11个,改造农村危房9 037户,新建家庭水柜2 026座(18.2万m3),解决了5.91万人的饮水问题,新建、硬化通村水泥路161条(592.5 km),行政村公路通达率100%。在产业发展方面,大力实施“十百千”产业化扶贫示范工程,不断做大、做强“221”(茶叶、油茶、桑叶、烟叶、林上林下经济)特色产业,共实现创建有机茶面积0.1 hm2,新种桑园0.23 hm2、油茶0.13 hm2、中草药0.15 hm2。在招商引资方面,共培育产业发展自治区级龙头企业1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共举办有机茶创建、种桑养蚕、中草药种植等劳动技能培训465期7.2万人次,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3.8万人(次),劳务收入27.3亿元,其中882人成为产业致富带头人[6]。
3 扶贫资源分配中政府逻辑与农民乡土逻辑偏差分析
3.1 政策逻辑分析
按照政府的关于扶贫攻坚的政策逻辑,宏观考虑整个区域的扶贫重点,惯性选择扶贫成效快、效果好的村庄作为重点扶贫对象。凌云县精准扶贫项目会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后进行分配决策。对几年的项目分配数据进行汇总发现,每年的扶贫项目会向发展人口多、发展潜力大的村镇倾斜。泗城镇位于凌云县城的周边,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总体经济状况好于较其他村镇,大量的扶贫项目和扶贫资源在泗城镇集中;玉洪乡位于边远山区,自然环境也较为恶劣,贫困发生率居全县首位,贫困资源项目极少[7]。在脱贫任务压力和政绩要求下,政府选择在条件较好的乡镇投入更多的扶贫资源,在已有的条件下,扶贫项目更容易推进,扶贫成效更快,能确保在上级要求的期限内完成脱贫任务。政府政绩与压力下的扶贫资源分配逻辑容易导致贫困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造成更大的不公平[8]。
3.2 基层农户乡土逻辑分析
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真正主体,提高贫困户对扶贫项目的参与度是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在走访中发现,玉洪乡的一个种茶项目按照规定种植规模达到1.3 hm2以上才能得到资助,对于普通贫困户而言资金有限,初始规模无法达到标准,就无法获得该项目的资助,该项目的支持资金就被村里的能人获得。再者,政府依靠一整套扶贫评价体系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并不都应该获得资助,在扶贫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于“小农意识”作怪,大多数农户认为自己最应该得到项目资助,而不是村中“能人”和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人[9]。
综上所述,从政府的视角看,一方面,扶贫资源的分配应该是遵循均衡性原则,从扶贫项目的分配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确定,都要保证每一个村都能得到相应的名额,以保证公平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迫于扶贫任务的压力以及处于政绩的考量,在对资源进行分配时,会有意识的把扶贫资源向村里的能人倾斜,保证该项扶贫任务能够如期完成,以接受上级政府的考核和验收[10]。同时,在国家一套严格的贫困户筛选体系下,只要是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就应该得到资助,不再考虑其他因素。而从基层农民的视角看,农户最看重的是自己的收入、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村民们认为政府不该为了政绩和任务而把扶贫资源分配给村里的“能人”与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之人[11]。可见,在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政府的政策逻辑与村民的乡土逻辑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扶贫立法力度
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分配与实施的公平正义,减少扶贫资源在分配时不合理情况发生,确保每一个贫困村和贫困户真正受益[12]。完善扶贫主体激励机制,有效处理政绩追求与扶贫长远目标的关系,对于因违反规定变相对扶贫项目实施能人优先的扶贫人员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
4.2 建立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
(1)强化对精准扶贫资源在各实施阶段的流动监控与审计,确保扶贫资源实施过程透明化,减少权力寻租问题的发生。(2)充分发挥农村微组织对扶贫资源的监督作用,广泛动员村民代表、村小组长与党员等积极参与扶贫项目监督工作,杜绝人情项目与弄虚作假等情况[13]。(3)完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积极引导村级组织合理、合法地分配公共利益,打破不公正的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重塑村级组织纯洁性[14]。
4.3 提高贫困户的参与度
加强宣传,着力提升贫困农民精准扶贫项目参与能力,贫困农户是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的重要主体[15]。精准扶贫项目瞄准的偏离很大程度上与扶贫信息不对称和贫困农户项目参与能力较弱有关[16]。要进一步加强对于精准扶贫项目的宣传工作,通过村民大会集中宣讲、包户干部与小组长入户宣传以及村委会及时全面公示等多种途径提升贫困农民对于精准扶贫项目的认知,不断提升其对于精准扶贫项目参与的能力[17]。
4.4 创新扶贫绩效考核方式
加快建立精准扶贫项目全过程绩效考核机制[18]。创新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考核机制,突破对于扶贫项目的单一结果绩效考核,逐步探究覆盖精准扶贫项目瞄准绩效、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等全过程的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对全过程绩效的监控与考核,精准找出影响项目实施绩效的各环节所存在的问题,继而进行精准追溯与整改,有效保证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19]。
4.5 定量识别与定性识别相结合
除了采取政府客观的评价体系识别外,还要充分考量各个贫困村的政治、文化、经济以及贫困户人品等各方面因素[20]。把村民的态度、偏好和主观感受等因素考虑在内,确保识别出来的贫困户更加精准,从而减少村民对识别体系的不满,有效助力脱贫攻坚的开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