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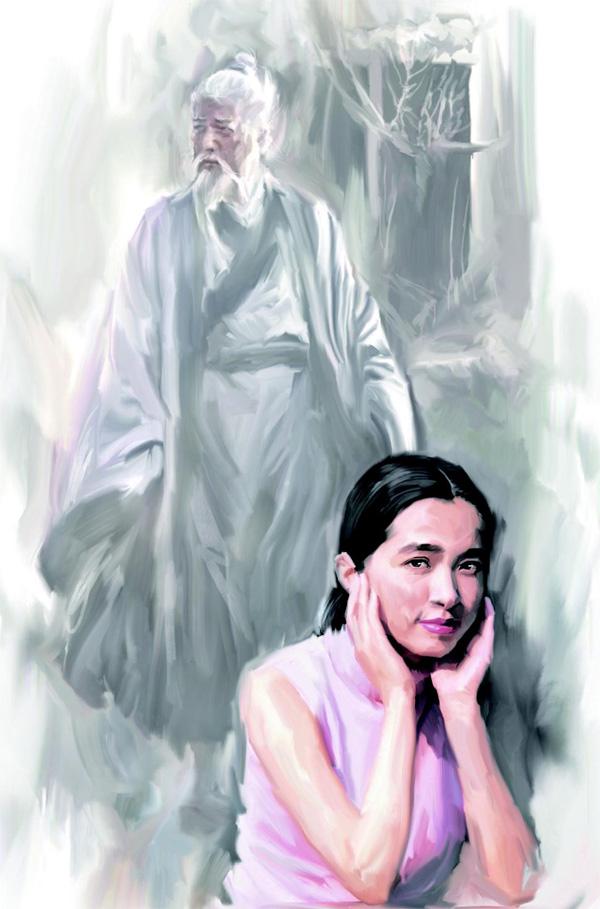
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听父亲在日常生活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二十多年。
父女二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李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
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地喜欢杜甫呢?
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地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地赞叹:“写得是好!”
他读书读到击节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诗;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理俱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诗;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都会叹一声:“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诗;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及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开头,那么说明他这次激动了,也说明这次通话往往会持续一个小时以上。
父亲喜欢马,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洗万古凡马空,是好。”——我知道“一洗万古凡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
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作品,他又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杜甫《房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感情真挚,倒是令我心服口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我曾当着爸爸的面这样说过一次,马上被他“逐出”书房),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但是写得工整精丽,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之词,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
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一舞剑器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我说:“嗯,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地比画了几个“之”,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然后,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
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得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里偷偷翻书看,找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攔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
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居然大声说:“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哦!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时,我才真正懂得“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的含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
父亲如此喜欢杜诗,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给他。
不过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
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轻捷。那是到了三十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这不是杜甫,简直就是我自己,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样的灯烛照着!可都不年轻喽,彼此都白了头发。再叙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没想到二十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变化有多大啊,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我从哪儿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
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读了却有如冰炭置肠,倒海翻江。
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心酸、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这一天。
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您说得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地点头:您说得对,老杜“着实好”!
那一瞬间,一定要用語言表达,大概只能是“心会”二字。
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出版时,已经是2011年,那时父亲离开快五年了。我赶紧去翻保存剪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
岁月匆匆,父亲离开已经十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在岁月的逝波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
(识 途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一书,刘程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