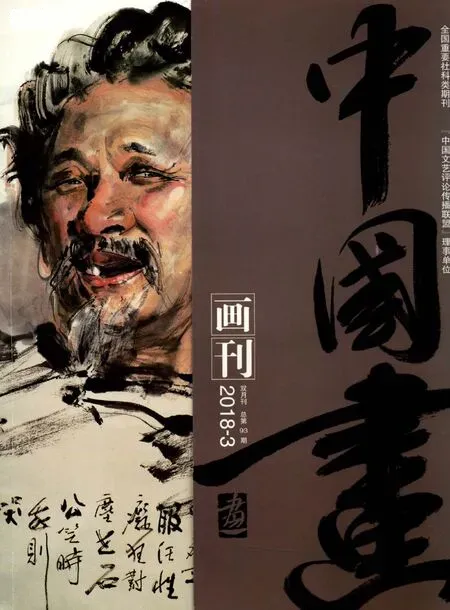如果学生都像老师是个问题,那主要是老师的问题
艺术两个字,艺在其先,术列于后。尽管大部分学习的功夫都花在“术”上,精义还是继承魂魄,这才导致学生像老师。然而这不正是教育的本义?因此我们都想找一个好老师,当年毛泽东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才着急,大呼“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乃至不惜“停课闹革命”,于是才有“老三届”与其后的69、70届,没读什么书也毕业了,因为体验过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而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几年后重开大学,进校的“工农兵学员”(无须考试,而由推荐入学),也是“上管改”去的。

峡江行舟图(局部) 陆俨少

夏山雨景 孙永(陆俨少学生)
如果还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恐怕不会有今天的问题,因为学生对老师始终抱有警惕,自己亦是学校管理者,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这样的局面足以叫人产生高度自信。记得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有个做法,请全民参与修改党章,连我这样的中学生,也响应号召写过一稿“党章”,当然纯粹是凑热闹,谁会听你的意见呢?也不可能有什么成熟与值得听取的想法。
但这样的局面不可持续,因为学生既然不听老师话,也就会质疑其他老一辈包括领导的话,当时马克思的名句“怀疑一切”是许多学生的座右铭,从学校起始的“文化大革命”就因为小将不完全受当局控制,乃由工宣队(全名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同)与军宣队进驻学校(在农村则有农宣队),当然并非仅仅宣传,而是掌控领导。一些学校的红卫兵试图抵制,如清华,还发生了武装冲突。随后便有上山下乡运动,尤其中学红卫兵,几乎统统去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是说还得认师,不过换了一批老师。
扯得有点远,想说的是,学生像老师乃常规教育的目的,不管信奉什么理论,即使那些革命口号喊得最响的,结果还是得回来。
但说到艺术教育,有它特殊性,那就是“艺”本身便意味着某种创造和突破。
哪个称得上艺术家的,没有一点自己的特色,或在所从事领域留下一点个人印记呢?这种特色与印记又往往是对自己不断否定与超越的结果。
你看毕加索,不同时期的作品变化有多大?黄宾虹前后期绘画,风格迥异,人称白宾虹与黑宾虹,八十岁以后居然还搞变法。
黄这样的艺术家才称得上真正的好老师,尽管到那个年纪他不教书了,但有这么一种追求与胆魄,才得“艺”之真髓。他带学生,也必然会把此种精神传递给他们。这样,如果学生真想求艺,就会不仅仅满足于“术”。顺其发展与演化的结果,则变得不那么像他(她)的老师。
然而秉持这样的教育观念与实践并不容易,要求老师都是大艺术家也应当归入妄想吧?所以通常我们看到,还是学生像老师(不管在形式还是理念上),学得像就是好学生了。能遇上大艺术家又学到他内在的精神,也只可能是极少数学生。
说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谷文达是陆俨少的学生。陆在浙美研究生班执教时已70岁,但艺术上仍求新求变,很欣赏谷的灵气,尽管对其离经叛道的做法也有自己的看法,但通常保持沉默,认为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应当支持。用谷的说法,“对于我感兴趣的前卫艺术,恩师给了我最大的包容”。
所谓谷“感兴趣的前卫艺术”是些什么玩意儿呢?他搞的“先锋派水墨画”叫“宇宙流”,自称是“人类灵性的图示”。对传统山水画,则认为北宋时期最有价值,“是阳刚的、祟高的”,此后兴起的文人画难免“阴柔、孱弱”,这与当年梁启超的说法几乎一样,与其时主流认识却大相径庭。谷采用水墨的大面积泼、冲、洗等技法同时还辅助以喷枪的运用,声称藉此便能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特质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相融合。有个时期他努力营造画面的破坏性外观,试图同时超越东西方传统。

山魂(局部) 卓鹤君(陆俨少学生)

山水(局部) 王健尔(陆俨少学生)
几乎与此并行,他开始从事“文字艺术”,即把所谓“原型”的汉字搞乱,在巨幅宣纸上颠倒、翻转、误写、重构,创作了“错别字系列”,在他看来,汉字承载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含义,所以颠覆传统从这里下手最合适。另一方面,谷把“错别字”当抽象画来创作,“我使用文字的分解、文字的综合等等,因为在我看来文字是一种新具象,抽象画一旦和文字结合起来。从形式上看是抽象的,但文字是带有内容的。这种结合使画面不是通过自然界的形象,而是通过文字传达出来,改变了原来的传达方式,也使这幅抽象画的内容更加确定了。”
这么一些做法,一般的老先生如何可能认同与支持?
陆也不见得认同,却还是包容。在招收下一届研究生面试时,曾笑着问考生:“你们对我的学生谷文达看法如何?”
毕业后,谷居然留校了。“当时搞前卫艺术的人很难留校,我能留下,得益于陆先生的支持和包容。”
谷文达后来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如果学校里都是陆俨少这样的老师,如何可能教出只像自己的学生?所以说,如果学生像老师是个问题,那主要是老师的问题。
另一个故事中的当事人就没这样幸运了。
林琳是1977年考入浙美的。那一届学生因为积攒了十年,普遍厉害。
进校不久,他便不满足仅仅做技法上的练习,恰在其时,欧美现当代艺术的一些状况经由图片展览与书籍进口的方式开始流入国内与院内,在年轻人中引起震荡。而林得风气之先,开始尝试各种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包括立体派和野兽派,这几乎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其时并非一届的同学、后来声名卓著的王广义来说:“作为一个特定的环节,林琳是非常重要的。还不仅是技术与学术的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毫不夸张地说,林琳在当时几乎是影响了我们这一届。”
但他出格的做法却让老师非常挠头。
据同窗查立回忆,班主任徐永祥就常与林琳为了几位艺术家抬杠:“徐先生推祟门采尔,林琳偏说门采尔这样的画家在上海有一大堆;徐先生钟爱尼古拉·费钦,林琳偏说尼古拉·费钦画得不准、画得很油,徐先生气得七孔出血。”这最后一句当然是夸张的说法。
徐之后,王流秋接手这个班。
对王而言,林也是个棘手的学生,他画了一幅惹起很大争议的习作:《席方平》,下笔避开传统苏俄绘画中列宾、苏里柯夫的褐色而展现了血淋淋的红色。很难简单地推断林这样做的含义仅仅是在作技法上的探求,还是另有用意,试图表现他理解的民族文化中传统的苦难。

风高(局部) 谷文达(陆俨少学生)

卧游武陵源(局部) 周凯(陆俨少学生)
临近毕业那年大家都按照学院安排下乡去体验生活,只有林坚持不去。他私下对88级陶瓷系的朱叶青说:“我现在就在生活。如果按照毛主席阶级划分论,我就算是小资产阶级。如果我这小资产阶级去农村呆上一个月、两个月,然后画一些反映工农兵的作品,那我是画不出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怎么会在一两个月内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呢?所以我只能画自己的生活,假如我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我仅仅就画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画出这样生活才有可能是真实的。”
他呆在学校搞毕业创作,内容是一个坐在钢琴前的女人,表情呆滞,形象有些变形,脖子很粗,略带马蒂斯、毕加索的画风,色调灰暗,题目却叫《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这么一种不服从与挑战的姿态无疑惹恼了王老师,他不准林琳在教室里继续画下去。于是林就跑到教室外的楼道里画,楼道太暗,再搬到宿舍里画,宿舍太小,难免不小心把颜料弄到同学的衣服上去,最后又到顶楼的平台上继续画。
对此林曾向同学表示:“我和王老师的艺术观点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是他不该表现得那么没有修养。”
临毕业前27天,学院贴出告示,开除林琳与另一个学生查立。当然这与其时“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有密切关系。
班里同学得知后组织签名请愿,要求学校收回决定,林自己也去找过院长莫朴,无果。最后只能卷起画作与铺盖回家。到上海后,街道居委会不予安排工作,还和派出所联系,去他家没收了一些课堂人体作业,说是黄色画。
后来在同学汪彤帮助下,林去了美国。在纽约街头替人画肖像,挣了钱后,最初是付学费,供自己读书;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硕士毕业后,则把最大一部分收入都用来买材料搞创作。住在黑人区,还给自己起了个黑人名字,叫比利·哈楞。然而1991年8月的一天,正是一个黑人青年,因为一点细小的起因,把他一枪撩倒。
林最后的作品是一批轮胎画。尺幅巨大,往往高至3米,宽达4米,试图实现他创造“平面上的幻象”的绘画理想。当时美国正值对现代主义的反动,绘画中再次引入大量社会题材、文化批判、异文化元素等等,而林琳没有乘势在“中国元素国际化”上做文章,以比较容易讨巧的方式来获得欧美艺术主流的“承认”,成为多元主义运动里东方的代表。他选择坚持和继续现代主义绘画与艺术的纯粹性。
没人知道,如果不是那次开除,如果没有这致命一枪,林琳往后在艺术上会取得什么样的发展与成就。
这些年,改名后的中国美术学院包容性强多了,但既然还是被认为“绝大多数学生画得都像老师”,即便在一些新领域,譬如装置,不用画笔了,我们仍可以通过作品大概猜出其指导老师,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在培养原创力方面,其实普遍的进步并没有乃至远没有从外面看起来那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