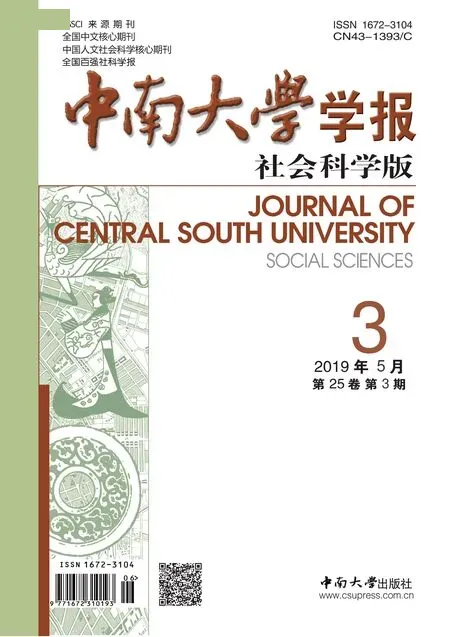丝绸之路开辟前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跨区域贸易探析
刘昌玉
丝绸之路开辟前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跨区域贸易探析
刘昌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周围地区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亚洲西端的跨区域贸易以两河流域地区为中心。利用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系统梳理与探析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跨区域贸易,包括东线的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阿富汗贸易、南线的波斯湾−印度洋贸易、北线的古亚述跨境贸易和西线的东地中海贸易。人类文明早期一系列跨区域贸易路线的开辟,以及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出现的服务于军事的多功能道路体系,对后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两河流域;商路;跨区域贸易;楔形文字文献
“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亚欧大陆的主要商业贸易路线,其中的亚洲西端部分在更早期就存在以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主要流经今伊拉克境内)为中心的若干零散商路和商路网。它们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射,到亚述帝国、波斯帝国时期分别形成多功能的亚述御道和波斯御道,贸易商路成为国家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分布零散的商路成为后来的丝绸之路的雏形,对丝绸之路的开辟具有深远 影响。
有关汉代丝绸之路以前亚洲西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跨区域贸易情况,国外学者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并且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另一个是20世纪末。当时学者们的研究仅局限于两河流域的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如马克以考古发现为证据,集中探讨了史前时期两河流域与埃及的贸易联系[1];李曼斯专注于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对外贸易研究[2];赫尔曼以青金石为贸易对象,专题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与阿富汗之间的跨区域贸易[3];维恩霍夫基于古亚述档案文献,研究了古亚述时期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殖民地[4];戴克森把研究视角转到古亚述时期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之间的贸易活动[5];克劳福德专门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的海上国际贸易[6];等等。此外,1976年的第23届国际 亚述学大会,以古代西亚的贸易作为主题,学者们提交了许多相关论文[7]。1995年,萨松所编的《古代近东文明》丛书第三卷第六章“经济与贸易”中,收录了9篇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商业与贸易方面的论 文[8](1373-1497)。1999年,戴克森主编的论文集《古代两河流域的贸易与金融》收录9篇关于两河流域贸易与金融的论文,涉及私人经济、资本投资、信贷、货币和商业模式等领域[9]。由于古代语言的障碍及考古材料的缺乏,国内学者对古代亚洲西端的贸易及商路研究非常薄弱,相关的论文匮乏,只对两河流域与巴林的海上贸易进行过初步研究[10]。
国内外学者关于古代两河流域跨区域贸易的研究成果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前提,但这些成果要么是单纯的贸易点或贸易线路研究,没有综合研究多条贸易路线,也没有系统研究贸易网络;要么是研究某个时期的贸易状况,没有以整个两河流域文明为对象来进行总体研究。本文既要从横向方面研究亚洲西端跨区域贸易的点、线和面,包括贸易中心、贸易路线和贸易网络,又要从纵向来研究两河流域贸易发展历史,即从史前直到波斯帝国时期的跨区域贸易发展历程。在空间上,本文以两河流域地区为中心,对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贸易路线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包括东线之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阿富汗陆路、南线之波斯湾−印度洋海路、北线之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跨境贸易、西线之两河流域−东地中海世界贸易,并且分析亚述御道和波斯御道这些首先服务于军事事务的多功能道路交通网络,以及与后来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阿富汗陆路贸易
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前的亚洲西端,中亚与印度河流域地区至两河流域地区主要存在两条跨区域贸易路线:一条是陆路,从阿富汗、印度河流域向西经伊朗高原,穿过扎格罗斯山脉,到达两河流域地区,然后继续向西直到东地中海沿岸,继续向北直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继续向西南直到埃及,称为北路,在时间上大约为公元前6000至前1000年;另一条是海路,从阿富汗、印度河流域地区,沿印度洋向西经波斯湾,北上直至两河流域地区,称为南路或印度洋−波斯湾商路,在时间上大约从公元前2500至前1800年。其中前者,即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阿富汗陆路是亚洲西端历史上最早的、也是历时最长的跨区域贸易路线。
两河流域地区与伊朗高原的联系由来已久,两地之间资源的“盈亏”现象是双方贸易产生的基本前提。因为两河流域缺乏矿产资源,而伊朗高原富含矿产资源,两河流域从伊朗高原进口矿产资源,同时出口粮食和羊毛纺织品至伊朗高原,这样双方可以实现商品互补。这是双方最直接的贸易往来,也是最早产生的贸易方式,贸易路线(商路)也随之开通。两河流域以大河文明为特征,伊朗高原以山地文明为特征。在历史上,两河流域各个王朝的统治者都将伊朗高原作为必须要征服与支配的地区,一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二是出于经济贸易目的。由于两河流域文明要早于伊朗高原文明,文化相比伊朗高原要更为先进,所以,在双方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以两河流域城市聚集文明作为支配、主动的一方,而伊朗高原游牧散居文明作为被支配和被动的一方,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单边”贸易模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伊朗高原在与两河流域的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过,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在伊朗东南部雅赫亚[11]、伊朗东部沙里索科塔[12]、波斯湾地区以及中亚等地的考古发掘成果陆续问世,学者们开始改变过去的看法,转而认为伊朗高原早在大约公元前3400至前3000年(相当于两河流域历史上的乌鲁克文化晚期与捷姆迭特纳色时期),已经与两河流域在贸易交往中处于平衡的地位。有证据表明,在建立和维持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与定居文明方面,贸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伊朗高原的这些贸易点,在同两河流域进行跨区域贸易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在这些贸易中,除了与两河流域的直接贸易,比如伊朗将本地雅赫亚所产的绿泥石(滑石)出口至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还作为东部更远的印度河流域、中亚阿富汗地区同两河流域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和原料加工地,比如阿富汗所产的青金石经过伊朗高原的沙里索科塔的中转与初步加工后再被运送到两河流域地区。
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地区的跨区域贸易十分重要,不管在考古发掘还是文献记录方面,都有大量相关证据存在,对于这条商路和贸易机制的探讨,成为学者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两河流域历史上,最早进行跨区域贸易的是其北部地区,最早的贸易都和资源产地相联系。在公元前7千纪的新石器时代,产自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山脉的黑曜石已经在两河流域被普通使用,这是人类最初为了提高生产力和劳动生产效率所进行的资源贸易活动[13]。公元前5千纪的欧贝德文化时期,欧贝德风格的陶器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和叙利亚北部被发现,表明两河流域北部已经同更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有了简单的贸易往来[14](69-73)。从公元前4千纪的乌鲁克文化期开始,随着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逐步进入文明社会,两河流域的贸易中心由北部转到南部,苏美尔人逐渐认识到资源的战略重要性。他们通过建立前哨基地来控制资源,为了获取安纳托利亚的铜资源,苏美尔人在土耳其的哈希奈比丘建立殖民点。此外,苏美尔人通过控制伊朗的苏萨和胡齐斯坦,从伊朗高原的塔尔梅西进口铜。公元前3000年左右,铜和锡的合金制成青铜,青铜比铜更加坚硬和实用。这开启了西亚的青铜时代,也同时促进了跨区域贸易的发展[1](6-9)。可以说,在整个乌鲁克文化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由于缺乏石材、金属和大型木材等原材料,急需同安纳托利亚、伊朗地区和更远的印度河流域进行跨区域贸易,这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以及楔形文字泥板记录都能够得到印证。
在亚洲西端跨区域贸易中,宝石、贵金属和木材作为商品从西亚各地运送到两河流域,其中以青金石贸易最为著名。这条连接阿富汗和两河流域之间的商路,以阿富汗的巴达赫尚为起点,青金石首先被运送到伊朗东南部的沙赫里索克塔,并在那里进行切片、清洗、加工成纯净成品,然后再运送到最终目的地两河流域。自史前时代直到公元前2900—前2400年的早王朝时期,青金石这种珍贵材料从远隔数千公里的阿富汗,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两河流域,作为最珍贵的宝石之一,深受两河流域上层人们的追爱[15]。比如苏美尔文学作品《恩美卡和阿拉塔之王》[16],讲述了大约公元前2700年的乌鲁克之王恩美卡用两河流域的粮食来交易阿拉塔(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吉罗夫特)的青金石和金银,为伊南娜女神建造神庙。可以推知,位于伊朗的阿拉塔也是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及阿富汗之间贸易的中转站。据另一部苏美尔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和胡瓦瓦》[17](149-165)记载,恩美卡之孙吉尔伽美什和他的亲密伙伴恩奇都长途跋涉来到雪松山(今黎巴嫩),杀死守林怪胡瓦瓦,砍伐雪松并用船将其运回乌鲁克,这从侧面体现了在当时两河流域与地中海东岸的木材贸易日盛。
亚洲西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陆路贸易延续数千年之久,是丝绸之路开辟以前西亚的主要贸易纽带,为丝绸之路在西亚的连通奠定了基础,其许多路线后来被丝绸之路所沿用。通过伊朗高原的过渡地带,以两河流域高度的文明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不过,随着古代商人探索范围与技术的进步,海上贸易逐步取代陆上贸易,成为亚洲西端的主要跨区域贸易形式,也必将推动又一轮的文化交流。
二、波斯湾−印度洋海路贸易
大约公元前2500年,亚洲西端的跨区域贸易发生转变:由陆路转向海路,由北路转向南路。两河流域逐渐减少了途经伊朗高原到阿富汗的陆路贸易,转向经波斯湾到印度洋再到阿富汗的海上贸易。从楔形文字文献出现的三个连续地名狄勒蒙、马干和麦鲁哈来看,这些地区所盛产的物品如青金石、红玉髓、象牙、木材、石材、黄金和铜等原材料被运送到两河流域。这三个连续的地名代表了波斯湾−印度洋沿岸的重要贸易站点,说明了当时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的 繁盛。
狄勒蒙原指阿拉伯半岛塔鲁特海岸一带,在公元前3千纪之后,特指位于波斯湾的巴林。巴林岛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富产优质枣椰。由于农业土地有限,粮食不足以维持本岛居民消费,狄勒蒙人从苏美尔进口粮食,同时出口鱼类和珍珠。在巴林考古出土了两种不同衡制(两河流域衡制和麦鲁哈衡制)、苏美尔和印度河流域题材的印章,证实了两河流域与狄勒蒙的早期贸易。苏美尔文献中提到的许多狄勒蒙商品,其原产地不在狄勒蒙,而在印度河流域或阿富汗,这说明狄勒蒙作为一个贸易中转港和集散中心,联通着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的远途贸易。
马干原指伊朗马克冉沿岸,后来专指阿曼,在两河流域文献中指位于狄勒蒙和麦鲁哈之间的地区。据两河流域文献记载,马干富含铜矿和闪长岩资源,楔形文字文献中称马干为“铜山”[18]。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大量的铜在阿曼半岛被开采。据“古地亚滚筒铭文”记载[19],古地亚派人到马干开采闪长岩矿,并且同马干人交易铜,后来他用闪长岩制造了许多自己形象的雕像,上面刻有长篇苏美尔语楔形文字铭文,记述闪长岩的来历、制作过程、神庙建造,以及歌颂诸神事迹等。阿曼铜资源的开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河流域对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地区铜矿的过度依赖,转向南方海路来开发马干的铜资源。这也是导致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的北方陆路逐渐衰落、南方波斯湾海路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此,马干成为继狄勒蒙之后,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海上贸易的前哨阵地和重要的货物枢纽中心。
麦鲁哈指印度河流域沿岸,大概对应于今天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信德省沿岸和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沿岸地区[20]。据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记载,麦鲁哈盛产黑檀木、黄檀木、“阿巴”木(ab-ba)等优质木材,黄金、玛瑙、红玉髓等矿产,孔雀、黑鹧鸪等鸟类,以及象牙等资源,成为两河流域进口物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2](161)。两河流域人们可能没有到过麦鲁哈,而麦鲁哈人肯定到过狄勒蒙和两河流域。据楔形文字文献记载,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曾炫耀,麦鲁哈的船停泊在了阿卡德城。此外,一枚阿卡德时期的圆筒印章表明,持有者是“麦鲁哈的翻译人员”(eme-bal)[21](15)。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词表工具书记载了大量麦鲁哈的货物和商人信息。乌尔第三王朝拉格什行省还有一个独特的“麦鲁哈村”(e2-duru5 me-luh-ha)[22],村里的居民是来自麦鲁哈的移民,他们和两河流域本地人已经互相融合,如有的居民起了两河流域的名字,接受了两河流域文化。麦鲁哈作为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的最东端和起点,不仅直接出口本地物产,还在阿富汗的绍图盖伊建立商业居民点,垄断青金石和锡矿等珍贵资源,并转手出口到两河流域,赚取高额利润。
公元前2004年,乌尔第三王朝灭亡,麦鲁哈在两河流域文献中逐渐消失,两河流域与麦鲁哈的直接海上贸易中止,转为间接贸易,即需要通过狄勒蒙的中转。狄勒蒙在这条贸易路线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过狄勒蒙的辉煌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大约公元前1800年开始,由于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并最终灭亡,以及两河流域中北部巴比伦和亚述的地位日益突出,昔日繁荣的波斯湾−印度洋海上贸易不久后终止。两河流域与东部地区的联系又转向陆路,伊朗高原的地位再次凸显。不过,安纳托利亚继史前时代黑曜石贸易之后,再次成为两河流域北线贸易的主角,从公元前2千纪初开始在亚洲西端贸易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三、古亚述时期安纳托利亚跨境贸易
古亚述贸易指公元前19世纪开始的古亚述商人与安纳托利亚地区进行的跨区域长途贸易,历时几个世纪之久,影响之深远,为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跨区域贸易之一。下文将从古亚述的贸易概况、贸易据点与城市、交易商品种类以及贸易组织与管理特征等几个方面来逐一探讨,以期展现出一幅清晰的古亚述贸易画卷。
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地区,是沟通南部巴比伦尼亚和更北部安纳托利亚的桥梁,古亚述时期(大约公元前1900—前1400年)的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若干居民点,从事跨境贸易,其中尤其以安纳托利亚的卡尼什(今土耳其境内)“卡鲁姆”(居民点)最为著名。在阿卡德语中,较大的居民点被称为“卡鲁姆”(karum,“港口”),较小的居民点被称为“瓦巴尔图姆”(wabartum,“贸易站”)[23]。在古亚述文献中,亚述商人记录了他们的装运货物、费用和商业合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学者们通过不懈努力翻译和出版了大量文献,以及发掘了丰富的考古证据,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古亚述跨区域贸易长卷。亚述在跨区域贸易中发挥了主导和中转的双重作用。古亚述跨境贸易的主要交易商品包括金、银、铜、锡、纺织品(主要是羊毛)等。
古亚述贸易在组织上的一个独特之处,是亚述商人的妻女在亚述的阿淑尔城加工制作纺织品,然后由其丈夫将纺织品和羊毛原料用驼队运送到安纳托利亚的卡尼什等地进行贸易,换取安纳托利亚所产的黄金和白银。此外,亚述商人还从事中转贸易。由于两河流域自身缺乏金属和石材等资源,亚述商人便将产自阿富汗的锡、产自马干和伊朗等地的铜转运到卡尼什,换取金银(作为流通货币)。其中,锡和黄铜都是制作青铜的原料。于是,随着这一时期锡、铜贸易的繁盛,青铜制品被大量制作出来,并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这预示着西亚青铜时代的到来。
古亚述贸易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管理。卡尼什“卡鲁姆”的管理者并不住在卡尼什城,而是住在他们的家乡——亚述的阿淑尔城。他们中许多人都是阿淑尔当地高级家族出身,在亚述朝中担任要职。家族的高级成员组成委员会,监督卡尼什的各项事物,对进口商队征收日常商业税。除此之外,商旅队还要缴纳每个过往地区的过路费,以及缴纳给卡尼什当地贵族的各项税赋。尽管税费负担沉重,这条商路的利润依然大得惊人,投资者获得的基本都是百分之百的回报率[24](4)。我们对于卡尼什贸易的认识主要来自卡尼什的考古发掘。卡尼什遗址的发掘不仅为研究赫梯国家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更为研究古亚述贸易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在公元1880年之前,卡尼什的当地居民就发现了一些楔形文字泥板,一共有4 000多块,它们后来陆续流入文物市场,被欧美各大博物馆收藏(柏林、伦敦、巴黎和耶鲁巴比伦藏品等)。1925年,捷克东方学家赫罗兹尼对卡尼什进行了尝试性发掘,出土楔形文字泥板500余块[25]。1948年,土耳其考古队在厄斯古奇的主持下,正式发掘卡尼什,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2005年,共出土楔形文字泥板18 000余块,目前从卡尼什出土的泥板文献共计约23 000 块[26]。这些泥板文献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书信、合同、裁决记录、词表、备忘录、草稿、注释和运输文献等。
书信文献大多数是商业书信,许多书信记录的是来自阿淑尔的商人报告商队到达及装备情况,也有记录安纳托利亚内部或不同商业殖民地的人们(亲属、合作伙伴、代理人和职员)之间进行的交流。在许多情况下,亚述人在安纳托利亚某地(卡尼什以外)从事商业活动时收到的信件被随便带回家,成为卡尼什文献档案的一部分。除此,还有专门处理家庭事务的信件以及官方公务信件。书信档案中也有一些是信件复本,原件由商人送到卡尼什,然后他们回到阿淑尔后又与留在卡尼什管理事务的儿子们通信。发出去的信件被包裹在泥制的信封中,信封上记录寄信人(有时也加盖其印章)和地址等[27](50)。有的发掘出土的信件依然被包裹在信封中,说明了它们的保存状况,也有可能一直没有被打开过。法律文献包括两小类:其一是合同,二是司法文献。合同文书由数百份借款通知单组成。一类为借贷合同,由赊账和委托组成,合同行文是从债权人(贷方)视角记录,他对债务人(借方)有索赔权(işşēr … išû)。这些合同内容包括白银数目、借方信息、到期日期和拖欠利息等。还有一类为雇佣合同(be’ūlātu合同),即雇佣从事商品运输的商队,还涉及购置房屋和奴隶、贸易投资等事宜。第三类合同涉及家庭法、收养、结婚、离婚和继承等[28]。司法文献则记录了司法裁决的整个过程,从私人召集和自愿仲裁到由最高司法部门市议会作出最终裁决。许多文献是关于证人和当事人出庭宣誓并作证的记录,包括宣誓记录和审问记录。比较特别的一类文献是从阿淑尔城发送过来的所谓“权威泥板”(tuppum dannum),包括程序指令和临时决定。除了书信和法律文献,卡尼什文献中还有一类比较琐碎的文献,包括备忘录、注释、词表、草稿和复本等,它们没有法律效力。这些泥板尺寸比较小,铭文较短,比如注释类文献是对一般交易记录的注解以及摘要。词表列举人员、纺织品或白银数目,费用,商品种类(粮食、羊毛、纺织品、铜、锡、白银),接收和储存等简短信息。运输类文献记录金银运输到阿淑尔,纺织品运输到卡尼什,以及运输人员等信息[29]。
约公元前1820年,卡尼什被赫梯国王摧毁,跨境贸易也随之终结。虽然后来亚述的沙姆西阿达德 (公元前1808—前1776年)和马里的级姆利里姆(公元前1775—前1761年)统治时期有过短暂复苏,但是随着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统一两河流域后,卡尼什贸易逐渐衰落。古亚述贸易以其独特的组织与管理方式而著称,其中的驼队贸易为后来的丝绸之路驼队的雏形,也提供了安纳托利亚早期贸易路线的原始证据。安纳托利亚高原作为亚洲通往欧洲的桥梁,这里的早期商路的开辟,为后来丝绸之路贯通亚欧大陆提供了最初的原型与参考,而更西部的贸易除了从北部的安纳托利亚沟通外,从东地中海沿岸继续向西的贸易路线也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早期证据。
四、东地中海世界贸易
东地中海世界指的是地中海东岸的各地区总称,自北向南包括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塞浦路斯岛(古称阿拉西亚)与爱琴海部分岛屿。这一地理区域位于古代世界几大早期文明的交汇处与中心点,包括希腊文明、赫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等,各个文明之间通过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如联姻[30]与贸易[31])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东地中海贸易纵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最后统一归为丝绸之路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作为丝绸之路的亚洲最西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石材、金属、木材等资源依赖于进口,本地产大麦、小麦等粮食以及羊毛等纺织品,而两河流域的周边地区正好资源丰富,比如安纳托利亚的黑曜石、黄金、铜,伊朗高原的红玉髓、铜与黄金,印度河谷的黑檀木、象牙,阿富汗的青金石,阿曼半岛(马干)和塞浦路斯岛的铜矿等。这种自然特征促使了国际跨区域贸易的产生与发展。以两河流域地区为中心,贸易向四周辐射,构建了若干条跨区域商路网络。其中,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到两河流域的黑曜石贸易成为最早的贸易证据。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时期时代早期,东地中海世界的黑曜石分布网已经形成,导致黑曜石贸易的产生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伦弗鲁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科学考古最伟大的成就之一[32]。从地质学角度来看,黑曜石根据化学性质和相同火山区的岩相学,可以划分为三类:碱性、钙碱性和过碱性。在史前石器时代,黑曜石被制作成砍削工具。由于不同产地的黑曜石的物质成分各异,这使得科学家们可以通过测量黑曜石的化学成分等技术方法来探究黑曜石的具体来源与产地,从而根据不同产地黑曜石的分布情况来窥探远古时代的黑曜 石贸易。所以说,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史前时代,我们对于黑曜石贸易的探索只能依赖于考古学、地质学、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对各地黑曜石微量元素检测的INAA (Instrumental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33]等技术手段来完成。这与文明时代贸易与商路的探讨主要依赖于文字文本材料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黑曜石这种资源在近东地区应用广泛,而到了文明时代,金属工具的使用逐渐替代石器工具,黑曜石则主要被用来制造个人饰品和奢侈器物,由实用功能转变为艺术功能。米洛斯岛是爱琴海世界最重要的黑曜石产地,它的黑曜石主要出口至希腊本土和爱琴海诸岛[34],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的希腊城邦[35],其中后者主要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爱琴海沿岸的伊兹密尔与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恰纳卡莱地区。爱琴海、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两河流域地区经黑曜石这一共同使用的工具媒介,沟通为一个整体,都被纳入东地中海贸易。
从公元前4千纪中期开始,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就在沟通波斯湾(印度洋)与东地中海(大西洋)的海上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美尔人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北部)弯曲一带的“殖民”垄断,控制了从波斯湾途径叙利亚港口直到埃及三角洲之间的贸易路线[36]。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所记载的进口商品种类来看,在公元前3千纪的苏美尔文明时期,海上贸易有了明显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波斯湾到东印度洋沿岸的印度河流域地区(古代称麦鲁哈),另一个是沿幼发拉底河向上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再由沿海港口跨海驶向爱琴海诸岛(如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以及埃及三角洲沿岸地区。后一条商路即属于东地中海世界贸易的组成部分。公元前2千纪,两河流域与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埃及三角洲之间的贸易商路得到迅速发展。主要由两条商路组成:一条商路从幼发拉底河中游河谷的马里城邦,途径塔德马尔到达地中海商路尽头的喀特那;另一条商路从阿勒颇出发,远离幼发拉底河岸的埃马尔,途径哈拉卜、喀特那和哈措尔直到埃及,途径的沙漠地带后来使用骆驼来运输商品,这条商路被称为骆驼商路[37]。其他的沙漠商路都是希腊化时代以及更后期才开通的。喀特那在锡商路中被提到,锡商路从马里经喀特那到达东地中海。塞浦路斯所产的铜经许多商路运输,包括东地中海贸易路线、安纳托利亚路线,以及途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到达两河流域地区的跨区域贸易路线[38]。马里文献中提到,衣物、纺织品、一种弓状物、珠宝、木材、葡萄酒和二轮战车作为贸易商品经喀特那被运输到马里,部分被运送到巴比伦。在喀特那发掘的一件镂空雕刻的狮头器皿(约公元前1340年)是由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琥珀制成,而这种琥珀也在同时期的迈锡尼被发现[39](62)。
上古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贸易体系,在空间范围上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希腊城邦、塞浦路斯岛等地区,它们沟通了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赫梯文明、叙利亚−巴勒斯坦文明和爱琴文明等几大古老文明。具体的商路有爱琴海诸岛到东方的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又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向东到达两河流域和伊朗等地;而东方的商品最远从印度河流域、中亚阿富汗地区经伊朗高原到达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又从两河流域中转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再经东地中海商路到达埃及、塞浦路斯岛,甚至最终到达爱琴海的希腊诸城邦。通过东地中海世界的沟通,古代近东各地的特产商品被交易到更远的希腊城邦,同样,希腊的特产也被交易到东方的近东地区。东西方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直接的交流并不是兵戎相见的战争方式,而是和平友好的贸易伙伴关系。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历史演变,政治因素逐渐凸显,公元前1274年埃及与赫梯的卡迭石战役[40],将原先的东地中海世界搅乱了。后来出现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的扩张政策,将东地中海世界纳入了自己的帝国政治版图,原先的国际贸易演变为帝国内部的贸易,原先受希腊人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交近东人之手,贸易权力的转移也预示了政治军事势力的演变。古代近东文明再后来被以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以及东方的帕提亚文明所代替,东地中海世界贸易的影响不断扩大,最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它们又统一纳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五、结语
古代两河流域的石材、木材和金属等自然资源极为缺乏,却盛产大麦、小麦、椰枣等粮食作物以及牛、羊等牲畜。两河流域周边地区是木材、石材和各类金属的主要产地,这种商品货物在地理上的不平等分布造就了早期贸易的产生。早期贸易的发展,导致商路和商路网交织形成,促进了古代两河流域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进步。古代两河流域商路的形成不是同步并行、同时产生的,而是在不同时间段,存在不同的商路,有的商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衰落,有的商路则变得繁荣,有的被取而代之,有的得以复兴。这里没有规律可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窥探导致商路和贸易盛衰的因素。
从大约公元前7千纪的史前时代到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中巴比伦时期,亚洲西端的跨区域贸易以和平方式为主,辅之以战争征服获取战利品。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史前时代,考古发现和历史遗迹成为我们认识当时贸易的仅有手段。自楔形文字出现之后的文明时代,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一同成为我们复原当时贸易的重要依据。早期亚洲西端的跨区域贸易,以陆路为始端,并且持续时间最为长久,达四五千年。在空间布局上,从阿富汗到两河流域横穿大约3 000公里,从波斯湾到安纳托利亚纵贯也是大约3 000公里。史前时期的两河流域北部初为贸易中心,后来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最早产生文明,逐渐代替北部成为贸易和文化中心。两河流域东部的伊朗高原作为贸易中转站,北部是亚美尼亚高原,南部到印度河流域地区(今巴基斯坦),直至今阿富汗地区,西部到达叙利亚和东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埃及、塞浦路斯岛乃至希腊。公元前2500年左右,波斯湾−印度洋贸易开始繁荣,以两河流域地区为中心的亚洲西端形成了海陆两条贸易路线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而这时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却向更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展开跨境贸易,继续扮演着贸易主导者和中间人的双重角色。
从公元前2千纪晚期开始,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愈发显得重要,原先和平的跨区域贸易演变为战争冲突与资源争夺。这一时期的主要商品不再仅是金属、石材和木材等自然资源,还包括马匹等战略资源。马匹既可以用于交通运输,又能用于军事作战,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约公元前1500至前1300年的中亚述时期,来自东部扎格罗斯山区(今伊朗)的马匹被出口到亚述,又从亚述转运到米坦尼,以换取那里的手工艺品。为了争夺伊朗西部曼奈德的优质马匹资源的控制权,亚述和乌拉尔图爆发了战争。除了马匹贸易,黎巴嫩的雪松也成为西亚各大政治实体争夺的主要资源。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骆驼运输在亚洲西端跨区域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骆驼商路沟通阿拉伯半岛、埃及、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这条商路在亚述帝国时期成为亚述国内的主要贸易通道,被称为“亚述御道”(阿卡德语:harrān šarri),发挥着通信、贸易、军事和公共交通等多功能作用。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开辟的“波斯御道”,很大程度上是在亚述御道基础上修筑的,从安纳托利亚的萨尔迪斯南下直达波斯首都苏萨,全长约2 700公里。这两条帝国御道一改早期商路单纯的贸易属性,在以军事目的为前提的背景下,兼顾驿道、商道和交通等多重功能,其主要路线后来又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雏形。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在亚洲西端沿用了亚述和波斯的道路遗产。这为沟通古老的商贸通道提供了可能,为更广阔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
[1] MARK S. From Egypt to Mesopotamia: A study of predynastic trade routes[M]. Austi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LEEMANS W.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M]. Leiden: Brill, 1960.
[3] HERRMANN G. Lapis Lazuli: The early phases of its trade[J]. Iraq, 1968, 30(1): 21−57.
[4] VEENHOF K. Aspects of Old Assyrian trade and its terminology[M]. Leiden: Brill, 1972.
[5] DERCKSEN J. The Old Assyrian copper trade in Anatolia[M].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1996.
[6] CRAWFORD H. Dilmun and its Gulf neighbour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HAWKINS J. Trad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M]. London: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 1977.
[8] SASSON J.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M]. New York: Chales Scribner’s Sons, 1995.
[9] DERCKSEN J. Trade and finance in ancient Mesopotamia[M].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1999.
[10] 吴宇虹, 国洪更. 古代两河流域和巴林的海上国际贸易[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5): 82−88.
[11] LAMBERG-KARLOVSKY C. Excavations at Tepe Yahya, Iran. 1967—1969[M].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12] TOSI M. Excavatios at Shahr-i-Sokht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second campaign, September-December 1968[J]. East and West, 1969, 19(3−4): 283−386.
[13] DÜRING B, GRATUZE B. Obsidian exchange networks in prehistoric anatolia: New data from the black sea region[J]. Paléorient, 2013, 39(2): 173−182.
[14] WATSON P. The chronology of north syria and north mesopotamia from 10,000 BC to 2,000 BC[C]// R.W. EHRICH.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5] LIMET H. Les Métauxà l’ époque d’ agade[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72, 15(1−2): 14−17.
[16] 拱玉书. 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17] GEORGE A. The Epic of Gilgamesh[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18] HANSMAN J. A “periplus” of Magan and Meluhha[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3, 36(3): 554−587.
[19] EDZARD D. Gudea and his dynasty[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20] 刘昌玉. 麦鲁哈与上古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50−56.
[21] EDZARD D. Die Inschriften der altakkadischen Rollsiegel[J].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1968(22): 12−20.
[22] PARPOLA S, PARPOLA A, BRUNSWIG R. The Meluḫḫa village: Evidence of acculturation of Harappan traders in late third millennium Mesopotamia[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77, 20(2): 129−165.
[23] OGUCHI H. Trade routes in the Old Assyrian period[J]. Al-Rafidan, 1999, 20: 85−106.
[24] LARSEN M. Old Assyrian caravan procedures[M].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1967.
[25] DONBAZ V. Keilschrifttexte in den Antiken-Museen zu Stambul 2[M].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9.
[26] ÖZGÜC T. The palaces and temples of Kultepe-Kanis/Nesa[M]. Ankara: Tu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1999.
[27] VEENHOF K, EIDEM J. Mesopotamia. The Old Assyrian period[M]. Freiburg/Göttingen: Academic Press Fribourg/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8.
[28] KIENAST B. Das altassyrische Kaufvertragsrecht[M].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4.
[29] ULSHÖFER A. Die altassyrische Privaturkunden[M].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5.
[30] 郭丹彤. 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盟和联姻[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 109−114.
[31] 刘健.“世界体系理论”与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2): 62−70.
[32] RENFREW C, DIXON J, CANN J. Obsidian and early cultural contact in the Near East[J].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966, 32: 30−72.
[33] ERICSON J, KIMBERLIN J. Instrumental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techniques of analysis, data analysi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obsidian standard[J]. Newsletter of Lithic Technology, 1974, 3(3): 44.
[34] TORRENCE R.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stone tools. prehistoric obsidian in the aegea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 PERLÈS C, TAKAOGLU T, GRATUZE B. Melian obsidian in NW Turkey: Evidence for early Neolithic trade[J].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011, 36(1): 42−49.
[36] MOOREY P. From Gulf to delta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The Syrian connection[J]. Eretz-Israel, 1990(21): 62−69.
[37] LAMBERT W. The domesticated camel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evidence from Alalakh and Ugarit[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960, 160: 42−43.
[38] MILLARD A. Cypriot copper in Babylonia, c.1745 B.C[J].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1973, 25(4): 211−214.
[39] PFÄLZNER P.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Royal Palace of Qatna[C]//Bonacossi D. Urban and Natural Landscapes of an Ancient Syrian Capital. Settlement and Environment at Tell Mishrifeh/Qatna and in Central-Western Syria. Udinese: Forum Editrice Universitaria Udinese, 2007.
[40] GOEDICKE H. Considerations on the Battle of Kadesh[J].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66, 52: 71−80.
Exploration into the trans-regional trade centered on Mesopotamia prior to the Silk Road
LIU Chang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Asia, is the earliest civilization in the human history, exerting influences of various degrees on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e trans-regional trade in the western Asia centered on Mesopotamia before the Silk Road opened up in Han Dynasty. This study, by employing the cuneiform textual literature as well as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empirical methodology, aims to offer a systematic trim of and exploration into the trans-regional trade in the western Asia prior to the Silk Road, including Iran-Afghanistan trade route in the east, Persian Gulf-Indian Ocean route in the south, Anatolia-Assyria route in the north,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route in the west. A series of trans-regional trade routes in the earlier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multi-functional road systems which appeared initially for military purpose during Assyrian Empire and Persian Empire, have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later.
the Silk Road; Mesopotamia; trade route; trans-regional trade; cuneiform textual literature
2018−05−06;
2018−05−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研究”(17CSS007)
刘昌玉(1984—),男,山东青岛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亚述学,联系邮箱:assyrialiu@126.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9.03.020
K12
A
1672-3104(2019)03−0176−08
[编辑: 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