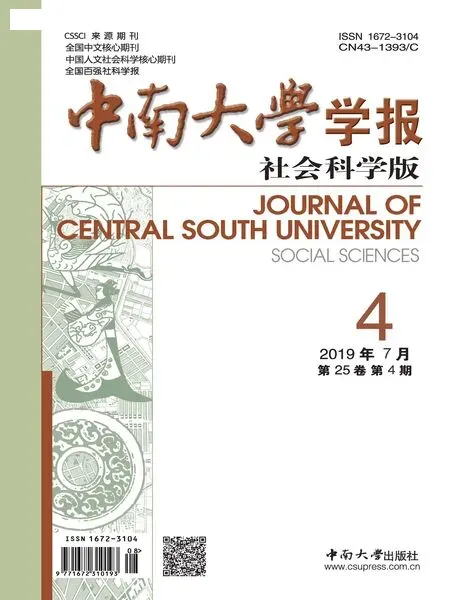从民间文艺到革命号角: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改造(1937—1949)
张屹,徐家林
(1.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2.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621010;3.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42)
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理念,“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革命阶级和政党所认同并实践。在党的革命动员历史中,特别是在根据地和边区,党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强化乡村民众动员的有效性。但要真正让乡村劳动群众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绝非易事,关键就在于找到乡村传统文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交汇点。为此,中国共产党将民歌、戏剧、说书等民间传统文艺纳入革命话语体系之中,通过对旧元素的改造与新元素的植入,尤其是通过革命文艺新作品的创演,使其成为联通民族民主革命与乡村民众的有效载体,实现了民间文艺与革命思想的对接与融合。本文拟以党对乡村艺人的改造为研究对象,探究我们党如何认识乡村艺人的革命动员价值,如何改造乡村艺人、形塑“文艺新人”,以及“文艺新人”如何改造传统文艺、创造革命文艺、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历史过程。以期通过这一过程的探究,加深对党运用传统民间文艺助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解。
一、革命的期许:乡村艺人的革命价值
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直接影响革命进程及其成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往往更能获得后人的关注,而那些历史细节或助力革命成功的一些普通群体则容易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活跃着一大批乡村艺人。他们的表演,娱乐了乡村民众,形塑了乡土社会。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潮中,他们也许并不起眼,然而他们却以其独特的方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革命动员功能和价值的认识正是从他们的文艺展演开始的。
(一) 在旧功能中发现乡村艺人的新价值
乡村民间文艺是乡村民众的情绪表达、情感寄托和精神归属。民众或吟唱民谣,以表达喜怒哀乐;或听曲看戏,以颂扬“忠孝节义”;或舞蹈秧歌,以祈求风调雨顺。这些民间文艺,大多自编自演,对于艰苦乏味、单调枯燥的乡村生活而言,无疑是一副必不可少的调味剂。李景汉曾用妙趣横生的生活话语,描绘了他在河北定县调研时所看到的乡村社会舞、唱秧歌的生活景象,“演唱秧歌的村庄的住户,大半借此机会请他们外村的女亲戚,特别是姑奶奶、外孙、外孙女等人,来村里家中住几天,款待他们。”[1](337)李景汉对舞、唱秧歌生活图景的描摹,生动地表明了民间传统文艺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力。但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又不止于娱乐民众,它还承载着“治国化民、惩恶扬善”的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功能,并表现为大众娱乐与民众教化的统一,调剂生活与动员民众的统一。其实,以传统文艺教化民众,并非是新时代的新风尚。传统戏曲《琵琶记》开场词即一语道破了戏曲褒贬取舍的依据:“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2](1127)即说明文艺娱乐对民众的教化,有其久远的历史。及至民族民主革命,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艺有其新的教化价值,主张将传播革命思想与传统民间文艺相结合,“现在我们的艺术工作的内容,自然是唯一的宣传抗战,而在用旧形式比较能够深入民众的场合,我们应该使我们的艺术工作的内容,多多通过民间的旧形式。”[3]由此可见,传统民间文艺所表现出来的娱乐与教化的双重功能,开始为革命者尤其是党的领导者所重视。
然而,传统民间文艺新的革命教化功能的发挥,仍须依赖旧的乡村艺人。一方面,旧乡村艺人是传统文艺的创造者。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收集艺术表演题材,从普通的民众话语中提炼表演语言,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表演内容。无论是歌颂爱情的山歌花儿,或是反映生产活动的劳动号子,无一不是来自乡村艺人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旧乡村艺人又是民间文艺的表演者。他们的文艺表演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民众情感与伦理体验、政治与道德观念的鲜活反映。因此,实现民间文艺新的政治动员功能,关键还是要改造和利用民间艺人。20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曾对民间文艺创演有过如下阐述:“民间文艺的被利用,还是以民间艺人的被利用为其主要的契机。”[4]郭沫若的观察,可谓抓住了民间文艺新价值利用的要领。
(二) 对旧艺人提出革命动员的新期许
回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党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当时党对乡村艺人的新期许。1941年,许光在总结根据地的剧院工作时,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加强新旧艺人的团结,争取旧戏班”,并主张将其作为向新方向进军的“先决条件”。[5]1944年,毛泽东也明确阐述了改造旧戏班,使之为革命服务的设想,并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6](583)。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要求改造乡村艺人,利用其服务革命动员的设想,开始由个人倡议上升为党和人民政府的文艺方针政策。1946年,华北人民政府将一份文件中规定的乡村艺人政策,在《冀鲁豫日报》上广而告之:“团结与改造一切民间艺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创作天才,利用一切民间艺术形式,充实新的内容,鼓励创造民众喜闻乐见、活泼愉快的新形式。”[7]这一政策,一方面明确了党对乡村艺人“团结”“改造”“利用”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乡村艺人的期许:希望他们能够创造更多易于被人民群众接受、服务革命的文艺作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期许并不止于文艺作品的创作,对乡村艺人的表演也提出了明确要求。1939年,毛泽东在观看秦腔《中国拳头》后,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演出“简单,明了,动人”[8](106)。革命领袖的赞扬表达了党对乡村艺人文艺作品及其演出的认可,同时也表达了党对乡村艺人创演的期望,期望其服务于人民、服务于革命,即凭借其文艺作品展演激发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革命意识,感召民众拥军支前,甚至加入革命队伍。柯仲平曾明确指出了改造平剧及平剧艺人的目的“是演给抗战革命的干部和民众看”,“给他们服务,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民族、百姓服务”,“也是为抗战、为革命服务”[9]。啸秋(即阮章竞)在检讨戏剧界改造问题及解决方法时也明确指出,乡村艺人的创作与表演(以下简称“创演”)应该“到民众中去,与民众打成一片,一边教育民众,一边向民众学习”[10]。这些话语虽不够完整系统,但也基本能够表明党对乡村艺人的新期许。
(三) 传统乡村艺人相对革命期许的巨大差距
中国乡村艺人的创演活动,从未像这个时代那样,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乡村艺人也从未像这个时代那样,受到革命者的如此重视。时代赋予中国乡村艺人新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们的现实状况,无论是生活习性,还是文化水平、思想认识,都与革命要求存在巨大差距,他们还无法承担传播革命思想、教育人民、动员群众的历史使命。在与乡村艺人的接触中,我们党也逐渐认识到旧乡村艺人所沾染的种种生活恶习。沈冠英讲道,“旧艺人多半有恶习,吃纸烟喝浓茶喝酒,赌博这些嗜好还不算,吸鸦片、吸白面、打吗啡针是旧艺人中普遍现象。”[11](50)沈冠英的话并非只是个人之见,旧乡村艺人的思想落后和不良表现在一份来自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旧艺人)坏处、短处当中,最大的一条是落后思想(如保守迷信等),坏习气和文化水平低。”[12](451)旧乡村艺人所沾染的生活恶习,与其萎靡的精神状态和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也必然表现在其对作品角色的理解和评价方面。革命者田欣就曾批评旧剧中的人物:“《山海关》的吴三桂,谁不知道他是勾结满清,摧残革命的汉奸罪魁,可是在《山海关》这出戏里的吴三桂倒成了净面老生。”[13]类似这样正面宣传“摧残革命的汉奸罪魁”显然与革命倡导的抗战救国等价值观念严重背离,因而也是党的革命宣传与革命动员工作所不容许的。此外,在乡村艺人中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例如在乡村艺人之间,曾流传着“收下徒弟买下马,由我骂来由我打”的俗语。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将艺人束缚在旧戏班、旧行会中,导致我们党团结乡村艺人、利用传统民间文艺进行民众动员的设想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乡村艺人还受到行会头目的剥削。如“必须按时缴纳给行会一笔进奉,不然行会头子就可以不要你在这一地区卖艺”[11](49)。因而,欲使乡村文艺服务于党的革命宣传工作,服务于民众政治动员,必须对乡村艺人进行革命化改造,使其在生活上戒除恶习,强健体魄;在思想上提高认识,拥护革命;在创作表演中“消毒”“祛邪”,去除文艺作品内含的有害成分。
二、革命的“植入”:乡村艺人的革命改造
中国的近现代革命通常把政治与社会改造和人的改造的同步进行作为寻求民族振兴的一种尝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乡村艺人的政治动员价值。但是,乡村艺人的思想状况,与其承担革命动员任务的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唯有通过规范约束、榜样示范等途径,将旧乡村艺人全面改造成为革命服务的“文艺新人”,才能使乡村艺人承担起民众动员的任务。
(一) 日常生活的身体再造
有学者指出,“身体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性思想是相对应的。它们相互补充,构成了现代思想的核心。”[14](53)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革命改造也是从其健康身体的重塑开始。回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旧乡村艺人革命改造的历史,“身体话语”是首先被纳入被改造的视野之中。通过对旧乡村艺人生活恶习的戒除,在身体与革命的互动中,实现了对旧乡村艺人健康体魄的重塑。清末以来,鸦片不仅改变了民族的命运,同时也无分贵贱地进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和下层阶级,抽吸鸦片绝非仅见于王公贵族与八旗子弟,在贫困的旧艺人群体中也相当普遍。抽吸鸦片不仅加剧了他们的经济贫困,同时也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党在对乡村艺人戒除鸦片问题的处理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既突出了戒烟的原则,又展现了戒烟方法的渐进与灵活。这一点在襄垣剧团的禁烟工作中即有体现。党颁布了禁烟条令,明确传达“禁抽大烟”的政策决心,并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使乡村剧团艺人认识到抽吸大烟的危害:“他们因抽大烟,有的把地卖光,有的把房子典当,有的引起家庭破裂、妻离子散。”[15](130)在此基础上,党制定了戒烟的阶段性目标,减少艺人戒烟的痛苦,也使得戒烟切实可行。在晋绥边区长城剧社的艺人改造资料中就有当时艺人戒烟计划详细而具体的记述,“在一个月内,分四周逐步减量,第一周每人每天发五粒烟土;第二周三粒;第三周一粒,第四周停发,加以巩固。”[16](143)还通过召开庆祝大会,给戒烟成功的乡村艺人戴红花、吃“喜糕”进行嘉奖。其意义不只是对成功戒烟艺人的褒奖,也是对尚在戒烟的艺人的鼓励。对于旧乡村艺人身体的革命改造,不限于肉体健康的重塑,还体现在服饰、发式等方面的改变,以塑造与革命要求相适应的新生活、新形象:“滑溜溜的时髦衣服都先后脱去了,女演员的洋式头发也变了样,换上了白毛巾包头……。”[13]田欣的观察说明,在身体重塑与革命规范的互动中,乡村艺人的外在形象与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然而,重塑乡村艺人的健康身体只是对其进行革命改造的第一步,当然也是最为显性的一步。对旧乡村艺人的改造还需要深入其思想与灵魂深处,彻底摆脱旧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其真正成为“内外统一”、服务革命的“文艺新人”。
(二) 思想情感的认同构建
在党对民间艺人的改造中,身体重塑立竿见影,思想与灵魂革命也成绩斐然。在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系中,“倒苦水”是十分有效的形式之一,即通过艺人叙述自己的苦难记忆,诠释过往的历史经验,对比当前,形成旧社会罪恶与新生活美好的情感体验,在此基础上,给他们指明方向,引导他们追求美好的新生活。“他们多少年来,都不被重视,没有社会地位,装了一肚子苦水。咱们改造他们,就可以个别的或集体的,叫他们倒苦水。”[17](24)“倒苦水后要刨根,引导到旧社会和地主的罪恶,刨完苦楚以后,叫他拿主意,树立方向,今后怎么办?”[18](127)通过“倒苦水”,艺人的思想表现出明显转化,并体现在文艺表演中,“在唱‘新旧社会对比’时,他笑容可掬,脸上充溢着对新的生活的热爱;但是一唱到地主的罪恶时,他双眉紧锁,挽起一个沉重的疙瘩,且心也好像萎缩了!”[19](151)可见,“倒苦水”似乎成了忆苦思甜的情感中介。借助“倒苦水”的政治仪式,艺人回顾了过去的苦痛,感受了当下的幸福,从而在思想层面上植入了革命的认同性,在内心深处树立起革命的崇高感,构建了对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全新政治认同。
由改善经济处境达到提高思想认识,是对乡村艺人改造的又一路径。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地位的提高作为乡村艺人改造的基本内容纳入乡村艺人改造体系之中,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采取了民众性的评议与分红办法(按工作努力的效果和表现,按工作的技能,按学习、团结、劳动来平等标准分级给予报酬)更鼓励了大家提高技能。”[20]党提高乡村艺人的经济地位,不仅根据“按劳取酬”合理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还深入听取乡村艺人关于经济分配等方面的意见,回应他们民主参与经济管理的诉求。曾有乡村艺人对“干部额外津贴制度”提出异议,党组织在调查后立即给予了回应,“经过大家讨论,废除了干部额外津贴制度,选出了经济委员会,账目公开。”[21](85)与此同时,解放区不断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使乡村旧艺人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使他们对新生活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翻身后的乡村艺人开始用新的文艺实践来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有一位分到了土地的年画艺人说:“咱画了一辈子神像,还是挨饿受冻,以后要学画人,不画那些鬼神了!”[22]有些年画艺人不仅不再创作旧年画,还在自己的房屋内悬挂起毛主席画像。通过这种“经济性激励”,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乡村艺人在情感上的认同,真心实意地拥护党、支持革命。如此,党即把长期游离于革命之外的乡村艺人纳入革命文艺动员体系之内,对于加强民众革命动员队伍,鼓动乡村民众参加革命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展演内容的革命规范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严格的政治要求,对乡村艺人的创演表现出强大的革命规范力量。这一革命规范力量首先体现在对乡村艺人表演内容的政治与历史观的革命性的严格要求上。如冀鲁豫革命区党委在其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反徐州》对农民形象的污辱,指出应当予以“删改”。重点强调对于“歪曲历史真相”的旧戏,如“‘曾国藩打南京’,以及全部剧情贯穿着迷信鬼神的,都改禁止上演。”[23](353)事实上,党对乡村艺人表演内容的革命规范并未只停留在个别戏剧层面,而是着眼于系统化、体系化要求,并有组织地开展工作。如李春兰在谈规范旧艺人表演内容时指出,“准备组织旧戏审查委员会,通盘审查旧戏,去掉戏剧里封建反动、迷信、堕落、腐化、色情的部分,拉一个戏单,由行署命令公布,开放旧戏,又必须按戏单唱。”[24]这一规范推动了乡村艺人的表演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提升。惩戒违规者是革命规范的另一维度。左权盲人宣传队有一位马姓艺人,曾用算卦骗人、骗钱,被其他同志发现后,盲宣队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让他坦白认错,保证以后永不再犯。并把他算卦挣的钱没收。……留这一百元是看你太苦,可不是奖励你!以后再犯加倍罚!”[25](148)这一权力规范,使乡村旧艺人深切体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之外的革命权威,在心理上形成了对行为底线的自我警觉。乡村艺人表演中蕴含的某些旧元素,必须以革命的要求予以规范,并以文艺新人创作与表演的、与革命相适应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新文艺取而代之。
(四) 楷模形象的榜样示范
革命楷模的形象塑造是中国革命动员的又一维度和基本方式。在乡村艺人的革命改造中,革命艺人的楷模榜样既是文艺新人的理想形象,也代表了革命者对艺人改造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标杆,是启发乡村艺人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在改造陕北艺人时,林山讲述了动员说书艺人韩起祥的经过,“把韩起祥作为一个典型,经常和他联系,派人跟他下乡,给他念通俗书报,讲故事,讲解革命道理,提高他的思想,帮助他编新书,记录、整理、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26]经过革命改造的乡村艺人,不再是村头田边表演娱乐的传统“戏子”,而是被赋予了革命使命的全新角色——“文艺新人”,成为革命政权向根据地和解放区民众进行革命鼓动的艺术尖兵。如坠子戏艺人沈冠英不仅由演唱《剿共歌》的乡村旧艺人,转化为编写革命新坠子《大战杨湖》、宣传革命的文艺新人,甚至还入了党,成为革命文艺动员的重要骨干。“濮阳联合办事处成立了鸭绿江剧社,社员四五十个人,沈冠英担任队副。对社会的生活,对演剧工作,他都十分尽心。还领着剧团,到各乡村演唱,推动农村剧团,唤起民众参加抗战工作。”[27](117)转变如此彻底的艺人并非个案,其中许多优秀者都被作为革命文艺楷模大力宣传,成为艺人学习的榜样。如“练子嘴英雄”拓开科、移民歌手李增正、劳动诗人孙万福、传统民歌艺人李卜等,都被《解放日报》等官方媒体广泛宣传报道,有些人甚至还受到革命领袖的接见、赞扬,成为根据地与解放区闪亮的“明星”。凭借“革命文艺楷模”的大力宣传和形象树立,帮助更多乡村旧艺人消除了革命改造的心理阻力,逐渐同情、支持直至参加革命。
三、革命的号角:乡村艺人的创演动员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改造,一方面,通过对艺人从健康体魄、到情感认同、榜样学习再到革命行动的重塑,实现了从旧乡村艺人到“文艺新人”的人之再造;另一方面,借助“文艺新人”的革命文艺创作与乡村文艺展演,如同吹响了革命号角,唤醒了乡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将游离于革命之外的乡村民众,纳入革命、生产与抗战之中,为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
(一) “文艺新人”的诞生
随着身体、情感以及偶像崇拜的变化,乡村艺人的形象认同与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新旧嬗变。这种新旧变化首先表现为乡村艺人对旧形象、旧身份的自我否定与新形象、新身份的自我认同。从活跃于太行山地区的旧戏班“富乐意”的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乡村艺人形象与身份变迁的生动图景。随着旧戏班改造为新剧团,“旧戏子”变成了“文艺新人”:“我们已不是过去那种混饭吃的、为娱乐而娱乐的‘戏子’,而是已经成为新社会里为人民服务的宣传战士。”[28]可见,“文艺新人”对自己的新形象、新身份高度认同,且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乡村艺人对“文艺新人”称谓的欣然接受,对于艺人自己来说,不只是称呼上的改变,而且是标志着一种新形象、新身份、新使命。他们已明确意识到自己新的角色定位是“为人民服务的宣传战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民众革命动员的自觉鼓动者。乡村艺人的新变化,还表现为民众对艺人新形象与新身份的肯定。如一位为剧团提供住宿的村民,在谈到乡村艺人的新旧变化时,发出了如下感叹:“这剧团可跟从前不一样了,人家打扫房子,又打扫院子。临走还问问家里借东西还了没有,看看短了啥!”[29](88)看来,乡村艺人改变的不只是形象与身份,更是思想和觉悟。一些“文艺新人”不仅有自我改造的觉悟,而且还有改造他人的自觉。陕西眉鄂艺人代表李卜在出席边区文教大会时就明确表示,“我要改造自己,也还要改造别人呢!”他还向文教大会提出建议,“旧戏子难于改造,旧戏子在陕北还有很多,边区外边就更多了,主要是我们的教育,先是把这些人的脑子弄明白。”[30]此时,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个旧乡村艺人,而是一个自觉的“革命的民众艺术家”。李卜只是千千万万个乡村艺人的典型代表。通过党的改造,无数乡村艺人从“旧艺人”转化为“文艺新人”,成为我们党乡村民众革命动员可以依赖的重要力量。乡村艺人形象与身份认同的新变化必然反映到创作与表演上,带来创作立场的转变。
(二) 创作立场的转变
乡村艺人的身份转变,使其创演面向的主题也发生转变。乡村艺人抛弃了“演戏就是为了赚钱,管他为谁服务”[31](101)的旧思想,逐渐理解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的问题,实现了演出面向的新转变。经过改造,乡村艺人开始从民众立场出发,检讨演出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们每次演出后,都会征求民众意见,开自我检讨会,检讨演出效果,询问每个脚角是否尽了自己的力量,和民众关系好坏”,[29]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自身表演的标准,说明了乡村艺人创作表演立场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乡村艺人还以民众身边“真人真故事”为素材,塑造了许多民众“热爱的人物、憎恨的人物”,获得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同。看了演出后,民众异常兴奋,“过去唱的那一朝一帝,现在演的是眼前的真人真事,话也好懂,事也好懂,这才是咱自己的剧团,演咱们自己的事呢!”[32](83)民众对乡村艺人表演的高度认同,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其创作立场的转变,解决了“我们的文艺为了什么人”的政治大方向问题。
要做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乡村艺人的创作与表演。改造以后,乡村艺人抛弃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创作主题,开始围绕翻身、抗战、生产等现实革命需要,开展文艺新作品的创作活动。这从根据地乡村艺人的话语与创演,或可窥见一斑。说书“英雄”韩起祥创作了新书《防旱备荒》,根据韩起祥的自述可知,这一作品的创作与当时蓬勃开展的生产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韩起祥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说旧书,去年自编新书到乡间,为的是帮助革命做宣传……。”[33]创演面向的转变不仅体现在被党组织树为“英雄”的典型艺人的创演上,其实,创演服务革命、服务人民的新文艺已是绝大多数乡村艺人的共识。一批完成了训练班学习的艺人,在即将回到舞台时的表态,就印证了乡村艺人的这种创演方向的转变,“再回到乡村去演唱,那些封建、淫荡、荒唐、腐败的说唱内容都换成土地改革、自卫战争、生产节约的新内容了……。”[34]鼓书艺人刘金堂的话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乡村艺人以文艺创演服务革命生产的热潮:“如开展冬学运动,他们编唱《劝妈上冬学》。反对阎锡山时,唱《王老汉拼命》。参军时就唱《参军》,还有《顽占区人民》。”[35](117)乡村艺人创作立场的转变是乡村艺人新的身份认同的自然结果,也为新的文艺作品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革命文艺的创作
革命文艺的创作首先是从利用旧形式开始的,因为“传统中还有着合理的部分和客观存在的可接受性”[36](389)。已经接受了革命思想的乡村艺人,利用其对旧的民间艺术形式的娴熟掌握,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旧形式中植入新内容,使其与党的革命思想相结合,与战时中心任务相一致。在边区文教会对南仓社火艺人刘志仁介绍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艺人是如何做到“旧瓶装新酒”的,“在耍故事方面,他不满足于耍旧的故事,四〇年初,看到新宁完小演《中国魂》《五里坡》,就用当地故事摆了当中的一段,后来将《反徐州》也用马故事摆了一段。”当地民众在看了演出之后,发出感叹:“南仓是扎日鬼的?故事也能摆新的,真是能出了能人啦。”[37]不仅是“耍故事”,乡村艺人对旧形式的利用还表现为对传统民歌的改造。民间歌手汪庭有以传统民歌《绣荷包》的曲调为蓝本,重新填词,将其改编为革命民歌《十绣金匾》。经过改编,新歌祛除了原曲缠绵悱恻、倾诉悲苦的情绪,融入了歌颂领袖、热爱生活的革命情感。艾青曾动情地说:“从汪庭有的这个《十绣金匾》歌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劳动人民对于革命领袖、革命政权、革命部队、革命根据地最纯真的爱,和对劳动生产的热情。”[38]经过乡村艺人的改编,不合时宜的封建观念与反动思想被驱除,旧故事被换成新题材,抗战、生产、革命等成为新的叙事主题,真正实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要求。
事实上,鼓励乡村艺人对旧文艺形式和旧文艺作品进行改造,只是基于旧文艺“叙事”的主题替换,还不是彻底的革命性改造,还没有实现真正的革命文艺新创造。从革命的新要求出发,新编具有革命价值观的新艺术,才是新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与实现革命文艺创造的新方向。正如李军全所说,“在中共看来,改造旧剧只是一个替换价值主题的过程,编演新剧则是对旧剧历史观的一种抛弃和革命历史观的一种建构。”[39]1942年,太行人民剧团在刘伯承五十寿诞庆祝会上表演了《劝荣花》《换脑筋》等新编现实剧,1944年又改编创作了新剧《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此外还创作演出了《送夫上前线》《三更放哨》《生产计划》等新剧。该剧团在创作新剧、表演新剧上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和热烈赞许,剧团成员韩德山因扮演《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被群众誉为“活有才”。为此,彭德怀题词“抗日农村剧团的模范”,薄一波也给剧团赠送了“农村剧团的旗帜”的奖旗。王聪文领导的太南胜利剧团也是积极吸收改造旧艺人、编演新剧目的楷模,尤其是在上党艺人段二淼加入剧团后,更是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革命新剧,如《看护所》《大战神头岭》《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较之旧剧的改编,新剧创作无疑是更为彻底的文艺改造。大量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与展演,不仅给文艺动员积累了新素材,也给传统乡村社会带来了可以预见的革命文化冲击。
(四) 革命乡村的构建
“文艺新人”们或借助旧形式融入新内容,或是直接跳出旧框框创作新作品,均致力于营造一种全民革命、全员生产的热烈氛围。而这种热烈的革命气氛一定会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强化民众对革命的认同与支持,调动民众拥护革命、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在乡村社会构建起生机勃勃的革命地理空间。乡村艺人的创作与表演在乡村民众动员中主要发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改造了民众思想,实现了民众的革命认同。正如《文艺杂志》评论的那样,新艺人的革命创演改造了一批人:“在演出后,曾经感动了二流子李壮,后来他转变的很好……附近各村都知道他们会演二流子转变,都来要求去演……。”[40]至此,新艺人的革命创演就不再只是一种娱乐,除了革命动员的新功能之外,还成为对乡村民众进行革命改造的有效载体。其中,道蓬菴农村剧团动员回乡战士归队的故事,可为此提供又一证明:“到战士家里,请战士出来与他们一起享受民众的慰劳。在吃饭中他们鼓励战士归队。终于在几天以后,这位战士因感动而回队伍上去了,临走时战士说‘不打败反动军我不回来!’”[40]无论是“二流子”被感动变好,还是回乡战士被劝说归队,他们的思想转变都与乡村艺人的文艺展演有着直接关系。“文艺新人”通过文艺演出活动,以发生在民众身边的故事的展演,帮助民众对人民革命的理解,并在其内心深处形成“革命光荣,懒惰可耻”的价值判断,进而认同、支持、参加革命和生产。其二,乡村艺人围绕革命中心工作开展创作与表演,服务于抗战、生产等现实任务。由襄垣农村剧团创作的《劝荣花》就是抗战后期流传较广的现实题材剧,剧中讲述了妇女主任动员妇女荣花参加生产劳动、维护家庭和睦的故事。阳城固隆农村剧团也在当地表演了这一作品,演员李翠仙曾在该剧中出演妇女主任的角色。在参演该剧后,她本人就深受教育,改掉了爱和丈夫吵闹、不喜欢参加劳动的毛病,主动下地干活、回家纺线织布,后来被太岳行署授予“模范演员”荣誉称号。她深有感触地说:“咱自家都不行,怎能去劝人?荣花能改过,咱为啥不能改过?”[41]发生在演员李翠仙身上的故事表明,乡村艺人通过新剧演出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教育,进一步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自己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进而更为自觉地做好革命宣传鼓动工作。
动员乡村民众拥军也是党的民众动员的基本任务之一,乡村艺人编演的新剧即包含反映这一工作的内容;同时,他们的新剧展演也教育了乡村群众,使根据地到处都是“拥军村”,推动了拥军工作在乡村的开展。如,乡村艺人创作排演了拥军题材剧《招待所》。此剧演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连看庙的僧人刘心玉观看该剧后都激动地说:“咱从前烧香,把命都烧了,现在八路军又救咱的命,拥军可比烧香好得太多了!”[42](79)僧人刘心玉的思想转变更加说明了乡村艺人编演新剧对民众思想的重要影响。不仅是新戏剧,说书艺人韩起祥说的新书,也在乡村的拥军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杨家窑子有一个姓刘的农民,听了韩起祥说到的四虎的故事,很受感动,马上叫他的老婆做了一双鞋子,送到前线给刘四虎。”[26]这些事例都是很好的说明。
综上,中国共产党对乡村艺人的改造是党依据自身政治传播和革命动员需要、形塑乡村艺人体魄与思想观念的过程,也是乡村艺人适应革命发展、平衡传统艺术形式与革命新内容、新精神的过程,更是文艺新人创建革命文艺、民众革命动员的过程。在乡村艺人改造的政治实践中,通过身体重塑、情感认同、展演规范、榜样示范等,实现了乡村艺人政治立场的根本性转变。随着改造的深入,民间艺人主动突破旧思想的束缚,或改造传统民间文艺,或创造新的文艺作品,“以文载道”,将革命思想融入其中,使传统民间文化服从并服务于革命宣传与政治动员,实现了传统文化与革命动员的有机结合。经过对乡村艺人的改造,革命意识形态强力介入乡村艺人的创演活动,并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其日常生活之中,达到了艺术性与人民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对乡村民众的政治教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中国文艺作品审美中,艺术性、革命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直得以强调,并在强调中不断升华,追根溯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党领导下的基于民众动员的民间文艺改造运动的深远历史影响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