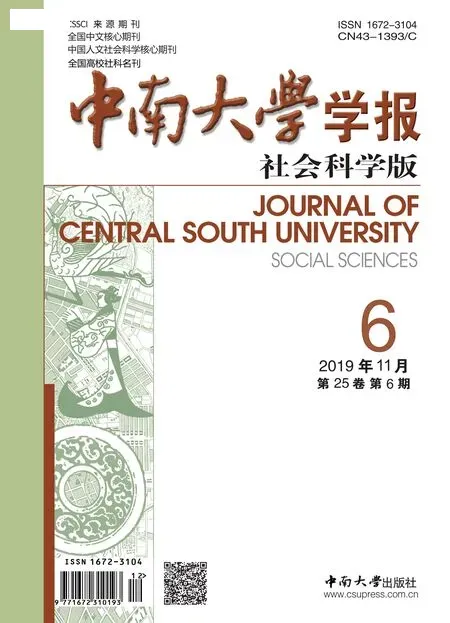《子虚》《上林》赋的经典化及历史经验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班固《两都赋序》论西汉赋作之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1](21-22)他所列举的赋家,后来有哪位及其作品成为经典?人们毫无疑问地指向位列第一的司马相如。“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2](2376),自是定论。其原因何在?本文探讨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经典化历程,以求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历史经验。
一、“以讽谏为歌颂”奠定了大赋的文体地位而被历代认同
读者对《子虚》《上林》赋的第一印象,在于它的歌颂品德。大赋自司马相如发展至今,歌功颂德作为大赋文体的精髓或精神内涵,一直没有改变,这是世所公认的。但是,大赋的歌颂品德是有着特殊的表述的。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子虚》《上林》赋的创作缘起: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3](3002)
一般认为,《子虚》《上林》赋,合则为《天子游猎赋》。《子虚》《上林》赋问世,虽然迎合了汉武帝的欢心,但争议也产生了,在《史记·司马相如传》篇末,司马迁既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又说“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讽)谏”,这就是两种评价。扬雄《法言·吾子》记载,扬雄回答“赋可以讽乎”:“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4](6)《汉书》称“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5](2609),批评司马相如的赋作没有尽到讽谏之责。《汉书·艺文志》说司马相如诸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讽)谕之义”[5](1756)。争议可说是由《子虚》《上林》赋而起,而越有争议越易引起世人关注,我们来看《子虚》《上林》赋中讽谕的实际情况。
何谓“讽谕”?即用委婉的言语进行批评。《子虚》《上林》赋[1](119-130)的讽谕,一是表现在亡是公对楚、齐的批评,“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称楚、齐未能尽诸侯的职责,又以游戏之乐与奢侈相比。我们注意到,此处的讽谕是面向诸侯而言。
《子虚》《上林》的讽谕,还表现在对田猎“奢侈”“靡丽”的批评,以及对田猎妨农与苑囿侵占农田的批评。《上林》记载:“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仔细读来,这段叙写自有其意味,所谓对田猎的“奢侈”“靡丽”的批评或“讽谕”,是天子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批评,而非臣下提出来的;所谓退猎还耕、退苑还农,是天子的主动行为,并非讽谕驱动,这是在歌颂天子。进而,赋中写道:“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完全是颂扬朝廷与天子的功德。因此,可以说《子虚》《上林》赋的讽谕,是“以讽谕为歌颂”,讽谕“田猎”行为而歌颂天子对“田猎”的自我认识及其采取的措施所取得的成效。
《子虚》《上林》赋的“以讽谕为歌颂”,主要还表现在对诸侯的讽谕以及对中央朝廷的歌颂。西汉前期,诸侯王势力十分强大,诸侯王与中央王朝力量对比有所谓“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之说。《子虚》《上林》赋通过描绘天子与齐王、楚王的田猎活动及政治活动,对比其间的高低优劣,借此抨击诸侯王,这是讽谏的指向,即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从而达到歌颂天子地位、巩固中央王朝统治的目的。
扬雄对汉大赋的“以讽谕为歌颂”有过批判性的总结论述:
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5](3575)
扬雄以《大人赋》为例,说明“风”是起点,“劝”是结果,以“风”达到了对天子的鼓励与歌颂。扬雄《长杨赋》,就是既有“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的讽谏,又重在“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的歌颂[1](138)。班固《两都赋序》对汉大赋“以讽谕为歌颂”是这样表述的:“或以抒下情以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即“抒下情而通讽谕”是手段,“宣上德而尽忠孝”是目的和效果。
所以汉大赋深得历代统治者的欢心,大赋也因此奠定了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来“宣上德而尽忠孝”式的歌功颂德,并历代有所延续。如唐代的律赋多歌功颂德,李调元《赋话·新话二》称“大约私试所作而播于行卷者,命题皆冠冕正大”[6](11),即是此意。马积高说:“宋代写典礼、宫殿、京都等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增加了。”[7](383)康熙、嘉庆年间,“学者们的著名作品多属铺陈军国大事、朝章国典的歌功颂德之作”,歌功颂德之作还“以馆试的律赋为多”[7](616)。赋歌功颂德,但其在歌功颂德时又有所讽谏,这种传统是由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而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大致不出“美刺”两端,历代朝廷都需要讽谏,更需要歌颂,“以讽谕为歌颂”,稳稳当当,自然既可作为大赋的象征符号,也可作为以大赋为代表的一类文学的象征符号。《子虚》《上林》赋“以讽谕为歌颂”不仅奠定了大赋的文体地位,而且奠定了大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
二、“以田猎为讲武”与后世的开放性叙写
《子虚》《上林》赋成为经典的另一因素,在于其对田猎文化作出了开放性叙写,以“讲武”适应时代需要,促进了田猎文化阐释的开放性,令后代赋作对田猎文化不断进行新的阐释,令田猎赋充满了生命力。
司马相如时代之前的田猎,一是指游艺。《老子》即称“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8](45-46),于是,“以田猎为游艺”往往成为讽谏对象。《尚书·无逸》:“文王不敢盘于游田。”[9](222)《晏子春秋·谏八》:“春夏起役,且游猎,夺民农时,国家空虚,不可。”[10](118)《诗经·齐风·还》小序:“《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11](349)司马相如前有枚乘《七发》,给太子讲校猎,虽然太子听了以后“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但校猎的游艺之乐并不能令太子健康,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要言妙道”[1](481)。二是指讲武。《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谈强国谋略,其中之一就是:“春以獀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12](153)明确地说就是以蒐、狝之类的狩猎来演练军队。《礼记·月令》则称“教于田猎,以习五 戎”[13](1379)。《小雅·车攻》写的是田猎之事,《诗序》曰:“《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11](428)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也有着充分的“以田猎为讲武”的叙写。《上林》叙写“背冬涉秋,天子校猎”,先是突出天子车马、仪仗之盛及将士出征与围猎的行程景象,“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叙写检阅围猎部队以及观览战利品的情况:“于是乘舆弥节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晻乎反乡。蹶石关,历封峦,过鳷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均猎者之所得获。”完全是把本次围猎看作某次作战的场景。
但“以田猎为讲武”本是远古的传统,当今的“以田猎为讲武”有什么意义呢?司马相如为什么要把围猎当作作战来写?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是王朝的重大威胁,汉武帝时,积极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汉元光二年(公元前133),“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入塞,觉之,走出。”[5](162-163)那么,武帝继位后读《子虚》赋而“大悦”,未必没有被赋中的讲武场面打动的因素;而司马相如赋作有无迎合朝廷为开战匈奴而积极准备的意味,不得而知;但其赋以阔大的场面、恢弘的气势来展示天子围猎的壮观,尤其是其中“跨野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等对骑兵的叙写,实际上是对应着与匈奴的作战。汉朝前期之所以不敌匈奴,就兵种来说,就是多车兵、步兵,汉武帝登基后,重点发展骑兵,这对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子虚》《上林》赋对田猎的开放性叙写,突出的是国家“文治武功”体制的“武功”方面,锋芒直指边境战争,这种指向虽然是隐性的却是可以让人感受得到的,而且历史事实是,征服匈奴的战争即将爆发。
扬雄《长杨赋》则直接叙说“以田猎为讲武”:“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这是对以田猎为讲武整军、选拔将士并以此震慑胡人的理性总结。赋中显示“讲武”的重要性时,历数武帝对匈奴及四境的征服,写道:“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旋。乃命骠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馁,莫不跷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1](135-139)这就直接说出了朝廷讲武的意义。司马相如的时代,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尚未大规模展开;扬雄的时代,汉朝击匈奴、征西域的战争已经取得了赫赫战功,扬雄的叙写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总结,这就是为什么扬雄写到了武帝对匈奴的征服而司马相如只是写到了以田猎为讲武的原因。
东汉的京都赋,几乎把田猎内容整体移植进来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因为讲武、武功对于歌颂王朝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田猎的意义就是耀武而威慑四方。班固《西都赋》叙写田猎活动“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东都赋》先写围猎讲武,“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铤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焰生风,喝野喷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按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申令三驱,车霆激,骁骑电惊”;再写取得的效果:“西荡河源,东澹海滣,北动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詟水憟,奔走而来宾。”[1](28-33)田猎“讲武”令四境来宾啊!张衡《东京赋》直写田猎与朝廷体 制的关系:“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1](62)田猎之“讲武”涉及朝廷的根本——文治武功,并以此来歌功颂德。因此,田猎的叙写实在是超越了题材自身而达到顶峰,而这一切又都是《子虚》《上林》赋所开创的。
《子虚》《上林》赋后代有所承袭,唐代有李白《大猎赋》,祝尧《古赋辨体》曰:“(《大猎》)与《子 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14](809)宋代丁谓有《大蒐赋》,其序曰:“司马相如、扬雄以赋名汉朝,后之学者多规范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读、袭征引,言语陈熟,无有己出。”[15](345)但又讲自己在丽则、庄重方面的创新。后世田猎赋呈多样化、多元性叙写趋势,承续《子虚》《上林》赋对田猎文化的开放性叙写,如《文选》赋“田猎”类,有西晋潘安仁(岳)《射雉赋》,把“射雉”作为“艺”来叙写;北周庾信有《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结尾以“惟观揖让之礼,盖取威雄之仪”[16](15),“礼”“仪”成为关注对象;唐代元稹《观兵部马射赋》记载“大司马以驰射而选材,众君子皆注目而观艺”,“岂独武人之利,实惟君子之争”等[17](145),强调文武双全。这些赋作对“讲武”的开放性叙写,从不同的方面弘扬了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以田猎为讲武”。
三、“以推类为巨衍”与大赋体式的确立
大赋的体制流行两千年,至今仍盛行,这个体制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奠定的。那么,司马相如之前的赋是什么样子的呢?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讲“命赋之厥初”时,大赋的体制已有基础,除“客主以首引”外,就是“极声貌以穷文”[18](270-277)。贾谊的时代是骚体赋,如其《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之类,赋句中带“兮”字的,也重在骚体所具有的抒情,故做不到“极声貌以穷文”。司马相如之前还有枚乘《七发》,虽然其叙写体式为以后很多赋家所采用,但由于其体式布局的凝固化,历来被认为是独立成体的。待司马相如被征召入京,他跟汉武帝说,《子虚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未足观”者,一为叙写的是诸侯之事,二为体量、体制还未达极致,于是司马相如作《天子游猎赋》,这就是汉大赋的体式。扬雄对司马相如创制的汉大赋的体式及内涵有过精准的概括,即“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此处的“推类”,即推而广之的叙说某类事物,达其“闳侈巨衍”,达其“竞于使人不能加也”之“极”。汉大赋的这个特点,也是有基础、有缘由的。赋在初创时期,宋玉就有《大言赋》《小言赋》,以楚襄王君臣讨论极“大”者、极“小”者发端,“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其中尤以宋玉所言极“大”之“壮士”骇人耳目:“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又:“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竕天,迫不得仰。”[19](107)从《大言赋》《小言赋》可知,一是世人有此讨论极“大”极“小”的风气,二是这种讨论是以赋体表达的。
《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的大赋创作是“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并记载其曾谈创作经验:“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20](91)这完全是指向其赋作的“闳侈巨衍”的。
扬雄极力鼓吹司马相如为汉大赋创定的体式。扬雄早年作赋,就以司马相如为榜样,“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5](3515),经其发扬光大的汉大赋体式成为后世的表率。扬雄又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21](49)扬雄称“丽以淫”,“淫”就是过分,就是“极”,如此之“极”,司马相如是第一人,“入室”者,即技艺得到师传,造诣高深。扬雄又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20](147)
扬雄是什么人?据桓谭《新论》记载: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22](62)据王充《论衡·超奇》记载:“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23](212)扬雄是被称为圣人、当代孔子的,司马相如及其赋作被这样的人赞赏,其名声当然是响当当的。其实,赞赏的作用是一时的,扬雄的赋作,以“推类”为方法,令赋的“闳侈巨衍”达到极致。
东汉时,司马相如及其赋作又受到班固的鼓吹,班固《两都赋序》称西汉的赋是从“武宣之世”算起,这就略去贾谊诸人,所列赋家以司马相如为首。班固的京都赋之类,囊括进田猎赋的内容,是对《子虚》《上林》赋的另一种仰慕与发扬光大。东汉中叶以后出现了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之类的作品,被称之为抒情小赋,虽然抒情小赋在后世大成气候,作品很多,但说起赋来,大赋仍旧为正宗,赋者仍以司马相如赋为表率。其原因既如北齐文人魏收提出的“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24](492),也在于人们赞赏韩愈所说的“读(韩)退之《南山诗》,颇觉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能到”[25],这就是所谓的“大”。《子虚》《上林》奠定了汉大赋的体制,提起汉大赋而必称《子虚》《上林》,写作大赋必以其为表率,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子虚》《上林》经典化的历史经验
《子虚》《上林》赋成为经典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其创立了“以讽谕为歌颂”的模式,经过一番争议与讨论,获得历代官方文学的认同,并被视为大赋文体的精髓。二是其“以田猎为讲武”的叙写策略,既适应时代的需要,又引发了后代田猎文化的拓展性叙写。三是其所奠定的“以推类为巨衍”的汉大赋体式,迎合了文人炫才与朝廷好大喜功的心理,并经著名文学家扬雄宣扬而被历代遵用。由此可知,《子虚》《上林》赋成为经典,虽有其自身的艺术魅力而被历代传诵的原因,也在于其所创制的内容表达与形式结构,被历代尊为表率。并且,其所创制的内容表达与形式结构具有开创性,后人以其为表率创作作品时可以有着极大的发挥。
外在的力量,如名人的推荐,朝廷的宣扬,选本总集的刊载等,只能让作品光彩于一时而不见得能长久。《子虚》《上林》赋成为经典,在于作品的内容与表达方式、艺术结构等方面的典范性、权威性,以及作品既获得其所在时代的盛誉,又留给后世发扬光大的空间。于此可见,《子虚》《上林》赋与杜甫诗歌的经典化路径不同,前者是以文体形态的开创者、为后世提供类型叙写的开放性而多有延续之作,以及创作手法的典范化而著称,后世承袭不断;而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则在于其艺术上的集大成,即元稹所言“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17](277-278),强调的是文体形态的完美性和创作成就的集大成。作品未成为经典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未得到历代读者的认同;而经典的养成却各有不同,各有其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的分析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