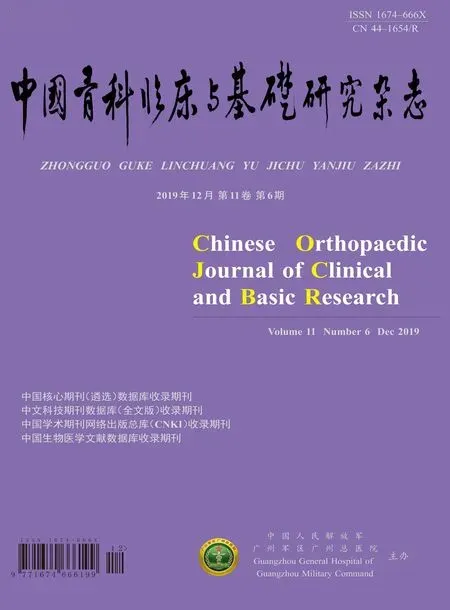电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研究进展
徐武岩,查丁胜,林 振,黄嘉文,吴 昊,林宏生,查振刚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是对称性多关节炎,以双手及腕、肘、足、踝和膝关节受累最为常见。病变关节腔内的滑膜组织可产生侵袭性血管翳,形成反复发作的滑膜炎症,引起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的破坏,造成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最终导致不同程度的残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1]。
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医疗模式的建立,医生关注的不仅是患者临床症状的改进,同时还注重对生活质量的改善,重视其心理健康。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电针广泛应用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肌腱炎、骨关节炎等骨科疾病的治疗与预防中,有良好的镇静、镇痛作用,有利于患者的功能康复[2-4]。而相关的机理研究则显示,电针治疗不仅能够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关节炎症反应,还能够促进关节滑膜及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进而达到治疗RA的作用[5-6]。现就近年来电针治疗RA的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1 RA的流行病学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RA发病率约为0.5%~1%,其中北欧和北美患病率为0.5%~1.1%,南欧为0.3%~0.1%,发展中国家为0.1%~0.5%[7-8];而在美国,北方较南方、城市较农村患病率明显上升,每年因RA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0亿美元[9]。在我国,RA患者约占总人口数的0.42%,人均经济负担高达15 717元,且每年都在递增[10]。
RA好发于女性,女性患病几率约为男性的3倍。该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发病高峰在30~50岁,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65岁以上女性最高[11-12]。RA的发生与遗传也密切相关,据报道,血清阳性RA的遗传率估计为40%~65%,而血清阴性约为20%[13]。
2 RA的治疗现状
RA至今尚无特效疗法,治疗仍停留于针对炎症及后遗症层面,目前的主要治疗方向是抑制炎症进展、改善关节功能,以达到缓解疼痛、预防畸形、提升生活质量的目的。
当前治疗药物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等。近年来随着对RA等免疫炎症疾病认识的逐渐加深,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拮抗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受体拮抗剂等生物制剂被批准用于临床[14]。但目前均不能完全治愈RA,对部分患者无效,口服药物也多具有依赖性、肝肾毒性和胃肠反应、骨质疏松、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无菌性骨坏死等副作用,某些药物治疗还存在易复发问题。物理治疗主要包括热疗、水疗、电疗、超声波疗法等,但只能适当改善临床症状,疗效并不确切。总之,寻找简便、有效的治疗方式,迅速缓解患者疼痛,改善受累关节功能及预后,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是目前RA治疗的重点和难点。
3 电针治疗RA的基础研究
3.1 电针对RA炎症反应的作用及机理
感染、遗传、内分泌、精神、免疫、营养不良等因素均有可能导致RA的发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主要以细胞免疫为主,先天免疫系统中的炎症细胞(包括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滑膜细胞的增殖分化并释放炎症介质,引发滑膜炎性反应,这一过程是RA持续进展、迁延不愈并最终导致骨破坏的关键环节[1,15]。大量证据表明,浸润在关节局部的炎症因子是RA关节损伤和炎症反应的重要介质,其参与RA的整个病理过程,是引起RA滑膜炎症的重要原因[16-17]。而细胞因子的表达和释放又受多种因素的调控,其中以血清核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为主的信号通路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18-19]。
3.1.1 电针治疗与炎症因子TNF-α是一种重要的生理性炎症介质,在介导宿主炎症反应、引起组织损伤方面起重要作用,是RA众多炎性细胞因子中最活跃的因子之一,主要由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分泌产生。新生血管形成被认为是形成和维持RA血管翳的一个重要因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新生血管形成的关键调控因素[20]。高洁等[21]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电针治疗可有效降低胶原诱导性关节炎(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CIA)大鼠外周血和关节液中TNF-α、VEGF水平,关节炎指数明显改善;王振宇等[22]的研究结果则表明,经穴预刺激能够显著降低关节炎模型大鼠血清中的TNF-α水平,抑制下丘脑中TNF-αmRNA表达,进而证实电针治疗具有良性预刺激效应。
IL-1属于Th1型致炎细胞因子,与RA滑膜细胞的增生、血管翳形成及骨质破坏密切相关。细胞间黏附分子(intercellular adhension molecule,ICAM)-1是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和巨噬细胞抗原复合物-1的配体,属于整合素家族,能够介导免疫反应过程中多种细胞间的相互作用。IL-1在某些病理情况下的组织或血清水平不同程度升高,可促进T细胞活化和迁移,是参与关节炎病程的重要分子。有学者将CIA大鼠分为正常组、模型组、泼尼松组和电针组,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经电针和泼尼松治疗后大鼠踝直径和血清TNF-α、IL-1β、ICAM-1含量均明显降低,电针组与泼尼松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3]。在李翠芳等[24]的研究中,电针配合穴位注射骨瓜提取物治疗大耳白兔后,其关节腔内IL-1β和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含量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关节肿胀减轻。
总之,电针治疗可通过影响体内多种炎症因子的分泌,减少抗原对病灶所造成的炎症刺激,缓解组织及血清内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减轻局部炎症反应,进而抑制炎症刺激所引起的局部血管增生及关节滑膜细胞增殖,改善关节炎症状。
3.1.2 电针治疗与信号通路TNF-α具有诱导NF-κB信号通路活化的作用。滑膜细胞受TNF-α刺激后,NF-κB p65在细胞核中表达增多,在胞质中表达减少,进而参与对炎性反应过程中多种细胞因子和ICAM表达的调控过程。TNF-α转换酶(TNF-αconverting enzyme,TACE)是TNF-α经膜结合前体转化为可溶性TNF-α必不可少的催化酶,可以裂解ICAM-1,使血管内皮细胞间隙变大,因此在白细胞聚集和渗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李佳等[25]研究发现,电针组CIA大鼠较模型组血沉、C反应蛋白、类风湿因子等炎症指标明显降低,滑膜组织中TACE及NF-κB通路蛋白表达均下降,TACE/NF-κB通路被抑制,因而推测TACE/NF-κB通路可能是介导RA的一个重要的信号通路。Dong等[26]构建佐剂性关节炎(adjuvant arthritis,AA)大鼠模型,采用电针刺激足三里和昆仑穴28 d,电针组踝关节组织中髓样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及NF-κB在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均下降,提示电针调节细胞因子的作用与抑制滑膜组织MYD88-TLR4-NF-κB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有关。
除了NF-κB转录因子之外,电针调节炎症因子表达的作用可能还与其他信号通路有关。祝骥等[27]运用蛋白质组学方法分析电针治疗前后关节炎大鼠滑膜蛋白质组的变化,结果发现20余种蛋白表达的改变,其中GTP酶(GTPase)、色氨酸、WDR蛋白表达量在电针治疗后均降低。GTPase是一种小分子G蛋白,与GTP结合后可调节细胞信号的转导途径。WDR蛋白是含有多个保守WD基序的蛋白质,与G蛋白介导的信号转导相关。GTPase及WDR蛋白可能通过调节G蛋白的信号通路,抑制滑膜细胞增生及炎症,从而缓解RA的症状。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有显著的免疫抑制作用,其受体也是G蛋白偶联受体。在肖阳等[28]的AA大鼠模型研究中,电针针刺环跳穴、阳陵泉穴可活化G蛋白偶联受体介导的信号通路,促使定向迁移至炎性病灶的免疫细胞合成并释放CRH,大鼠关节局部CRH表达水平显著提高,大鼠运动功能得到改善。
3.1.3 电针治疗与神经递质 电针治疗不仅可以调控体内多种炎症因子的分泌,抑制相关信号通路的异常活化,还可能通过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进一步介导RA的发生发展。朱骏等[29]研究发现,电针治疗可显著提高CIA大鼠滑膜组织中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含量,上调IL-4表达,抑制干扰素-γ水平,而加用VIP受体拮抗剂后,其作用消失,表明电针抗炎作用与VIP介导的抗炎机制具有显著相关性。
3.2 电针的镇痛作用及机理
电针的镇痛效果在临床上已被广泛证实,但其确切机制仍有待研究,目前认为可能通过外周与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邢立莹等[30]的研究显示,电针针刺足三里、环跳穴20 d后,电针组AA大鼠较模型组大鼠痛阈显著提高,考虑电针可能通过抑制组胺等致痛物质释放或拮抗相关受体活性来达到镇痛效果。Goldman等[31]将小鼠分为正常组及腺苷A1受体基因敲除组,两组小鼠均于足三里穴局部应用腺苷A1受体激动剂或给予针刺,结果发现正常小鼠足三里穴位局部腺苷含量明显增高,痛阈显著升高,而对于腺苷A1受体基因敲除小鼠则无效,说明针刺可能通过机体局部释放腺苷并作用于腺苷A1受体而发挥镇痛作用。在韩晶等[32]的研究中,与模型组AA大鼠相比,电针组针刺大鼠右侧L3、L5夹脊穴后下丘脑和脊髓组织中腺苷A1受体活性增加,腺苷A1受体mRNA表达上调,痛阈明显提高,提示电针可通过激活受RA炎症刺激而被抑制的腺苷A1受体,促进内源性腺苷或腺苷A1受体激动剂与之结合,影响介导疼痛的信息传递,从而起到一定的镇痛抗炎作用。
亦有研究认为电针镇痛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内源性阿片肽而实现的[33]。以β-内啡肽(endorphin,EP)为代表的内源性阿片肽对疼痛感受起重要的调节作用,它可以抑制感觉传导递质P物质的释放,而电针可促进下丘脑和脊髓β-EP的合成与释放,明显提高镇痛作用。张皓等[34]发现,电针刺激夹脊穴可显著提高AA大鼠痛阈,且下丘脑、脊髓的β-EP含量明显上升。在蒋永亮等[35]的研究中,电针组CIA大鼠予双侧“足三里”、“昆仑”穴针刺治疗10 d,放射免疫法检测到滑膜内有大量β-EP分泌,证实电针可发挥抗炎和上调滑膜β-EP表达水平等作用,镇痛效果显著。
4 电针治疗RA的临床研究
4.1 电针治疗在调控炎症因子和相关信号通路方面的优势
如前所述,细胞因子被认为是参与RA免疫炎性反应的重要介质,与RA的发生发展、治疗预后均密切相关;信号通路在RA发病中也起到关键性作用,不仅影响细胞的增殖和凋亡,还能介导多种炎症因子的释放。诸多临床研究也证实,电针在调控炎症细胞因子及相关信号通路方面均具有独特优势。
欧阳八四等[36]在取穴、针法均相同的条件下,治疗组在阿是穴处加用电针,对照组单纯针刺治疗,结果表明电针能有效降低RA患者外周血和关节滑液中促炎性IL-1、IL-6的含量,提高IL-4、IL-10含量,减轻滑膜炎性反应,减缓关节结构破坏进程。随后,该课题组将活动性RA患者随机分为电针组与单纯针刺对照组,取穴以阳经为主并配以阿是穴,结果显示,电针组对关节滑液中TNF-α的改善作用与单纯针刺组相似,但在外周血中的改善作用优于后者,治疗后外周血和关节滑液中VEGF水平降低,电针组效应均优于单纯针刺组;这一结果提示,电针治疗可降低TNF-α和VEGF水平,减轻炎性介质引起的关节滑膜炎症反应,进而缓解RA患者的临床症状,特别是炎症反应后的疼痛和肿胀症状,这对提高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都至关重要[37-38]。王晔[39]将68例RA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予电针联合扶正祛邪方治疗,治疗3个月后观察组中医证候评分、疾病活动评分(disease activity score,DAS)28、生活质量评分以及血清TNF-α、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SIL-2R)水平改善情况及总有效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表明电针联合方剂可能通过抑制SIL-2R水平,达到阻断IL-2生物学效应的目的,进而有效抑制RA患者体内炎症反应,降低疾病活动度,缓解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抑制NF-κB信号途径的激活对RA治疗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明荷等[40]将140例RA患者分为电针组及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电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电针治疗,2个月后两组患者症状均有所改善,电针组NF-κB、TNF-α和IL-1β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4.2 治疗效果
电针治疗充分运用传统医学的经验,根据中医“筋痹”的治疗原则,选取相应穴位进行针刺。该方法将毫针与电流相结合,在普通针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的基础上加强了对穴位的刺激,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它还具有操作简便、费用低廉、无明显不良反应等优点。鉴于针刺阳明经穴能激发人体经气,调气活血,而电针可加强刺激,增强疗效,徐萍等[41]选取92例RA患者作为受试对象,电针组采用电针刺激阳明经穴,对照组采用单纯针刺治疗,结果表明,电针组在关节疼痛、关节肿胀、关节压痛、晨僵时间等方面的改善幅度较对照组更加显著。贾爽杰[42]的临床研究亦显示,对于活动性RA患者,电针配合中药离子导入治疗可有效降低血沉、C反应蛋白等炎症指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治疗总体效果优于单纯针灸。
电针治疗不仅能改善关节功能、控制病情进展,而且能够显著降低DAS28,拮抗药物的不良反应。周殷等[43]将68例肝肾阴虚型RA患者随机分为电针加西药组及单纯西药组,12周治疗后电针加西药组在缓解休息痛、关节肿胀数和压痛数、中医证候评分等方面均优于单纯西药组。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设置电针联合中医药组及单纯西药组,同样得出类似的结论[44]。欧阳八四等[45]将RA患者分为电针组与单纯针刺组,2组整体取穴均以阳经为主,局部取穴遵循“以痛为腧”原则,治疗后发现电针组达到ACR20的患者明显高于针刺组,疼痛评分明显降低,患者生存质量显著提高。
4.3 技术要点
4.3.1 穴位选择 应根据病症选取适当腧穴或治疗部位。选择规律:按电流回路要求,选穴宜成对,以1~3对(2~6个穴位)为宜,当选择单个腧穴进行治疗时,应使用无关电极。
4.3.2 电针操作[46]①应避免快速反复提插,尤其在血管较少的非常见韧带和肌腱处,以减少软组织血管破裂,避免组织进一步受损。②电针操作过程中直接使用脉冲电通入人体,其安全使用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和流程。如严禁电流直接流经心脏,不允许双上肢左右两个穴位同时接受一路输出治疗;在靠近延脑、脊髓等部位使用电针时,电流量不宜过大,注意电流回路不要横跨中枢神经系统,刺激不可过强等。③严格把握电针使用的禁忌证,如皮损、肿瘤局部或安装心脏起搏器;过敏体质及已知对针灸、电针治疗不耐受者;患有出血性疾病或难以控制的凝血障碍等。
5 小结
目前对RA的治疗尚停留在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延缓关节畸形及关节破坏进程的阶段,无法达到根治效果。作为传统的非药物治疗方法,电针治疗主要通过影响体内多种炎症因子的分泌,抑制NF-κB等信号通路的异常活化,提高β-EP等内源性阿片肽的释放等,发挥抗炎镇痛和免疫调节效用。诸多临床研究亦证实,应用电针治疗可有效控制RA炎症反应,减轻疼痛症状,改善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尽管电针治疗RA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缺乏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同时少有报道明确提出针刺手法的具体标准,在电针频率、波形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欠缺。而RA的发病机制是多元的、复杂的,电针的治疗机制也是多靶点、多途径的,今后应尽量摆脱单靶点、单分子的研究模式,深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以阐明电针治疗RA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