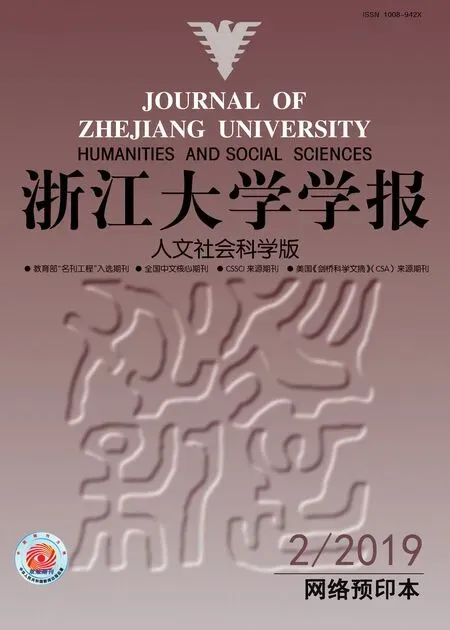论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
高 奋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翻译引进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文献和文论,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一发展既体现在成果数量和质量上的提升,也体现在国际化倾向的增强上。从新批评、形式主义、神话原型、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族裔批评、生态批评、空间批评、幽灵批评等,我们在文艺理论、批评方法、批评问题等多个方面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研究成果。虽然经济和信息全球化正在消融民族和国家的边界,网络和金融科技全球化助推了人类生活方式的趋同倾向,但是当前的文化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依然体现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单向输出和普及化的特征,其后果可能导致非西方文化体系的萎缩。真正的文化全球化应该是多民族和多国家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在多元交流和碰撞中推进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同步发展。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同样需要解决单向度全球化问题。
21世纪以来,学者们不断回顾和反思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在肯定借鉴的必要性的同时,强调要“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1]13,提出要“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2]13。学界现有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成就回顾和问题反思上,对今后的走向尚需更多的讨论。本文将在比照中西思想异同的基础上,就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一、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立场的主要特性是对本国文化的高度自信和高度自觉。它的核心精神可用鲁迅的“汉唐气魄”来概括:“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3]198这一立场坚信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既不是被动移植,也不是有限选择,而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自由取舍和运用所需文化资源。在根源上,它以强盛的国力和高度的自信为基础;在本质上,它强调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坚信跨文化、跨民族的对话是思想创新的源泉;在举措上,它以中西互鉴为先决条件,坚持从本民族的问题、思想和方法出发,“对其他文化形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4]136。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所实践的是“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从本民族最本源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点出发,审视、观照国外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实现中华思想的转型[5]25。
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将印度佛教的禅改造为中国禅宗的过程是充分体现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的范例。印度禅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学者们以道家学说对佛教禅进行诠释式、整合式、扩容式的创造性翻译,用老庄思想改造印度禅,将以“禅定”为中心的印度禅改造为以“慧的意境”为中心的中国禅宗,将印度禅对佛的崇拜和对西方净土的追求改写为中国禅宗对内在自性的觉悟。这一创造性翻译既保留了印度禅的宗旨,又使老庄思想重新崛起,以两种思想的融合,为文明创新提供了范本[5]25。诚如学者所言:“禅宗之禅,是中国僧人和学者,借助创造性翻译,而实现的创造性思维。它建立的基础是中国的庄、老,而不是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是借佛教之躯,而赋庄、老之魂。它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建立在对自心体认基础上的辩证思维。”[6]2
40年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走过了翻译引进外国作品、文献、文论和方法,以及充分运用西方文论和方法的两个基础阶段,目前正处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我们要坚持以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为原则,即以中国思维为主导,中西思想为参照,对外国文学进行创新性研究。遵循这一基本原则,我们能够拥有并保持面向世界的视野。我们要重视以下两点:
一是以中国思维为主导。中西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都做了深入论述。近百年来,由于西方书籍的大量翻译、引进和传播,中国外国文学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的“概念思维”,但可能疏忽了中华民族的“象思维”。我们需要明晰两者的差异,以突显本民族思维的主导作用。西方“概念思维”的“首要特征是抽象性,即把思维对象从具体的感性现实中抽象出来,并以下定义的方式加以严格规定”[7]47。这是由柏拉图概括和提炼的,是一种让概念的抽象普遍性超越并凌驾于事物的具象特殊性之上的思维模式,它的核心原则是本质/现象、主观/客观等抽象概念与感性事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中国的“象思维”则“不对现象作定格、分割和抽取,而是要尽量保持现象的整体性、丰富性与动态性”。“它不是要到现象的背后去寻找稳定性和规律,而是要在现象的自身之中找到稳定性和规律。它也对事物进行概括,发现事物的普遍性,但始终不离开现象层面。概括的结果,仍以‘象’的形式出现。”[7]46它以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具有整体性、关联性、互补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以中国思维为主导,我们的整体思维不仅可以避免西方思维的二元对立和概念先导的局限,而且可以克服西方思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充分发挥中国学者擅长领悟的天性,释放我们的创新能力。
二是重视中西贯通。中西贯通就是基于中国诗学的整体观照,辅以西方理论的科学分析,将“心”的感悟与“物”的解析结合起来,以贯通审美领悟与理性认知。中国传统批评的“心”悟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以生命体验为本质特性,实践“以意逆志”的审美方法,将文学纳入自然、文化、心灵中加以整体考察,从文学的内在关联性、互补性和动态性中领悟其生命洞见。西方文学批评对文学的“物”析体现在西方著名文论家乔纳森·卡勒所归纳的两种主导批评模式——语言学模式和阐释学模式[8]61中,前者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修辞学研究,重在揭示文学作品的内在形式构成,比如情节、人物、主题、象征、反讽等基本成分和修辞手法;后者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性别、生态、空间等外在视角出发,运用特定理论去解析文学的内涵。这两种模式都将文学视为感性之“物”,用理性分析去提炼普遍概念。中西贯通的目标在于将整体生命观照与精细理性分析相结合,以达到思想的深刻性与论析的严谨性的融合。老一辈思想家、批评家钱锺书、朱光潜等早已提供了中西贯通的研究范例,下文将进行细致的实例分析。
二、强化外国文学批评的审美导向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批评立场,就需要确立以本民族的思维和诗学为基础和主干的批评导向,同时学习并自主运用西方文论。充分对比中西批评的特性、优势与局限,有益于我们构建自主的、创新的外国文学批评导向。
西方现当代主导的文学批评具有显著的理论先导的特性。形式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混沌理论、生态主义、空间理论等各种理论轮番上阵,它们的频繁建构/解构主宰了文学批评的短暂兴衰和快速更替。在理论繁荣之下,文学批评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渐渐湮没于政治、文化和科学理论之中。西方学者不断发出“回归文学本身”的呼吁,但是根深蒂固的本质/现象二元对立假说和“定义—分析”[9]132研究法则,依然促使西方学界将文学批评依附于不断涌现的新理论。不绝于耳的“回归文学本身”的呼声本身便昭示了这样的事实:在西方主导的批评理论和方法之下涌动着一种传统的、被忽视的批评模式。
也就是说,除了乔纳森·卡勒所归纳的语言学和解释学这两种显在的批评模式之外,还有另一种隐在的批评模式。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集》(AGlossaryofLiteraryTerms)中曾将实践性批评分为两类:明断式批评和印象式批评。前者类似于卡勒所指称的有预设标准的批评模式,它“不单单与作品进行交流,而且将批评家的个人判断依附于特定的文学准则,从主题、谋篇布局、技巧和风格等切入,分析和阐释一部作品的效果”[10]51;后者类似于普通读者的阅读模式,“力图阐明对特定段落或整部作品的感受,阐明作品在批评家心中激起的反应(印象)”[10]50。
如果将艾布拉姆斯的明断式批评和印象式批评向前推进到本质层面,可概括出西方批评的两种基本类型:认识性批评和审美性批评。
认识性批评是西方现当代批评的主导模式。它指称这样一类批评:它用一种特定的认识(理论)来预设批评的原则、视角、方法和目标,旨在以理性分析作品来提取概念或佐证认识(理论);该批评所遵从的认识(理论)通常已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确的术语、定义、思想内涵、功用,有一定的影响力。它的主要特征有五:(1)理论(概念、定义)先导。(2)视文学为现实的模仿:要么视作品为介入现实的实践话语,通过批评揭示作品对政治、性别、种族、文化等现实问题的态度、观点,或视作品为反映现实的镜子,用批评展开社会、文化、历史考证(解释学模式);要么依照语言学理论剖析作品的内在构成和创作技法(语言学模式)。(3)赋予批评居高临下的权威地位,按照理论准则和假说对作品进行定位、分类、剖析、考证、解释和提炼,文学只是批评的附庸。(4)依据选定的理论和术语框定有限的批评视角,很少去感悟和品味作品本身。(5)研究结论与理论假说一致。比如洛伊斯·泰森的一篇论文开篇便阐明:“我想通过茨维坦·托多洛夫的主题句模式来阐明该小说的叙事‘语法’……根据这个框架去找出文本是如何通过重复出现的行动(类似动词)与特征(类似形容词)和相关的特定人物(类似名词)之间形成的关系模式来建立起来的……我认为所有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三个动词:‘寻找’、‘找到’和‘失去’。”[11]12全文细致严谨地分析了小说中的“寻找—找到—失去”结构,最后的结论与开篇的预设一致。我们所概括的几个特性在此文中全都展现。这是一种严谨的研究方式,其假说明晰,视角和方法明确,分析细致,逻辑严密,将特定理论运用于作品分析中,可看到作品中先前看不到的东西。
不过认识性批评也有其局限。一是缺乏自主活力:依托特定理论,一旦理论过时,批评也过气。如果理论狭隘,批评则显得怪异。二是以偏概全:作品没有获得整体解读,而是聚焦某预设的选题,容易导致误读或过度阐释。三是不可持续性:批评家受制于理论,既不整体领悟作品的情感思想,也不运用自己的情感与想象。批评更像一种呆板的验证,而不是心灵的交流。批评时常不能揭示作品最深刻的思想,也不能体现批评家的深刻感悟,理论的艰涩常常体现在批评中。
其实,优秀的批评家即便从某种理论出发,也不会受制于该理论。他们仅仅将理论作为跳板,始终将重心落在生命感悟、人性洞见和心灵冲突之上。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第7章“《达罗卫夫人》——使死者复生的重复”便是范例,该章围绕着米勒本人原创的“重复”理论展开,但真正使他的评论熠熠发光、充满活力的是他对伍尔夫作品中“心灵与心灵之间关系的微妙差别”[12]54的极为深刻、极具穿透力的论析。在这里,重复理论只是平台,批评所揭示的是一位批评家透视小说家的作品所领悟的心灵奥秘。
审美性批评是指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作品的情感思想的批评。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印象式批评就是典型的审美批评。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批评,在现当代批评中常常受轻视、被边缘化,其经典评论见于蒙田的《随笔集》、维克多·雨果的《论莎士比亚》、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演讲录》、保罗·瓦莱里的《达·芬奇方法引论》、瓦尔特·佩特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等诗人和小说家的评论中。自觉的审美批评在西方的历史不算长。“审美”(aesthetic)一词取自拉丁语,原意为“感性学”,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第一次使用该术语,将其定义为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13]导论。此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阐明了美“不带任何利害”“普遍性愉悦”“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共通感”四大契机[14]37-76,为审美批评在西方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1818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将康德的观点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相结合,阐明了审美批评的内涵:“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如果不把他自己放在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俯视全体”,他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我们只有“将那种与一切环境无关的人类本性中那些真实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品的精神与实质”,在鉴赏过程中考察人类不朽的灵魂与“时代、地点和当时的生活习俗”等外在因素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批评的实质。我们易犯的错误是,“仅仅将环境作为不朽的东西,而完全忽略了那唯一能使环境活跃起来的灵魂的力量”[15]227。1865年,马修·阿诺德提出了批评的无功利本质,指出批评的法则是“超然无执”[16]81,超越于社会、政治、党派等利益之上。1873年,唯美主义者瓦尔特·佩特倡导审美批评的目标是“最充分地表现美”[17]序言。1925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普通读者》,阐明审美批评的原则和步骤。以上大致构成西方审美批评的主要发展历程。
审美批评的特征是:(1)不带先入之见。将作品中的感性描写作为研究对象,感悟和品味其中的情感和思想。(2)视文学为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认为文学是“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的面前”,文学的目标是用这些事件和情节去探索人类的“天性”[18]5。(3)视批评与文学创作同源同质。批评就是批评家探索作品中灵魂的力量的过程。(4)不带任何功利性。(5)关注心灵与社会、文化、环境、时代等各种现实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批评的焦点始终是生命性情本身。
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演讲录》是审美性批评的范例。他相信一个批评家如果缺乏对人类心灵的洞悉,在认识心灵时没有孩童般的喜悦,那么不论他学识多高,他都不能读懂作品。基于这一认识,他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去阅读莎士比亚,认为《暴风雨》展现了人的想象之美,它去除了暴风雨的恐怖成分,用场景的和谐、女主人公的神圣气质、爱情的神圣性等展现了“人类天性的一切伟大的组成力量和冲动”[15]282。他认为要理解《哈姆雷特》主人公性格和行动的矛盾,就要从考察人类的心灵构造出发,去感悟人物在外部冲击与内在思想不平衡的状态中人性的犹豫、困惑和抉择[15]342-352。
弗吉尼亚·伍尔夫推进了柯氏的观点,阐明了审美批评的原则、过程、利器和准绳。她指出批评的原则是,“依照自己的直觉,运用自己的心智,得出自己的结论”,其过程是“鉴别纷繁的印象,将那些瞬息即逝的东西变成坚实和持久的东西”,所使用的利器是“想象力、洞察力和学识”,评判准绳是“趣味”[19]。也就是说,伍尔夫视批评为批评家运用自由精神表达独立见识的过程;他首先需消除先入之见,获得对作品的完整感受,然后在想象力、洞察力和学识的帮助下感悟作品的真义;批评的标准是批评家来自天性和学识的情趣。她的批评以作品是否揭示人物的性情为衡量标准,指出笛福的伟大在于“他的作品建立在对人性中虽不是最诱人却是最恒久的东西的领悟上”[20]104,称赞简·奥斯丁“赋予表面的和琐碎的生活场景以最持久的生命形式”[21]149,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揭示了“人性中正在沉睡的巨大激情”[22]168。诚如蒂博代所言,西方审美批评体现了“把自己置于作者的位置上,置于研究对象的观点上,用作品的精神来阅读作品”[23]122的特性,努力实践批评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情感思想交流,同时又保持足够的距离,从整体上领悟作品。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主导批评模式是审美批评。中国传统诗学认为文艺批评是一种审美体验,比如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前者为批评的前提,后者为批评的方法。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批评的前提是,批评者需了解作者的性格、情感思想、修养气质等(知人),同时需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风貌(论世)。批评的方法是“以意逆志”:“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也就是说,批评即心灵的对话,不要因为语句的表面意思而影响对作者的情感思想的理解,要以批评家之心意去求取诗人之心志,或者以古人之心意去求取古人之心志。孟子思想的哲学和伦理学基础是人性论和性善论,即人心是相通的,人的本性皆善。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春秋繁露·精华》),指出文艺批评并无定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明确了审美批评的自主性和多元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审美批评的“知音说”。首先他要求批评者“博观”,以六观方式整体观照文学作品:“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即形,则优劣见也。”[24]438也就是说,批评者要整体审视情感与文体、语言、创新意识、新奇与雅正、典故和声律。其次,他揭示批评与创作同源同质,皆由心而发,因而要以心观之:“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24]439也就是说,创作是观物→情动→辞发的过程,而批评则是观文→情动→妙悟的过程,两者殊途同归,所表现和领悟的都是人之情思和洞见。
此后的学者诗人围绕以意逆志、知音等审美批评核心思想,从多侧面扩展审美批评的范畴,比如兴会(批评的感发性)、美丑(批评的统一性)、趣味(批评的品味)、自然(批评的标准)等。同时,运用各种活泼的批评方式,比如:“文为活物”,一种用意象来评判作品的方式,如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等鲜活意象评点作品;“法须活法”,一种既符合法理又保持文章的活泼性的行文风格;“美在虚空”,一种虚实相生的批评方式;“眼照古人”,即借古人之事以表达自己之意[注]“文为活物”“法须活法”“美在虚空”“眼照古人”这四点是学者龚鹏程对中国传统批评法则的总结。详见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81页。。
中国审美批评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1)视批评的本质为生命体验:知音说、神与物游说。(2)视文学为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诗言志。(3)强调批评的整体观照原则:知人论世说、六观说。(4)视批评的基本方法为批评家与作品(作家)的心灵对话:以意逆志。(5)强调批评的多元性:诗无达诂。(6)推崇集整体性、关联性、互补性、动态性为一体的审美机制:兴会观、美丑观、趣味观、自然观。(7)倡导开放灵动的批评模式:文为活物、法须活法、美在虚空、眼照古人。
中国文学批评的渊源是汉儒讲论经义的章句(逐句分章释义)、训诂(解释经文字义)、条例(归纳原则)和魏晋以来受佛典疏义影响而形成的开题(讲解题意)和章段(章节段落),因此中国传统批评的目标是:既要从文字上领悟作者之用心(情理),又要从题目、章段中领悟作品的主旨和文辞之美。也就是说,批评的核心是情理和文辞,两者不可分割,情理为主,文辞为次,如刘勰所言:“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词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4]288要揭示情理与文采,以意逆志和整体观照是中国传统批评的主导方法与视野。
比如南朝钟嵘的《诗品》在评价诗人李陵时,用评语“文多凄怆,怨者之流”[25]1突显其诗的风格,同时还道出其诗风渊源、诗人生平,短短40余字,一气呵成,生动勾勒了李陵的诗作和性情的形神特质。又比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他首先在总序中阐明《水浒传》与《史记》的差异在于,前者“因文生事”,后者“以文运事”[26]001,表明他对文学的想象性与虚构性的认识。他将批评的重心置于人物性情与文采技法的评点上,揭示小说最精妙之处在于“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重点称颂李逵的“天真烂漫”、鲁智深的“心地厚实”[26]002等人物个性,以及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等创作技法。然后他用序一阐明作者之意,序二阐明题旨,序三阐明作者生平。接着摘录《宋史纲》《宋史目》相关史实以示对照。最后对每一章回做出总批和评注,详述篇章布局、人物关系、人物性情、章回关联、创作技法、文辞风采等,情理与文采合一,极为精妙。比如他在第26回总批盛赞小说以虚实相生法表现鲁智深之英武的精妙:“须知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绾激射,正复不定,断非一语所得尽赞耳。”[26]312
可见中西批评异中有同。西方主导的认识性批评与中国主导的审美性批评大相径庭,而西方边缘化的审美性批评与中国主导的审美性批评则本质相通。认识性批评与审美性批评的差异是本质性的:前者视批评对象为“物”,用理性去解析它,其目标在于探求并推导人类的普遍性法则;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理论假说,理性分析作品后,最终回到理论假说的验证或修正。后者视批评对象为“心”,用批评家之心领悟作品(作家)的心意,其目标在于获得生命体验的交流、共鸣和洞见;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批评家与作品(作家)生命感悟的交汇,整体观照作品后,最终道出生命真谛和艺术之美。在西方美学史上,学者们不断开展对理性缺陷的批判,比如维科用“诗性智慧”对抗笛卡儿几何学在诗学研究中的滥用,康德阐发“审美判断力”,尼采用“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合体为生命精神正名等。西方审美性批评与中国审美性批评的相通之处在于,两者均视批评为生命体验;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审美批评重在探索生命精神,强调用想象力、判断力与学识去感悟生命体验;中国审美批评同时关注生命情理的揭示和生命精神的形式表现,已经建立起神思、虚静、妙悟、虚实等创作范畴,情志、文质、意象、意境、气韵、形神等形式范畴和知音、美丑、趣味、风骨等批评范畴。
强化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审美导向,就是要以中国思维和中国传统诗学为基础和主干,在中西贯通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审美批评的前沿化和全球化转型。因而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坚持“诗言志”的文学观。视文学为生命精神的表达,以想象性和虚构性为主要特性,而不将文学依附于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和理性认识。(2)坚持“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视文学批评为不带先入之见的生命体验和洞察,而不让批评依仗理论的权威居高临下,视作品为批评的附庸。(3)强调“知人论世”“六观说”等整体观照批评视野。依据阅读体验来确定研究问题,依据研究所需自主地运用中西文论,从多侧面考察和领悟作品的情理和文采,关注文学内外诸因素的关联性、互补性、动态性,决不用理论来限定批评的议题、方法和目标。(4)强调“神与物游”的批评过程。使批评始于批评家与作品(作家)的生命感悟的交汇,整体观照作品后,最终抵达生命情理和作品文采的美的境界。
当我们用心去领悟和洞见外国文学作品中最具活力的心灵力量和艺术美,我们的批评才能更具创意和深度。
老一辈思想家、批评家早已提供中西贯通的研究范例。比如朱光潜在《诗的实质与形式》一文中以对话方式探讨实质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并未采用西方惯常的“定义—分析”模式,而是采用中国思维的整体性与关联性。他将实质具化为情感和思想,形式具化为语言,重点阐明情感、思想、语言之间的关系,不仅揭示西方传统的“实质说”与“形式说”的缺陷,而且指出西方现代理论家克罗齐的“艺术即形式、直觉即表现”理论的局限。他最终提出“实质形式一致说”,将实质与形式的关系提升到意境的高度[27]275-302。整个讨论包含中国诗学的情志说、言意说、文质说等多个诗学范畴,深刻而犀利。比如叶维廉在《史蒂文斯诗中的“物自性”》一文中,将中国道家美学“肯定物之为物的本然本样”的“物自性”观与西方柏拉图以来所坚持的“真理存在于超越具体真实世界的抽象本体世界里”的“物超越”观相比照,在此基础上评析史蒂文斯的诗歌,揭示其诗性美基于“物之为物自身具足”的观点[28]7-8。该批评融中西诗学、整体观照和细致分析为一体,精彩演绎了他自己对优秀批评家的界定:“一个完美的批评家必须要对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对诗人由感悟到表达之间所牵涉的许多美学上的问题有明晰的识见和掌握,不管你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辩证的程序。”[29]12
三、推进整体观照法,实现理论创新
从方法论上看,中国主导的审美性批评所运用的是整体观照法,而西方主导的认识性批评坚持“定义—分析”法。下面对比这两种方法,以阐明整体观照法的价值和意义。
“整体观照”是中国诗学的基本方法。“观”作为一种方法,指称用心灵去映照万物之“道”的审美体验方法。“观”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普遍采用的一种感知天地万物的方法,比如老子《道德经》通过观照万物来洞见生命之本质,所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认识生命和世界的方法,便是经典的整体观照法。唐宋之后,受佛教影响,取自佛经的“观照”成为中国审美感知的重要方式。其内涵与道家的“观”相同,强调观照主体用澄明心灵去洞见被观照事物的本质,使主体的生命精神与万物的本真相契合。它是一种生命体验,基本特征如下:
(1)其要旨有二:以主体为核心,从心灵出发,以直觉感悟事物;以物我合一方式感悟事物整体,获得对事物的生命精神的洞见。(2)其根基是中国的“象思维”。“象思维”的基本特性是用直觉洞见事物之本质,其思想以“象”的形式呈现。(3)其优势是重视整体性、关联性、互补性、动态性,能够洞见事物之核心;其弱点是不重分析,逻辑体系不强。
西方诗学始终视文学为“物”,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其基本方法长期承袭柏拉图在《斐德若——论修辞术》中提出的两大修辞法则:“头一个法则是统观全体,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概念下面,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使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可以一目了然”;“第二个法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剖析成各个部分”[9]132。我们暂且简称它为“定义—分析”法则。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便是这两大法则运用的典范,它从确定模仿说的定义出发,分析并阐明悲剧的类属、功能、构成、作用等。自西塞罗、贺拉斯至中世纪,西方理论和批评“一直被包括在修辞学的范畴内……修辞学对于诗艺的主导地位从来不曾受到质疑”[30]65。16、17世纪,文学研究与修辞学“结盟”[30]225。18、19世纪,西方文论和批评的研究对象从审美客体过渡到审美主体,文艺界对情感、想象、趣味的兴趣大增,然而修辞学始终与文学研究如影随形[30]512-570。20世纪的文艺研究突破文学学科的束缚,广泛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理论来研究文学,但是“定义—分析”的基本方法依然坚如磐石。“定义—分析”法的基本特征如下:
(1)其要旨有二:以某种(些)有影响力、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参照,用其中的定义为批评提供预设标准;对研究对象仔细分析(解),从中提取抽象概念,正如柏拉图所言,“除非把事物按照性质分成种类,然后把个别事例归纳成为一个普遍原则”,否则“就不能尽人力所能做到登峰造极”[9]144。(2)其基础是西方的“概念思维”。“概念思维”的要旨是从具象中归纳概念,并以定义严格规定它;依据定义分析“物”的结构、形态、性质及其运动规律。(3)其优势是逻辑推论,分析思辨强;其弱点是,从个别现象中提取的概念因样本极小,很可能不具备普遍性,却常常被视为普遍规律,因而以偏概全在所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通病。
显而易见,整体观照法所运用的“以心观心”之法与审美性批评所倡导的“以意逆志”方法本质相通。整体观照法可以有效推进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和走向世界。目前已经取得成效的中国批评理论创新大致有三种形态,都是基于整体观照法之上的成果。这三种创新方式是:
第一,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化。学者们整体观照和阐释中国古典文论,以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比如文道、情志、形神、言意、神思、物化、知音、意境、风骨、趣味等为经纬,承袭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基本理路,视野开阔,论析深入,博古通今,以现代人的学识阐明中国传统诗学的博大意蕴和价值。代表性著作包括: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2001)、朱良志的《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2005)、陈伯海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2006)、成复旺的《神与物游——中国传统审美之路》(2007)、胡经之和李健的《中国古典文艺学》(2006)、龚鹏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2008)等。
第二,以中西对话方式推进理论创新。学者们在整体观照和透彻理解西方特定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找出它们的局限,提出突破性观点,在中西对话的国际前沿平台上实现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由于西方理论的目标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普遍概念,其研究问题和观点通常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其批评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实用性的,大都停留在现实层面,很少推进到生命层面。而中国诗学的核心是生命,我们能够在整体观照和透彻把握的基础上,将西方文论推进到生命诗学层面,昭示其深层本质,实现批评理论的突破与创新。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中国批评理论创新的范例之一。在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他首先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从生物层面推进到生命层面,指出:“适者生存”只是人类获得“人的形式”的第一次生物选择,“真正让人把自己同兽性区分开来是通过伦理选择实现的”,是“伦理选择”使人类获得“人的本质”[31]35。这一原创性的“伦理选择”观已经获得中外学者的关注。以此为核心,他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禁忌、伦理两难、伦理线、伦理结等各侧面建构其整体思想,而且将批评中心从西方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和抽象概念推进到文学批评实践,论析从古希腊到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伦理困境和冲突,体现了以中西对话实现理论创新的途径的有效性。
第三,以方法论和批评视野的改变来推进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学者们旨在突破西方批评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并推进具有整体观照视野的世界主义、比较文学、跨文化阐释等方法,以促进开放、包容、对话的批评方法的创新。
1865年,马修·阿诺德为推进英国的文学批评曾指出:“对所有事物展开精神的自由运用,这个概念本身便是一种享受……它给一个民族的精神提供了基本的元素,倘若一个民族的精神缺少这些元素,无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补偿,终必由于营养不足而死亡……真正的批评,主要便是这种人性特质的运用;它服从于一种本能,这本能推动它去试图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已被想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无关于实际、政治和一切类此的东西;并且珍视接近这最好境地的知识和思想,不容其他任何的考虑来侵犯。”[16]79-80这一席话所倡导的“精神的自由运用”对今天的中国外国文学批评依然有很好的启示。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审美性批评”和“整体观照法”正是自由运用我们的精神、充分表现我们的创新精神的三大要素。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预印本的其它文章
- 外国教育史学在中国
- 走向现代治理的文艺政策
——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政策演变及其历史经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