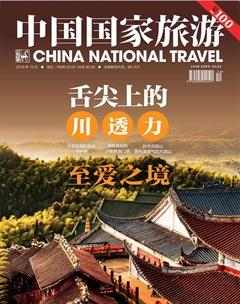驶往西班牙的火车
弗吉尼亚·伍尔夫
你每年都要横渡海峡,当火车缓缓驶过法国港口迪耶普的街道时,你也许再也见不到那幢屋子了,再也不能通过那幢有花盆、有阳台、还有慵懒的女仆倚窗向外张望、历经岁月、粉蓝相间的不列颠拉毛粉饰四层楼房,去感受一种文明的衰落和另一种文明的兴起。
你并不为之所动,端坐捧读——也许是一本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跨越鸿沟、保持延续,面对那些觉得自己从英国的岛屿文明中获得了解放,而向欧洲大陆的另一种文明挺进之辈,因一时的冲动而变得如此怪异、如此放荡不羁,你嗤之以鼻。然而反思一下他们究竟经历过了多少事情吧。不妨回想一下很早以前,也许是在很小的时候,坐在去维多利亚的马车里,我们从车窗里所见到的伦敦街头的模样。到处都是同样的凝重,仿佛那个瞬间并没有移动,而是突然间静止下来,因为突然间庄重感把匆匆过客们那转瞬即逝的姿态都永久地定格下来。他们不知道自己已变得多么重要,假如他们知道的话,他们或许就停止买报和擦洗门沿了。此情此景让我们更加感动不已,因为在我们离开英国的关键时刻,他们居然却还得继续做着这些平凡琐事。所以对那些最终成功渡过了海峡的人们来说,当他们对很像在一场小小的死亡预演中一闪而过的张张面孔作最后的审视时,自然而然应当感到震撼;应当挪动一下手提包,应当开始与人交谈,应当为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个人人都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打开心扉的理想社會的来临而颤抖。
但这仅仅是片刻的激动。接下来,那颗离开了躯体、在窗口上悸动不已的心灵,最渴望的莫过于获准进入那个新社会,那儿的房屋都被捧成浅粉和浅蓝色的菱形;妇女们都穿着坎肩,裤子都是灯笼裤;山顶上都矗立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黄色的杂种狗;街道上的椅子;鹅卵石—— 一句话,充满了欢乐、浮躁和激情。

“我真为阿格尼斯感到惋惜,因为现在必须等到她的未婚夫在伦敦找到工作后,他们才能结婚。现在工作的地方太远,没法回家吃午饭。我该想到父亲会为他们做点什么的。”这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句子,出自两个英国女孩之口,因为她们对着镜子、皱着肩头,在精心梳理着自己漂亮的短发,所以听起来时断时续,像是牢房的根根铁条,沉重地从心头抽过。 我们必须躲避的正是这种聊天,正是老旧的英国式每个星期的钟点、工作和分门别类的安排,既古板又单调。随着火车驶离迪耶普,这些障碍似乎在一种更符合人的天性的文明大锅里翻滚沸腾,化为乌有了。每周的天数变少了,钟点消失了。到了下午五点了,但银行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自然而然然地关门打烊,也没有从数不胜数的电梯里涌出上百万市民或准点去赶晚餐,或在较为贫穷的郊区,去吃整整齐齐放在浅底玻璃盘中的冷肉片和黑酱蛋卷。法国人之间固然存在差异,但我们说不准这些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而角落里的那位肤色苍白、体态丰腴的夫人,坐在那儿微笑着,好像正在驾驭着人生,奔驰在被拉丁民族用天赋抹平了的沟壑和疆界之上。
她起身向餐车走去。她坐下时从手提包中取出了一个小号的煎锅,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一张摊开的《时报》下面。每上一道菜她就趁侍者不在的功夫敏捷地偷偷藏起一部分。她丈夫微笑着表示赞许。我们只能说她很勇敢。他们也许很穷。他们攒下的食品还真不少。刹住奢侈之风,量体裁衣而不打肿脸充胖子,这毫无疑问是法国人生活智慧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当面前放着的是一块有着厚厚层黄色表皮的并不新鲜的奶酪时,她解嘲地笑了笑,用那种像宝石般闪烁而又带有其全部口音的优雅语言,屈尊地解释说她养了只狗。然而她养的也可能是任何别的什么。“生活就这么简单,”她似乎在说。
“生活就这么简单——生活就这么简单,”南方快车的车轮整晚都在用其愚笨或讥讽的方式不停地倾诉,因为在这心绪难宁的夜幕里,在链轴的咣当声中,加上铁路员工痛苦的叫喊以及到黎明时分不堪忍受的身心俱疲的折磨,任何不相称的言说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旅行者颇为名言警句所累。由于离家远行如同一张坚硬的壳,把他们打磨得冷漠无情,使他们变得落落寡合,习惯于独来独往,他们那裸露的心灵里便形成了宽泛的推论。车轮或百叶窗的重压在跳动中化作愚昧不堪的节奏,历数着生活中的虚假深沉,重复着散文的残章断句,令人心烦意乱,他得他们十分忧郁地凝视着沿途的景色,而法国中部的景色是足够乏味的。
法国人讲究条理,但生活本身是简单的;法国人平庸无奇,但他们有好的道路。不错,他们的道路从长着细长的白杨树的地方,直通到维也纳,通到莫斯科,经过托尔斯泰的故居,翻山越岭,然后长驱直入,抵达到处都张灯结彩的闻名遐迩的城市的中心。然而在英国,道路总是最终通到一座悬崖,摇摇晃晃地绕到海边的沙滩。住在英国开始显得有危险了。而在这儿,人们真可以建一幢房子井且不与别人为邻;可以沿着这漫无尽头的白色道路散步,走上个两英里、三英里或四英里,才遇到只大黑狗和一位或许被这空阔无边的景色和自己的行动不便弄得心情沮丧的老太太,她已在河岸上坐了下来,用一根绳子牵着自己的奶牛,她就这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心无旁骛,俨然一座纪念碑。要是我们的英国诗人即使能够时片刻地分享她的静坐、进入她的心境,忘却入世凡尘的戚戚小事,而像她那样去关心人类的命运,那该多好啊!
但是,由于离开波尔多以后的乡间越来越辽阔,进行最简单的思维所需要的那份专心被击破了,就像一只手套因过大的手插入而破裂一样。画家的幸运在于他们使用的是画笔、油彩和画布。然而词语却脆弱易损,它们接触到视觉美的东西便逃之夭夭。它们以最直言不讳的方式令人失望,使人堕入混乱不堪、令人惊恐的幽幽空谷——由于眼睛的一览无余满是白色的城镇、排成一队行走的骤子、孤零零的农舍、巨大的教堂、随着暮色的降临而碎成苍茫一片的辽阔田野、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如同燃烧的火柴头般闪烁的果林,以及那些伴着橘子、云朵和风暴发出红光的树木。美似乎在头顶停住了,人们如此这般地在美的波涛中洗涤自己。窗外的景象纷至沓来:一位沉浸在哀伤中的女士登上汽车,驾车穿过一片荒凉的平原—去哪儿?为什么?马德里的街道上,一个孩子不断地朝基督像抛撒五彩纸屑;车厢里的英国男子正在讨论一篇丘吉尔先生最近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而他的礼帽正好遮住了窗外群山的一半。“别这样,”你禁不住对这美景说,“低点儿,低一点儿:让我通过人的眼睛来看看你吧?”
英国男子的礼帽绝对无法度量群山的美;但车内与车外的景象却不断在融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车里皱皱巴巴的红白屏风,礼帽而设的背景,日落时分对丘吉尔先生发表在《泰晤士报》上那篇文章的奇谈怪论,竟是由街头、橄榄树、山羊、兰花、彩虹、灌木、山脊、沙洲、树丛、土丘等组成,且难以计数、无法描述、不可思议。你的心思心语碎成短短的句子:天热——老人——煎锅——天热——圣母玛丽亚像——酒瓶——午餐时间到了——才12点半——天热。然后一次又一次反复地出现那些东西:石头、橄榄树、山羊、兰花、蜻蜓、彩虹,直到想象的戏法把它们组合成一道道军令、一句句劝诫和一声声激励,倒是很适合行军中的骑士、夜晚孤身站岗的哨兵和统领大军的将帅。
随着夜色变得渐浓,小路已是十分朦胧,那些想象中的骑士们似乎在出于生命的本能,直奔某处非常迷人的景色而去,而他们的坐骑则奋蹄扬鬃,在大地上不停地疾驰。骑士们轻松怡然,他们向前、向前、向前。他们思量着,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呢。
这时只见一只狐狸从路上窜过,由于这是一段草皮小径,可以肯定快到山顶了。尤其显得奇怪的是,骑士们仿佛是在数百年前的英格兰,骑马行进了漫长的一天,这时所有的危险都已过去,他们终于见到了客栈的灯光,老板娘一边走到院子里招呼客人围火而坐, 边做着晚饭,他们坐下来,昏昏欲睡,几个笨手笨脚的男孩和拿着红花的女孩在他们身后窜来窜去,母亲喂着孩子,一个一言不发的老汉从灌木丛中折下枝条扔在火上,火光呼呼蹿起,把众人看着得目瞪口呆。
或许人永远也无法知道,在这样的路程中黑夜过后,会是什么样的白天。听听头顶上传来的声音吧:先听听鸽子扑腾展翅的声音,然后是流水的声音,接下来是一个老汉叫卖小鸡的声音,再然后是远处山谷里传来的驴叫声。听听吧:当一个人侧耳倾听时,那种散漫随意的生命之音,便带着历经千年而恒久高贵的坚忍,开始从一个与非洲大陆隔岸相望的村庄的中心徐徐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