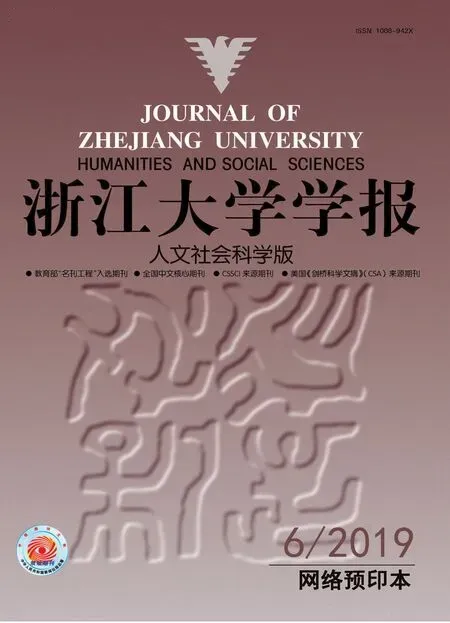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2)
刘禹锡与柳宗元于贞元九年(793)一同进士及第,又先后考取博学宏词科,释褐为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同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旨在兴利除弊、振兴大唐的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又一同经历了政治上断崖式的坠落,和其余六人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各自辗转流徙于穷乡僻壤。从酝酿革新运动的那一天起,他们便互引对方为知己,风雨同舟,安危与共,联手抗御不幸命运的播弄和敌对势力的倾轧。在天各一方的孤寂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与日俱深的嘤鸣之情。
一、再贬之前:奉召赴京途中的“春风初度”
刘禹锡与柳宗元的诗歌唱和始于贞元十五年(799)前后。贞元十二年(796),刘禹锡任太子校书时,其父刘绪病卒于扬州,刘禹锡扶柩归葬于故乡荥阳(今属河南)。刘禹锡丁父忧期间,柳宗元自京寄来叠石砚以表慰问。刘禹锡遂写下《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一诗以表感谢:“常时同砚席,寄此感离群。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碧云。烟岚余斐亹,水墨两氛氲。好与陶贞白,松窗写紫文。”[1]547“叠石砚”,指重叠似山形的砚台。“常时同砚席”,点出两人平日交往之频。刘禹锡曾与柳宗元同学书法于皇甫阅,又同榜登科、同朝为官。“同砚席”,此之谓也。“寄此感离群”,托出对柳宗元的感激与思念之情。“离群”,此指告别僚友,丁忧家居。柳宗元寄来叠石砚的本意是慰其寂寥,却让诗人在铭感之际,更添离群索居的牢愁。中间四句描写叠石砚的音色及形貌:不仅声如寒玉般清脆激越、形似碧云般重叠参差,而且纹路清晰,氛氲有致,不失为人间珍品。这种爱赏之意是与诗人对赠砚者的感怀之情糅合在一起的。结尾两句将古代书法名家陶弘景牵引出场,不及“砚”字,而“砚”字自在其中。诗人表示要追步陶弘景,在松窗下刻苦习书,以不负友人寄砚美意。这就使得诗歌首尾之间“貌离神合”,似断还续。
刘禹锡写作此诗时踏上仕途不久,灿若云锦的前程尚待迤逦展开,内心充满对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未来的憧憬,甚至不无出将入相的幻想,所以,尽管正值丁忧,诗中却不见萧索之气和忧伤之色,纵有一点“离群”独居的孤寂之感,也淡如轻烟,挥之即去。因而诗的格调是清朗的,画面是清丽的,没有融入任何人生枨触。作为刘禹锡的早期作品,它只是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与遣词造句技巧的成熟以及对古代典籍的娴熟,而缺少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所以,在刘禹锡作品中往往被人所忽略。但它却是刘柳结下文字缘的第一篇作品,也是两人之间的第一首赠诗。当然,是否能称之为唱和诗尚可存疑,因为在柳宗元现存的160多首诗歌中,找不到与此相关的原唱或奉和之作。
刘禹锡与柳宗元第一次正式唱和则是时隔15年之后了。这期间,他们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既有过“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的流金岁月,也有过“锻翮重叠伤,兢魂再三褫”(同前)的灰暗时光。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十二月,贬居沅湘之滨长达十年之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作为“八司马”中的幸存者终得奉召返京。他们约定结伴同行,然后分别从朗州和永州出发。两人会合于何时何地,史无明载,但从襄阳宜城开始,他们已经联镳并驰了。因为在襄阳宜城他们曾一起投宿善谑驿,并共同拜谒淳于髡墓,赋诗酬唱。首唱的是刘禹锡,他的《题淳于髡墓》一诗便创作于此时:
生为齐赘婿,死为楚先贤。应从客卿葬,故临官道边。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1]554
柳宗元则有题为《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的奉和之作:
水上鹄已去,亭中鸟又鸣。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荒陇遽千古,羽觞难再倾。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2]第42卷,1153
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大夫,以博学、滑稽、多智、善辩著称。司马迁《史记》称他为“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3]3197。“善谑驿”乃驿站名,相传为淳于髡放鹄之所。后人讹为“善谑”驿,大概是因为其人滑稽善谑。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之作都颂扬了淳于髡的才智与贡献,表达了对客死他乡的先贤的追怀之意。
因为这是刘柳唱和诗的“首秀”,或可视之为“春风初度”,拜谒淳于髡墓的这组并不算高妙的唱和诗才引起我们的重视。刘禹锡的原唱以“齐赘婿”与“楚先贤”对举开篇,强调淳于髡出身微贱却甚有贤名。颈联称赞淳于髡善于托物以讽,多用寓言故事来讲述治国理政之道,劝谏楚王。这种言此意彼的政治智慧也许正是刘禹锡自感欠缺的。“放意能合权”,意谓淳于髡恣意而行,“离经”而不“叛道”。这同样是智慧高超的表现。尾联置酒墓前,抒发对墓主的景仰之情。“一石酒”,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是淳于髡政治智慧的又一载体,诗人以此结篇,见贤思齐之意不言自明。
柳宗元的和诗命意相似,但不是以叙事起笔,而是以写景开篇。“水上鹄已去,亭中鸟又鸣”,将历史的幻境与眼前的实景融合为一,引导读者由亭中鸟的鸣叫想象淳于髡当年以鹄为喻、劝诫楚王,并留下“一鸣惊人”这个成语的历史往事。这就不只是写景,而兼具比兴之意了。同时,这又避免了与刘禹锡原唱用笔的重复。“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揭出成就淳于髡一生美名的两大功绩:“使楚”与“救齐”。这既需要胆略,也需要谋略,可知淳于髡不失为兼具勇气与智慧的古代先贤。这就应和了刘禹锡原唱中的“先贤”二字,为其做了必要的诠释与补充。但斯人已矣,如今只能长揖墓前,怀想其高风。“荒陇”,暗示淳于髡墓地周围一片荒凉,显然难得有人前来凭吊。千古之下,除了他们这些以济世安邦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之外,谁还会缅怀这位湮没已久的古代先贤呢?而淳于髡当时狂饮“一石”、豪气干云的景象则再也不能复现!“难再倾”,有几多感慨、几多憾恨?“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诗人表示,在祭奠淳于髡的此时,自己准备像蔑视礼法、纵酒放诞的刘伶那样痛饮狂歌,直至酩酊大醉,因为墓主是自己的异代知音。这是化用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诗意,将淳于髡引为同调,点明自己虽具有淳于髡那样的抱负及才智,却沦落不偶,久遭弃置,此去尚前景未卜。
元和十年(815)二月,抵达长安近郊后,柳宗元喜赋《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一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2]第42卷,1154以为“阳和”已至,复出有望,因而触目之处都是新蕾绽放的春日景象。为柳宗元的乐观情绪所感染,刘禹锡也写有《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一诗,记录了当时悲喜交集的心情:“雷雨江山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1]306“十年”二句,极写今昔处境与心情的反差,感慨连连,喟叹多多。诗题中并没有“奉和”之类的字样,形式上也不具备唱和诗的特征,但从内容上看,却无妨认为这是对柳宗元前诗的一种回应,是不以唱和为题却具有唱和性质的一篇作品。在初闻长安钟声的此刻,刘禹锡何曾料到,这次奉召回京固然为沅湘十年的谪居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却成为一段新的贬逐生涯的起点。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赋写的“玄都观诗”不仅使自己重罹灾厄,也把柳宗元等友人送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过,他与柳宗元的诗歌唱和倒因此而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二、再贬之际:“玄都观诗案”导致的临歧分别、一唱三叹
刘禹锡愤而创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因为京城中的政治氛围已使他及同侪很难适应,而执掌政柄者依然对他们采取排挤、碾压的态度。宰相中的武元衡、杜黄裳虽然在削藩问题上与永贞革新集团的主张不谋而合,力主对不听节制的藩镇用兵,但在更多的问题上却与“二王刘柳”意见相左,而且在政见的歧异中还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对重回京城等待任用的刘柳等人抱有本能的抵触情绪,根本不愿意看到他们东山再起。所以,尽管朝政的运行尚属正常,但政治气候的严酷却非刘柳等人当年在朝时可比。
新的任命迟迟不见下达,有意启用与继续禁锢他们的两股政治势力正在博弈。渴望尽早为国效力的刘柳等人不甘长久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刘禹锡遂写下《阙下口号呈柳仪曹》一诗:“彩仗神旗猎晓风,鸡人一唱鼓蓬蓬。铜壶漏水何时歇?如此相催即老翁。”[1]306时不我待,他们多么希望能早日履新,一展抱负!可是,一股潜在的势力却依然在为他们设置障碍。以刘禹锡疾恶如仇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反应。恰逢阳春三月,京城的大小道路上,看花的人群川流不息。本不著名的玄都观就因为满园桃花灿烂,变成了车马杂沓、人声鼎沸之地。这不能不使刘禹锡联想到朝廷中那些靠迫害革新志士起家的新贵,于是即兴吟成使他及同侪再度遭贬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1]308诗人以“桃花”影射朝中不可一世的新贵,讽刺他们在将自己排挤出京后才得以飞黄腾达。诗中的芒刺不仅深深刺痛了那些“对号入座”的朝官,而且大大激怒了以逼宫方式登基的唐宪宗。众口铄金,当这首诗被舆论认定为政治讽刺诗之后,曾经一手制造“八司马”事件的唐宪宗觉得自己的尊严遭到亵渎、权威受到挑战,一怒之下,便听从了武元衡等人的窜唆,下诏将刘柳等人再度贬逐出京。
因为刘禹锡是这首“反诗”的作者,所以他遭到了比柳宗元等人更严厉的处分,被贬到最偏远、最荒凉的播州。就在此时,柳宗元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主动恳请与刘禹锡交换贬所,即把条件相对较好的柳州让给刘禹锡,自己去最为艰苦的播州上任。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载其过程并抒发感慨道:
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4]512
“子厚泣曰”云云,既表现了柳宗元对挚友困境的体察之微和了解之深,也体现了他为解救挚友于水火倒悬之际而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由于裴度等人也相继从中疏通,唐宪宗终因担心有损“孝理之风”而收回成命,“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这是刘柳等人再次被贬逐出京。赴任途中,刘柳二人又结伴而行。行至衡阳回雁峰前,分袂在即。前路茫茫,生死安知?除了诉诸诗歌,再也找不到别的恰当的抒发离愁别恨的方式。于是,他们前所未有地频频酬唱。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写道: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2]第42卷,1159
诗中有无辜被贬的不解与不平,有泣别挚友的无尽感伤,当然,也有对不甘示弱于政敌的刘禹锡的劝导。“直以”“休将”云云显然隐括了玄都观看花诗引发的风波,意在委婉地劝说刘禹锡不要“逞才使气”,以“文字”惹来不测之祸,既深见挚友之情,又恪尽诤友之责。
刘禹锡答以《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一诗: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1]553
首联呼应柳宗元原唱,抒发连遭贬黜的悲慨和对翻云覆雨的朝廷的怨愤。颔联以“黄丞相”自况,而以“柳士师”喻指柳宗元,意谓同样多次被贬,柳宗元的崇高声望与品德却令我深愧不如。这既是自谦,也显出刘禹锡对“愿以柳易播”的诗友的折服。颈联与尾联发挥诗题中的“赠别”之意,极写难以排遣的离情别绪:雁行阵阵,猿鸣声声,使分手在即的他们愁肠百结。稍可自慰的是,蜿蜒流淌的桂江宛如一根纽带把柳州和连州联结在一起,他们日后尚可彼此怅望江水,遥寄相思之情。全诗穿越时空,一气盘旋,语淡情浓。后人对此诗备极赞扬,以为更胜柳宗元原唱。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云:“字皆如濯,句皆如拔,何必出沈、宋下?‘长吟有所思’五字一气。‘有所思’乐府篇名,言相望而吟此曲也。于此可得七言命句之法。”[5]200王氏特别欣赏此诗的炼字锻句,以为不在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之下。一般认为,七言律诗在沈、宋手上得以定型,王夫之故有此说。其实,刘禹锡兼擅各体,即便七言律诗的成就也在沈、宋之上,此诗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西塞山怀古》等篇皆非沈、宋所能望其项背。因而,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五云:
一解四句,凡写四事:一写十年重贬,是伤仕途颠踬;二写千里又分,是悲知己隔绝;三写坐事重大,未如颍川小过;四写不曾自失,无异柳下不浼,最为曲折详至也。五、六为衡阳写景,此是二人分路处。七为桂江写景,此是二人相望处也。[6]第4册,246
金圣叹逐句剖析,句句搔着痒处,诗人的艺术匠心尽在其观照之中。《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三纪昀则云:“此酬柳子厚诗,笔笔老健而深警,更胜子厚原唱。七句绾合得有情。”[7]1556柳宗元的原唱也颇见功力,完全可称为唐诗中的精品。刘禹锡的和诗是否更胜于原唱,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不能由纪昀一锤定音。但“老健而深警”,确乎揭示了刘禹锡此诗的艺术特征。
柳宗元读到刘禹锡的和诗后,情思激荡,打破“一唱”即止的惯例,而务欲“三叹”方休。于是又赋《重别梦得》一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2]第42卷,1160从昔日的共同遭遇说到今后的共同选择,既烘托了知己之感,又流露出归隐之意,同时还表达了晚年结邻而居、朝夕往还的愿望,宣示了友谊的老而弥笃、至死不渝。
刘禹锡酬以《重答柳柳州》:“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1]632临岐回想,诗人觉得自己和柳宗元一样,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像“长者”一样忧劳国事,不敢稍怠,却屡屡罹祸,历尽坎坷,实堪伤怀。但所有的荣辱尽成悠悠前尘往事。若得恩准,能与柳宗元相偕隐居,“耦耕”度日,则此生于愿足矣!这是他们再次遭受贬谪之际的真实想法,却是在政治高压下自觉难有作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当后来政治处境改善后,刘禹锡放弃这一选择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万事休”,显出刚强不屈如刘禹锡此时虽然没有折节,却也觉得政治前途已经非常渺茫,不必再做徒然的挣扎。
柳宗元再展翰墨,续作《三赠刘员外》一诗:“信书诚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湘别,何年休汝归?”[2]第42卷,1161感慨以往过于书生意气,一味迷信书本,不知世事之艰、政事之险,以致遭人暗算,自误一生。期望今日揖别于湘地后,能早日被朝廷一同放归,重新聚首至永远。刘禹锡迅即吟成《答柳子厚》一诗:“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1]631依循原唱既定的抒情旋律,同样倾吐了与柳宗元相伴相随的心声。较之柳宗元原唱的直抒胸臆,刘禹锡前二句连用“伯玉”“四愁”两个典故来表达情怀,更见曲折婉转之致。三四句亦各有所本。诗人巧妙融化谢朓诗句,向柳宗元表明自己分别之际的想法:早晚有一天要相随辞官,从禁锢自己身心的重重罗网中挣脱出去。这其实是对前诗中业已吐露的愿望的重申。而这又足证:在“挥手自兹去”的此时,他们已经别无企求,唯愿能相守相伴,不再天各一方。
本来唱和诗属于应酬之作,难免敷衍成篇,失之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但读刘柳的这三组唱和诗却绝无此感。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对诗艺的掌握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字字皆从肺腑中流出,满贮着给对方以慰藉的体温。从艺术的视角来考察,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刘柳先后采用了七律、七绝、五绝三种诗体,也就是说每唱和一次就变换一次诗体,而且变换的规律是篇章渐次缩小,由七言八句五十六字到七言四句二十八字,再到五言四句二十字。这不能不让人推测个中缘由。也许因为第二、三组唱和诗都是于马上口占而成,不暇熔裁,采用七绝或五绝的体式,可以省却一些研磨对偶、韵律以及经营布局的功夫,相对容易写就。这是急就章所习用的讨巧办法。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尤其是首唱的柳宗元有意识地尝试运用多种体裁来驰骋才思、展示功力,以避免唱和形式的单调、呆板。当然,无须讳言,就艺术水准而言,则是与篇幅同步递减:可以说,七绝不如七律,而五绝又不如七绝。试将柳宗元的这首五绝与他此前创作于永州的《江雪》相比较,高下判然而分。这又验证了另一条规律:无休止地唱和到一定程度,必然滑向艺术末路。
在短时间内如此迭相赓和、反复吟唱,在刘柳值得大书特书的友谊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当盛年的他们此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当面讽咏、同场竞技的机会。
三、再贬之后:连州与柳州间的“鸿雁长飞”
元和十年(815)至十四年(819),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谪居连州与柳州。与此前分别贬居朗州与永州时一样,两人频繁通信,讨论哲学、文学、医术、书法等话题。或许因为不想向对方倾诉内心的悲苦与愤懑,向其传输过多的负能量,刘禹锡与柳宗元这四年虽有不少唱和诗,却几乎没有以抒怀为主题的。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固然属于抒情写意的寄赠作品,却是同时寄赠包括刘禹锡在内的四位同命运共患难的友人的,并非单为刘禹锡而赋写。而且,从现存文献看,刘禹锡并没有回赠,也即没有奉和。这似乎有些反常,但想必有其合理的原因。从柳宗元的这首诗也可以窥出一二消息: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2]第42卷,1164
此诗将贬居遐荒、壮志成空的悲愤之情和友朋星散、聚会无期的忧伤之意一并融入山水景物的描写中。首联将登楼所见景色绘制成深蕴情思的画面。以“海天”缀于“愁思”之前,暗示诗人的愁思犹如天一般广阔、海一般深沉。全诗便由这个勾魂摄魄的“愁”字层层下翻,转出一重又一重令人伤心惨目的境界。颔联聚焦近处的夏日景物。诗人不取风和日丽之时,偏择“惊风”“密雨”之际,而“惊风”“密雨”所侵袭者又恰好是常被用作比兴材料的“芙蓉”与“薜荔”,这是有其深意的。显然,这一具有鲜明的时间与地域特色的景象被诗人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颈联推出岭树重叠、江流纡曲的远景。近处风狂雨骤,触目成愁,诗人处境之孤危可知。那么,远在漳汀封连四州的友人的境况又复如何?诗人为寄情而极目远望,但远望的结果却是心音未通而愁肠已断。尾联感叹同居遐荒、音书阻滞。“共来”统摄诗人及诗题中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烘托出患难与共之感。同处瘴地蛮乡,却难相过从,这已够不幸;而更不幸的是,山长水阔,鸿雁不度,友人间连音书也难以顺利传送,只能彼此徒然忆念、空自相思。
这首诗作于柳宗元抵达柳州未久。此时他内心的创伤尚未得到修复,犹自沉浸在无辜被贬的怨愤中,故而要向四位友人一吐胸中块垒。即使是这样,他也不是“质直言之”,而是“比兴言之”,且只字不及时政、时事及被贬原因,只是泛泛诉说心情。这说明他实际上心存忌惮,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不便长期谈论,更不便相互讨论。因此,这之后,他便再也没有与友人继续谈论这一话题,亦即再也没有给友人寄赠类似作品。或许在寄赠这首诗时他已冷静下来,不希望因友人往返唱和引发新的诗案,再生祸端,所以加上了“免复”之类的附言。而四位友人,包括刘禹锡,都与他心息相通,深明其意,也就不予奉和了,否则难以解释刘禹锡谪居连州期间曾写下《答杨八敬之绝句》《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书情题郡斋八韵》《和南海马大夫闻杨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等诸多唱和诗,也曾与柳宗元就书法问题多次唱和,而唯独对柳宗元的这首诗加以冷处理,不做任何回应。而柳宗元在诗的尾联披露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交通不便、音书难达的情况下,彼此很难及时读到对方的即景抒情之作,待得读到时往往节令已改、景物已换,甚至心情已变,这样也就没有奉和的必要了。
刘柳二人这四年的唱和诗主题相对集中,那就是你来我往地讨论书法。这一主题没有时间性的要求,也不必有“政治正确”与否的担心,可以从容构思,径抒己见,因而两人乐此不疲。这些以书法为主题的唱和诗内容独特,构思别致,不仅是诗歌苑囿中的奇花异卉,而且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刘禹锡与柳宗元都酷爱书法艺术,而柳宗元尤甚。刘柳的这组唱和诗包括柳宗元的《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重赠二首》《叠前》《叠后》,以及刘禹锡的《酬柳柳州家鸡之赠》《答前篇》《答后篇》等。因为是知己相酬,彼此可以直言不讳,将自己对书法的认知及感悟和盘托出,所以,两人的用笔较之其他题材的唱和诗要显得轻松活泼些,时而相互调侃,时而相互勉励,同时,两人又凭借对书坛掌故的精熟,寻章摘句,篇篇用事,把唱和诗“相诫”“相勉”“相慰”“相娱”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对此,拙作《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论书诗》(《美术报》2013年6月15日)已详加梳理与论析,兹不赘述。要言之,诚如拙作所概括的那样,这几组唱和诗“亦虚亦实,亦庄亦谐,是两人谪守连州和柳州期间难得一见的快诗,犹如满天阴霾中的一缕亮色,又如以哀婉为主旋律的乐章中飘逸出的几个愉悦的音符”。“但快意中未绝憾恨,轻松中亦见沉重。取譬甚小,而寓意甚深;看似有趣,而实则无奈。因此不宜视为以游戏笔墨和娱乐感官为宗旨的庸常的唱和赠答之作。而包蕴于其中的探究书法的热情以及有关书法的见解,对后人也很有启迪。”
四、余论:刘禹锡对“故人”的深切缅怀
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年近九十的老母亲在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后与世长辞。在扶柩返乡途中,他突然接到了柳宗元去世的讣告。既丧慈母,又失良朋,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使刘禹锡悲痛无法自制,乃至一改平日的庄重斯文,“惊号大叫,如得狂病”。在这凄极痛绝之际,他长歌当哭,除了写下《祭柳员外文》外,还创作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寄托自己深沉的哀思:
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君殁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1]407
在引言及诗作中,三次称柳宗元为“故人”,且于首句和末句重复使用这个称呼。而这个称呼他极少加诸其他友人。在《祭韩吏部文》中,他只是尊称韩愈为“夫子”。在他心目中,柳宗元是唯一心心相印、生死相依的“故人”。当年在衡阳握别时,“故人”曾倾吐过“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的心愿。时隔五年,言犹在耳,他竟已溘然长逝。昔日分别时那“伤心惨目”的情景分外清晰地映现在刘禹锡的脑海里,使他欲哭无泪。“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两句有多少曲折、多少感喟!
其后,在为柳宗元编辑文集的过程中,诗人不时为英年早逝的亡友扼腕叹息,对他的思念也与日俱深。《伤愚溪三首并引》抒发了其炽热的心声:
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
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1]412
引言与《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一样称柳宗元为“故人”。诗人明言“柳子没三年”,可知这组七言绝句创作于他谪守夔州期间。诗人采用移情入景的笔法,借衰飒之景,传哀挽之情,将痛悼亡友的一腔深情如盐着水般融化在巧妙熔铸的景物中,不言憾恨,而憾恨弥漾于字里行间,此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充分显示出刘禹锡驾驭七言绝句这一体式的精深功力。
这当然不是唱和诗,但从诗的情境看,无妨认为这是时隔多年后,刘禹锡穿越历史,对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的一种深情回应。由诗中抒发的浓重的孤寂之感不难发现,由于柳宗元的意外辞世,他在情感上长久处于痛失知音的“空窗期”,因而也严重消减了唱和的热情。柳宗元卒后的三年以及刘禹锡谪守夔州的三年,其唱和诗寥寥无几,且全然不见当年与柳宗元唱和时的那种声气相投、心息相通,那种精神上的高度默契与依赖。换言之,他与柳宗元唱和,是顺应生命的律动,或者说出于披肝沥胆、倾吐心声的强烈需求,是“为情而造文”;而他与其他不少诗友的唱和固然也不失真诚,有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应酬的成分,不免“为文而造情”了。当然,在与白居易“初逢”于扬州之后,白居易填补了柳宗元原先的位置,成为与刘禹锡唱和最为频繁的友人,尤其是两人晚年闲居洛阳期间,诗酒唱酬的热度与密度空前飙升,从数量上看,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我们自然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同样,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从这一意义上说,至少在刘禹锡本人的唱和史上,他与柳宗元的唱和诗不失为一种“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