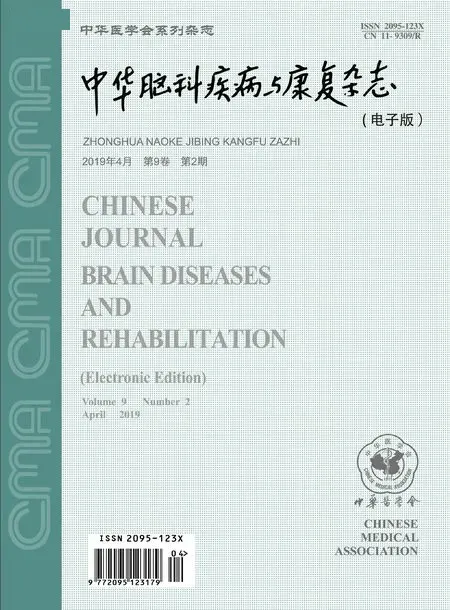颅脑损伤后癫痫发作的研究进展
王丰 林元相
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癫痫发作常见于急性TBI的患者中,中重度TBI患者发生率为22%~33%,并且与ICU住院时间延长有关[1,2]。根据TBI后癫痫发作的时间可分为即刻或早期的(≤7 d)TBI后抽搐发作(posttraumatic seizures,PTS)和晚期的(>7 d)TBI后继发性癫痫(posttraumatic epilepsy,PTE),可导致颅内压增高、脑水肿加重以及各系统代谢紊乱,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继发性脑损伤,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应该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3]。TBI是导致PTS和PTE的主要原因[4]。TBI后大脑会立即发生明显的电生理变化,这可以通过脑电图检测到[5]。癫痫发作不仅导致TBI后早期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而且也是TBI后数年死亡的主要原因[6]。许多研究在TBI后进行癫痫发作预防,并取得了不同的成功[7]。预防主要用于PTS,但对PTE发作几乎没有效果。可能对PTE的潜在机制知之甚少,使其更难以控制[8]。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出现可以有效预防PTE的新疗法[9]。
一、PTS和PTE的定义
癫痫发作是TBI后可能发生的主要并发症,是TBI患者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TBI后,癫痫发作分为立即(<24 h)、早期(1~7 d)或晚期(>1 周)[10]。 发生在 TBI后 7 d 内的发作,称为PTS;PTE是发生在TBI后7 d以上,反复的无诱因发作[1]。
二、PTS和PTE的流行病学
目前国内尚缺乏对PTS和PTE的流行病学的大规模前瞻性、多中心调查研究。据欧美流行病学研究发现,PTE占一般人群中症状性癫痫的10%~20%,占所有癫痫类型的5%[11]。和平年代人群中PTE的总发病率约为2%,但在退伍军人中随访5年或更长时间时,其发病率高达25%[11]。国内外对TBI患者多中心随访统计表明TBI初期GCS评分和是否存在额颞叶挫伤、颅骨骨折是PTS发生的预测因素。PTE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TBI严重程度、是否存在PTS、脑内血肿或脑挫裂伤、高龄(>65岁)以及颅骨(线性或凹陷性)骨折等[12]。发生PTE的风险在TBI后的前2年内最高,并且与TBI严重程度密切相关,2年以后风险显著下降,但持续数十年内仍存在发作的可能性[13-14]。TBI同时也是儿童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儿童TBI后早期PTS的发生率很高(10%~53%),大多数(78%)发生在受伤后24 h内[1];PTE总发生率为0%~12%,多在伤后8个月至5年内发生。与轻、中度TBI相比,严重TBI的儿童发生PTS的风险显著增加,总体而言,可能高于成人早期PTS的发生率[1]。
三、PTS和PTE的发病机制
至今为止对于PTS和PTE发病机制尚无定论,可能的机制如下:
(一)兴奋性毒性损伤
谷氨酸是脑中的主要兴奋性神经递质,而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是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谷氨酸作用于离子型受体或代谢型G蛋白偶联受体,均可促进细胞内信号级联反应。离子型受体包括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α-氨 基-3-羟 基 -5-甲 基 异 恶唑-4-丙 酸 (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ate receptor,AMPA)和红藻氨酸盐。谷氨酸能和GABA能神经递质的平衡对于维持正常的神经功能至关重要[15]。谷氨酸信号通路异常在TBI的病理生理学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急性创伤后谷氨酸释放是造成脑损伤后兴奋毒性的原因,导致神经元损伤、死亡和存活的神经元功能障碍;另一方面,兴奋性谷氨酸通路的延迟破坏导致认知和运动功能的缺陷[15]。在TBI后早期,在皮质和海马区域,存在突触后NMDA受体(NMDA receptor,NMDAR)亚基2B激活和NMDAR亚基2A的下调,导致持续的Ca2+外流,神经可塑性受损和神经细胞死亡的风险增加[16]。随后NMDAR亚基可以恢复,伴随着神经活化的改善,神经营养蛋白的表达增加和神经可塑性增强。这种延迟的神经通路重激活不仅可以通过NMDAR的变化调节,而且可以通过AMPA受体来调节。然而,神经激活的恢复,导致出现各种不良的兴奋性神经传递的风险,包括PTS的发生[17]。
在兴奋毒性损伤的后续阶段,旨在对抗过度兴奋性输入的代偿性变化,受体组成出现变化。特别是GABA受体亚基的功能障碍导致局部环境过度兴奋,引起PTE的风险。因此,TBI后神经细胞兴奋性毒性机制是导致PTS及PTE的关键因素[15]。
(二)神经炎症
神经炎症是TBI后继发性脑损伤的核心过程,并且在PTE的发展形成中起关键作用。TBI后癫痫发生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发生在3个阶段:原发性脑损伤期、潜伏期(活动性神经炎症和神经生物学改变导致癫痫发作倾向增加),以及自发反复发作期即PTE[1]。TBI后神经炎症的特征在于血脑屏障、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和迁移,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以及进行性脑水肿和脑功能障碍。神经炎症通过关键的炎症信号因子(IL-1β和HMGB1)引起癫痫发作,反之癫痫发作也会促进神经炎症。IL-1β的特异性单核苷酸多态性对PTE发展形成具有促进作用,表明可通过调节神经炎症级联反应来影响癫痫发生。可是,尚未证实免疫调节疗法减少急性PTS或PTE发生率的有效性[1]。TBI后几天,在受损的脑区将引发细胞功能障碍,包括一系列影响正常体内平衡的级联损伤反应[18]。这种反应取决于雷帕霉素(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传导机制,已被证实其会导致组织损伤和持续的兴奋毒性,特别是mTOR1c与PTE的病理生理学有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mTOR活化对PTE的长期影响[18,19]。另一个重要的亚急性反应是由Toll样受体介导的,TBI后,这些Toll样受体的激活可导致持续数周的谷氨酸兴奋毒性[20]。因此,炎症反应导致Toll样受体激活与TBI后癫痫发作相关,胶质细胞上的Toll样受体在TBI后引发炎症导致强烈的胶质增生反应[21,22]。最初的损伤级联之后的神经炎症是通过活化的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介导的,其可能是导致TBI后PTS的重要生理病理机制之一[23]。最近的研究证据表明IL-1β作为一种脑脊髓液标志物,可监测PTE模型的持续性神经炎症反应进程,有成为预测TBI后PTE形成的生物学标志物[24]。
(三)tau蛋白过度磷酸化
tau是一种微管相关蛋白,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通过介导微管的结合和非结合状态之间的平衡来维持神经元的稳定和轴突运输,而微管又通过部分磷酸化的tau调节[25]。磷酸化的tau的过度聚集通常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额颞叶痴呆病理过程相关,其中也包括TBI后PTE的形成机制[26]。此外,人体内外的临床研究均有证据表明过度磷酸化的tau导致神经原纤维缠结在PTS及PTE形成中起重要作用[27]。
(四)基因调节及脑膜脑瘢痕形成
GABA信号传导通路与PTE的关系密切,GABA活性降低和谷氨酸含量增加的变化可能与TBI后microRNA的异常调节作用有关[28]。TBI后形成脑膜脑瘢痕病灶是外伤后迟发性药物难治性癫痫的主要病理基础,是引起迟发性癫痫发作的重要病因。胶质增生是导致脑膜脑瘢痕形成的主要病理生理机制。在动物实验中发现,PTE组的动物脑部损伤病灶在显微镜下可见神经细胞死亡、胶质增生等改变[29]。PTE患者术后的病理检查也证实了切除的瘢痕病灶内存在大量的胶质细胞增生。然而,患者在外伤严重程度及损伤部位相同的情况下,晚期出现的脑瘢痕范围却不尽相同,而且并非所有患者都出现PTE,说明脑瘢痕的形成存在个体差异,且可能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近年来对PTE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寻找其基因标志物,希望找到PTE特异性基因突变,并将之应用于PTE的预防和治疗中。在研究过程中,许多科研团队发现了IL-1β、GAD1、A1AR、MTHFR 等基因点突变与 PTE 的形成有关联[30]。这些基因表达与外伤后脑内的炎症、代谢、神经传递等诸多方面相关,在PTE患者与外伤后无癫痫个体的体内表达存在差异,但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验证。以上研究提示基因突变可能是导致PTE的一个重要因素。
简述以上机制,在TBI后急性期,谷氨酸兴奋性毒性促进早发性癫痫发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继发神经细胞损伤级联激活下游致痫因素,例如mTOR活化和Toll样受体上调等,这些亚急性变化导致PTS向PTE过渡。随之可导致形成tau蛋白病,tau蛋白病可进一步促进PTE的产生,从而促进慢性神经变性[31]。结合脑膜脑瘢痕形成等机制,最终发展形成PTE。
四、PTS/PTE的预防和治疗
TBI后癫痫发作已被证明会对大脑造成继发性损伤,可导致缺氧、颅内压增高、脑水肿、脑出血、脑内代谢需求增加、谷氨酸兴奋毒性增高[31]。为了预防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目前关于癫痫发作的神经损伤治疗分为两类:PTS的预防以及PTE的治疗,二者都集中在抗癫痫药物 (antiepileptic drugs,AEDs)的使用。为了降低TBI后癫痫发作的发生率,大多数临床医生会对患者应用预防性药物。虽然有证据表明这些预防性抗惊厥药可以减少早期癫痫发作,但长期预后并未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在预防迟发性癫痫发作方面没有发现对死亡率或神经功能障碍的有益作用,而且没有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某一种药物比另一种药物更有效,如苯妥英、卡马西平、丙戊酸和苯巴比妥,尽管其具有相似的用途,但可用的药物靶点和用药途径不同。因此,在用药之前,必须根据患者状况和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进行选择[31]。总之,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来研究第二代和第三代AEDs在PTE治疗中的功效。
多模式神经监测数据表明,在脑电图出现癫痫样放电之前,会出现脑血流动力学改变包括脑血流和脑氧的改变。惊厥性和非惊厥性癫痫发作都会出现脑代谢率和脑血流增高,从而引起颅内压升高和脑代谢紊乱加重,导致继发性脑损伤。代谢紊乱包括氧化代谢减少、葡萄糖消耗增加和大脑氧化还原状态受损,在TBI后74%的患者中发生[1]。所以,对于TBI后意识障碍的儿童和成人,需要连续脑电图、脑血流动力学监测,因为该人群中非惊厥性癫痫发作,周期性放电和相关的继发性脑损伤的发生率很高[1]。
(一)PTS 的处理
对外伤后是否使用预防性AED仍然存在争议。有研究建议预防性使用AED,以减少TBI后早期PTS的发生率。预防性使用AED可减少PTS发作可能性,以避免PTS导致进一步加重颅内压增高等风险[32]。苯妥英和卡马西平被认为可有效预防PTS。有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给予苯妥英预防的患者早期PTS的风险显著降低,给予苯妥英、卡马西平或丙戊酸钠预防的患者迟发性PTS的风险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苯妥英预防可有效降低严重TBI成人患者早期PTS的风险[33]。然而,晚期PTS不会因AED预防而减少。目前由脑创伤基金会和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发布的关于严重TBI治疗的指南建议仅在受伤后7 d进行癫痫发作预防。苯妥英仍然是理想的治疗方法,因为其已被广泛研究,并且已证明其有效性。与苯妥英相比,其他抗癫痫药物,如苯巴比妥、丙戊酸和卡马西平仍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证明其疗效和安全性[33]。有荟萃分析显示,与苯妥英相比,应用左乙拉西坦预防PTS在作用效果上没有显著差异[34]。卡马西平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但药物相互作用和仅有肠胃给药形式限制了该药物的使用。苯巴比妥由于其镇静作用,可能掩盖了TBI患者真实的精神状态[33]。多个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预防性使用AED能有效降低成年重症TBI患者早期癫痫样发作的风险。但是,对于晚期癫痫的发生率无任何预防作用[35]。甚至由于AED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以及对意识和认知障碍等影响,不建议常规采用AED预防晚期癫痫[36-38]。
(二)PTE 的处理
1.药物治疗:临床医生通过患者TBI病史、临床典型癫痫发作、和脑电图检查可确诊PTE。对于确诊为PTE的患者,包括非惊厥性癫痫,应该采用规范化的药物治疗。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许多新型AED,但对于PTE的控制仍十分困难[39-40]。常用的药物主要包括苯妥英钠、丙戊酸钠、卡马西平、巴比妥、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奥卡西平、托吡酯等。根据癫痫发作的次数和性质,选择单一药物治疗,或两种、多种药物联合治疗,应该通过定期监测患者血清AED的浓度调整AED的使用种类和剂量。治疗持续时间通常为2年,但在实现完全癫痫控制后,AED停药的最佳时机尚不清楚。同时,应该重视AED的不良反应,药物毒性或不可忍受副反应会影响疗效,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受损[41]。
动物模型研究表明,可以将用于其他适应证的抗炎剂作为抗惊厥药的替代物。孕酮在几种脑损伤模型中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效果。较小样本量人体研究确实显示出一些积极的结果。然而,目前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在TBI后常规使用黄体酮以预防PTE[33]。
2.外科手术选择:对于病程2年以上,经过2种AED正规治疗无效,每月1次以上发作,应诊断为药物难治性PTE。对于药物难治性PTE或患者难以耐受药物的副作用,应进行癫痫手术评估。在决定手术计划之前,应对癫痫灶进行严格定位。严重异常或受损的脑组织应始终引起高度怀疑,在定制寻找癫痫发作区的计划时应首先考虑监测这些区域。定位方法包括癫痫发作行为学分析、头皮脑电图、神经影像学以及神经心理学检查,必要时行硬膜下皮层脑电图或深部脑电图等形式的有创性监测[42-43]。如果可以明确癫痫灶,则存在多种手术选择:位于非功能区的的局灶性PTE可以行癫痫灶切除术或脑叶切除术;当癫痫灶范围很大,如数个脑叶甚至整个大脑半球,可行大脑半球切除或离断术;当癫痫灶位于功能相关性的大脑区域时,可采取联络纤维切断术作为癫痫灶切除术的替代方案[44-45];当癫痫灶不明确或无法行切除手术时,可以考虑行神经调控治疗[46];迷走神经刺激术及丘脑前核刺激术在药物难治性部分性癫痫都具有一定的疗效[47-48]。尽管神经调控手术在PTE中应用的研究还很少,但当其他方式失败时,仍然是一种选择[49]。
综上所述,TBI后PTS和PTE是常见的并发症,不仅导致早期并发症和死亡率升高,而且也是TBI后数年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对TBI后癫痫发作机制的很多研究取得了成果,但仍有很多等待解决的未知问题。药物预防主要用于PTS,但对PTE几乎没有效果。针对TBI与此后大脑内慢性变化相联系的途径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开发新疗法至关重要。此外TBI后药物难治性PTE,可以考虑进行癫痫灶切除或神经调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