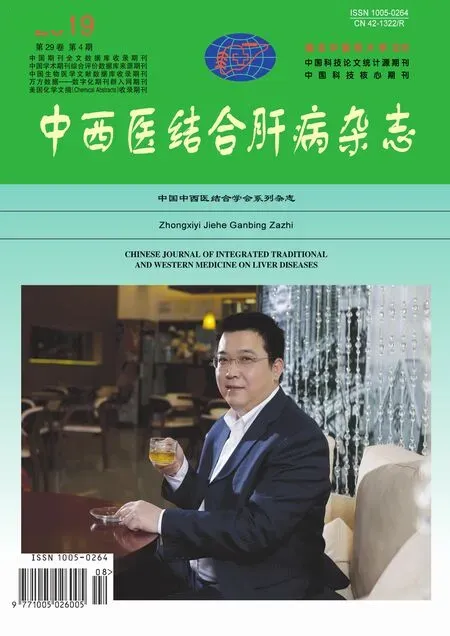络病学说指导下的化瘀通络法治疗肝纤维化的研究进展*
董慧琳 聂红明△ 赵彬彬 姜煜资 陈建杰 王灵台△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病科 (上海, 201203) 2.上海中医药大学
肝纤维化是机体对各种慢性肝损伤的一种修复反应,是一切慢性肝病共同的病理学基础,也是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的必经阶段。肝炎病毒、乙醇、药物与毒物、血吸虫、代谢和遗传、胆汁淤积、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多种损伤因素对肝脏的长期慢性刺激,均可导致肝纤维化。谁能阻止或延缓肝纤维化,谁将能医治大多数慢性肝病[1]。现代医学目前尚无疗效肯定的抗纤维化药物,但已经认识到,病因治疗是延缓肝组织性进展的主要手段,如抗病毒治疗是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治疗的基础,经IFN-α或核苷 (酸) 类似物抗病毒治疗后,从肝组织病理学可见纤维化甚至肝硬化有所减轻。但也有不少情况下,即使去除或控制病因,肝纤维化仍可持续发展。而中医药抗肝纤维化治疗的优势已经逐渐得到业界认可,尤其是以络病学说指导下的化瘀通络法治疗肝纤维化疗效肯定,获得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并逐步得到国际认可。
1 肝纤维化的中医病机认识
传统中医学并无肝纤维化概念,但根据其疾病特点和临床表现,临床多从“癥积”“胁痛” “黄疸”“积聚”等中医病证进行辨证论治。对于肝纤维化的病因病机,众多医家对此各有所见,特别是近代医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病机进行了探讨,如关幼波认为:“肝纤维化本于气虚血滞”,由此而致瘀血滞留,着而不去,瘀血与痰湿蕴结,阻滞血络则成痞块,进而凝缩坚硬;若脉道受阻,则络脉怒张,青筋暴露”。姜春华则提出:“肝纤维化以瘀血为先”。刘平等认为肝纤维化主要由于气阴亏虚(肝、脾、肾),湿热疫毒内侵,血行不利,脉络密阻所致,提出“正虚血瘀”的病机理论。刘树农指出:“肝阴虚,湿热之邪留恋及络脉瘀阻,实为肝纤维化所共有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此三者,又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还有学者认为,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是湿热疫毒入侵,并与正气不足有关。病机关键是热毒瘀结,肝脾损伤。如早期以湿热郁结为主,继而出现湿热疫毒互结,后期则以肝脾两亏为主,兼有瘀毒、湿热等。凡此种种,均说明肝纤维化病机和证候的复杂性。有学者通过对1981年~2012年间所有关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文献(共3 471篇)进行证候学分析,发现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证候主要分布特征是:肝肾阴虚1 333篇,脾肾阳虚818篇,瘀血阻络522篇,肝气郁结428篇,湿热蕴结326篇,水湿内阻44篇。可见,肝纤维化的病机极其复杂,虚实夹杂,涉及脏腑经络和阴阳气血[2]。
著名肝病专家王灵台教授认为,肝纤维化是络病理论的一种具体表现,是络毒蕴结积聚的结果,也是络病发展的晚期阶段[3]。即络病学说是肝纤维化的病机主线和共性,这种认识是基于对慢性肝病的病机特点和络病理论深刻把握的有机结合,在业界独树一帜。王老认为,慢性肝病是一个长期慢性动态发展的疾病,在疾病发展的过程中,初病在气,久病则入血入络,成为顽疾,治疗非常棘手。临床所见之慢性肝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常常在肝胆经络循行的部位有所体现,如目胀目涩、胁痛、胁胀、胸闷、少腹胀痛等,而胁下痞块、面色晦暗、舌质暗红、舌下静脉曲张、脉弦细涩等更是血瘀阻络的有力佐证。因此,王老每在遇到这类患者时就善于运用络病理论辨证施治,往往能收佳效。王老创制的治疗肝纤维化的灵甲柔肝方[4]、治疗胁痛的肝舒贴[5]等都是络病理论在慢性肝病中的应用典范。而纵观文献报道,临床各家学者亦以络病立论居多。可见,络病既是一种病理状态,又可成为新的致病因素,是恶性循环的中介,是多种疑难杂症共同的发病环节[6]。在肝纤维化的研究中,深入研究络病理论,有助于加深中医对肝纤维化发病本质的了解。目前市场上具有抗肝纤维化的中药制剂逐渐增多,如安络化纤丸、大黄虫丸、鳖甲煎丸、和络舒肝胶囊、复方鳖甲软肝片、扶正化瘀胶囊(片)等,无不以活血化瘀、养阴软肝立法,无不体现出络病理论的指导思想。
2 络病学说概述
“络”的概念,始于《黄帝内经》。据统计,“络”字在《内经》中出现次数共计331次,其中《素问》中出现169次,《灵枢》中出现162次[7]。何为“络”?《灵枢·脉度》中曾明确提出:“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为孙。”络以经脉为纪,支横别出。《灵枢·经脉》中说:“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经脉为时磕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当数者为经, 其不当数者为络。” 络脉包括浮络、孙络、别络和脾之大络等几部分,它在人体上下内外无处不至,从大到小,呈网状分布,广泛存在于脏腑组织之间,与经脉既息息相关而又是独立的系统,不能仅仅将它视为经脉的浅表分支。络脉系统既是气血津液贯通的枢纽, 也是机体内外沟通的桥梁,具有联络全身,沟通表里,运行气血,营养代谢,调节机能活动等作用[8,9]。
汉代张仲景在《金贵要略》中提出肝着、黄疸、水肿等病症与络脉瘀阻相关,首创大黄虫丸,以虫类药活血化瘀、搜剔通络。然而,在当时“重经轻络”的大背景下,时至明清时代,以叶天士、喻昌、王清任为代表的诸多医家才明确提出络脉学说,并将其发展延续。叶天士曾言“遍阅医药,未尝说及络病”,他认为“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入络入血”,提出“久病入络”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络病学说理论体系。络脉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由于络脉结构细窄,又呈网状分布,故而通行于络脉中的气血易滞易瘀。治疗络病,在看清络脉这一结构特点的情况下,保持络脉的通畅成为治疗的关键。围绕“络以通为用”的原则,叶天士提出:治疗络病需辨清虚实、寒热、深浅,络病属实者,治以辛温通络、辛润通络、辛香通络、虫蚁通络等,属虚者,治以辛甘通补、补气通络、滋润通补等[10]。
时至今日,以吴以岭、邱幸凡、史常永等为代表的现代学者,继承了前代医家的理论,结合现代先进的科研方法与技术支持,使络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临床运用中,以络病理论治疗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纤维化疾病等领域均取得了较好效果[11]。叶天士云:“医者不知络病治法,所谓愈究愈穷矣。”络病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所体现的微观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中医理论在微观领域里的不足,丰富了理解疾病的角度,给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12]。
3 中医络病理论指导下的化瘀通络法治疗肝纤维化的临床运用
中医学并无肝纤维化或者肝硬化这些确切名词的记载,现多认为其属中医学胁痛、黄疸、肝积、肝着等范畴,由于正气亏虚,疫毒侵袭,情志不畅,劳欲过度,饮食不节等原因损伤肝络,疾病迁延日久,积聚而成。李东垣曰“血者,皆肝之所主,恶血必归于肝,不问何经之伤,必留胁下”,叶天士曰“络乃聚血之所”,吴瑭则将二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肝主血,络亦主血……肝郁久则血瘀,瘀者必通络”,明确提出了“治肝必治络”的主张[13]。杜宇琼等[14]认为肝纤维化临床表现多见黄疸、胁肋闷胀或痞满、积聚结块、出血、痹证、肌肤甲错、面目黯黑、皮肤青筋暴露等,舌脉则多见舌质紫暗或有瘀斑瘀点,脉沉涩,均为瘀血的表现。之后他们总结了一些现代医家的观点,目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均认同慢性肝病的发展过程可近似等同于肝络病变的过程,且肝纤维化以及肝硬化集中体现了肝络病的特点即瘀血阻络[15]。
罗小闯[16]分析了从1984~2014年间期刊数据库(CNKI)中所有包括中医治疗肝纤维化的方药、证候,按照术语规范标准进行收录整理,按照频次进行统计,共收集具有明确证候文献142篇,经统计分析得出肝纤维化证候11个,瘀血互结、肝郁脾虚、湿热瘀阻、肝肾阴虚、肝气郁结为最常见的证候,占总数的83.27%,其中尤其以瘀血互结证出现频率最高,占26.54%。肝病日久入络,络脉痹阻,瘀血互结,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纤维化,主要以化瘀通络法为主,经辨证论治,再加扶正、祛痰等治法。刘焕先[17]选择120例慢性乙型肝炎后肝纤维化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应用甘利欣)和治疗组(应用化纤丸)各60例,经过3个月治疗,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85.0%和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钱梅艳[18]观察病临床例共60例,在常规保肝治疗(口服复合维生素、肌苷片)的基础上,加服以化瘀通络为主的自拟方(鳖甲、土鳖虫、鸡内金、青皮、陈皮、龟板、穿山甲、生牡蛎、丹参等),治疗3个月后,治愈11例,显效26例,有效18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为91.7%。钱亚玲[19]将临床上71例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患者给予阿德福韦酯联合益气通络中药方(由生黄芪、乌贼骨、茜草、丹参、三七粉、制香附、陈皮、党参、炙鳖甲、炮山甲、白花蛇舌草、生甘草等组成),治疗24周后,治疗组第24周HBV DNA阴转率为30.5%,优于对照组的5.7%。郑昱[20]用健脾活血通络胶囊(由白术、虫、鳖甲、威灵仙、柴胡、法半夏、女贞子、墨旱莲、甘草等组成)治疗肝纤维化大鼠8周,发现健脾活血通络胶囊可改善肝纤维化大鼠的肝功能,使其肝纤维化指标明显下降,改善微循环及血液流变学状态。
肝纤维化是肝硬化的必经阶段,如何使肝纤维化得到逆转,延缓甚至中断其向肝硬化的转变已成为肝病治疗的重点和难点。近些年来,临床上运用中医化瘀通络法治疗肝纤维化均取得了较好疗效,结合西医抗病毒等治疗,对于抑制肝纤维生成,促进肝纤维降解,已起到一定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化瘀通络可减轻纤维化程度,抑制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α平滑肌肌动蛋白的表达,从而抑制肝星状细胞(HSC) 的活化,起到抗肝纤维化作用[21]。
4 展望
络病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在多个学科的多种慢性疾病中广泛应用。肝纤维化的治疗是肝病转归的关键,从中医络病理论去解读肝纤维化的病机,并结合现代西医学的研究进展,为肝纤维化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多年临床实践已经证实了其有效性,临床疗效也逐渐得到业内广泛认可。但是,在循证医学的原则下,如何把络病理论指导下的化瘀通络法治疗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治则治法进一步推广使用,需要更多基于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的临床研究,来证实其疗效的科学性。此外,由于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涉及多种因素多个环节,需要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