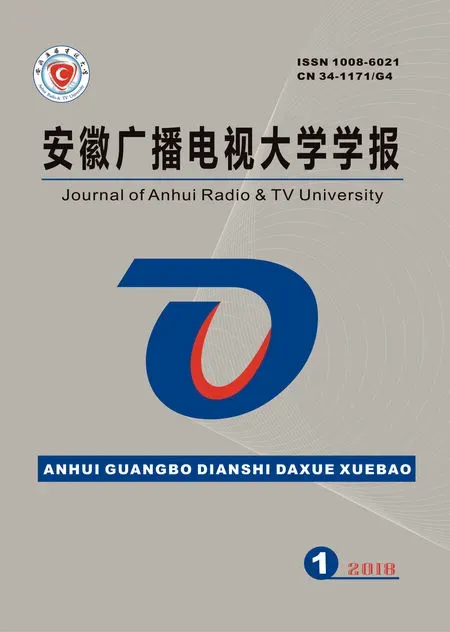1861年前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创作中的农民主题
陈蔚青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屠格涅夫(1818-1883)和涅克拉索夫(1821-1878)同为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19世纪中叶时代剧变的大背景下,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关注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存境遇,写下了一篇篇催人泪下的感人篇目。尽管两位作家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出现了思想立场上的分化,但他们在农奴制改革之前的具有俄罗斯民族鲜明特点的创作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俄国的社会生活,同时又闪耀着人性的光彩。作家们对危在旦夕的社会局势的关注,对受苦受难人民的同情和对民族振兴大业的不懈探索在客观上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也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选取屠格涅夫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前写就的随笔集《猎人笔记》和中篇小说《木木》以及涅克拉索夫的《在旅途中》(1845)、《昨天,在五点多钟的时候》(1848)、《缪斯》(1852)、《萨沙》(1854-1855)、《被遗忘的乡村》(1855)、《大门前的沉思》(1858)、《叶辽穆什卡之歌》(1859)等一系列作品对屠涅二人笔下的农民主题做归纳和剖析,以探究两位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和高超的写作手法。
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均出身贵族。屠格涅夫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性情温和的退职军官。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则是个脾气暴躁的农奴主,她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在她亲自经营的庄园里,只要农奴稍有过失,便会受毒打,遭流放,强制嫁娶,遣送当兵。母亲的专横和暴戾给少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留下了阴暗的回忆,他也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充满同情。1850年11月,在母亲去世之后,屠格涅夫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当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就立刻让仆役们自由了……”[1]后来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中篇小说《木木》里就以瓦尔瓦拉为原型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女地主形象,控诉了母亲的种种恶行,表达了对农奴制的不满和抵制。而涅克拉索夫则在幼年时期就随退役的父亲迁居到了伏尔加河畔的雅罗斯拉夫尔省的祖传庄园格列什涅沃村。未来的作家在西伯利亚流放犯必经的“弗拉基米尔大道”旁度过了自己并不愉快的童年。目睹了粗暴蛮横的农奴主父亲对农民和对家人的恶劣行径后,作家心中萌生出对为非作歹的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反抗之情。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野蛮而落后的农奴制已成为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农奴制危机的加剧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如火如荼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知识分子反封建思想的成熟。而与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相识更加速了屠涅二人确立现实主义文学观和坚定反农奴制立场的进程。诚如屠格涅夫日后所述,“别林斯基与他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是自己的‘全部信仰’。”[2]涅克拉索夫也正是在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指引和影响下,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渐渐接受和明确了“自然派”的写实原则,力图全面地反映生活的真实。在家庭环境、社会变革和“领路人”的支持与引导等种种因素的催化下,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在19世纪40年代几乎同时将视线投向俄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生存境遇。通过挖掘广大农民身上一直被忽视的闪光点和揭露他们遭受的种种来自顽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与摧残,作家们表达了对俄国农民的深深同情和对根深蒂固的农奴制的谴责与批判。
一、重审农民形象
在根深蒂固的农奴制的压迫下,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打破了俄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农民阶级的轻视与偏见,着重挖掘一直被忽略的俄国农民的心灵美与道德美。通过描写他们淳朴善良、热爱劳动等美好品质,作家们企图呼唤人们重审农民阶层,将他们视作一个个有着高贵灵魂的、有血有肉的个体。
1847年,屠格涅夫在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猎人笔记》中,以前人没有探触过的角度挖掘了农民生活的新内容,展现了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才华、优良品行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深受别林斯基肯定的《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随笔《霍里与卡利内奇》里,两位农民主人公便率先以各自的优良品行和卓越才干打动了我们。霍里精明能干,积极上进。他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才智,过上了相对独立富裕的生活。卡利内奇则淳朴天真,热情而喜爱幻想,还拥有识字、养蜂、治病等特长。他们虽性格迥异,却相亲相爱。二人的手足之情令我们不禁感慨:在“吃人”的农奴制之下,俄国农民中竟会有霍里与卡利内奇这般纯洁美好的人物。这不仅仅是生活的真实,更是屠格涅夫进步的思想立场和敏锐的艺术眼光的体现。作家就是怀着这般对农奴制的憎恶和对农民的同情与尊敬,以《霍里与卡里内奇》为基调在之后的一篇篇“笔记”中唱出了一曲曲俄国农民的赞歌。
除了对农民美好品质的赞扬之外,屠格涅夫还在《猎人笔记》的部分篇章和在巴斯科耶看押期间写就的中篇小说《木木》里描写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民的悲惨境遇,对桎梏人性的农奴制具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作用。在屠格涅夫笔下,一方面是俄国农民拥有的积极的性格品质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是他们被奴役和压迫的弱势地位,这种极为矛盾的状况“显然地证实农奴制的不可不废”(瞿秋白语),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含蓄却有力地表达了他的反农奴制思想。
和屠格涅夫一样,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农民也具有善良勤劳、睿智聪慧、自尊自爱等优秀品格。作家擅长描写诗意化的劳动场景,农民热爱劳动、勤勉耕作和劳动本身都是涅克拉索夫的歌颂对象。例如,在长诗《萨沙》里作家就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农民在田地里欢乐劳动的美妙画卷:“看见农家将一把把的种子/撒在地里是何等的高兴!/看见你抽出秀美的穗儿,/土地母亲啊,该多么叫人欢喜。/……/再没有比打谷更愉快的时节:/轻松的活儿在齐心合力地进行。”[3]诗歌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俄国广大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对劳动的热爱。而在诗歌《大门前的沉思》中涅克拉索夫则怀着无限同情描写了一群赶来求见权贵的农民。门外双脚布满血痕、衣衫褴褛的庄稼汉与门内“做着酣畅的好梦的”[4]骄奢淫逸的大官形成鲜明对比。涅克拉索夫愤怒地呐喊:“你被祖国悄悄地咒骂着,却有响亮的赞词来把你歌颂!……”[4]370涅克拉索夫笔下农民阶级与贵族阶级生存境遇的巨大差距更让我们体会到广大农民的无助与不幸。屠涅二人通过塑造一批美好的农民形象,表达了对广大农民的尊敬和同情,展现出封建势力的迫害并不能压抑俄国农民生动而高贵的灵魂。
二、塑造动人的女性农民形象
除了重审农民形象,挖掘俄国广大农民的美好品质,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还格外关注女性农民的命运,并在各自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动人的女性农民形象。
屠格涅夫以对女性的独到描写享誉世界。虽然“屠格涅夫家中的姑娘”(Тургеневская девушка)里多是来自上流社会的贵族小姐,但平民女性,尤其是女性农民仍占据一席之地。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以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一批动人非凡的女性农民形象:如《彼得·彼得洛维奇·卡拉塔叶夫》里聪慧善良,与地主相爱相守,却因违背律法遭到之前的女主人迫害而主动自首的马特廖娜;《幽会》里单纯羞怯、对爱情充满向往却所托非人的农家少女阿库利娜。屠格涅夫还用一整篇《枯萎了的女人》深情而细腻地刻画了卢克丽娅这个感人至深的女性形象:因为一次不小心的摔伤她从仆人中的头一号美人变成了如今“干尸般的女人”[5]。昔日的爱人弃她而去、另娶他人,卢克丽娅并未抱怨,反倒充满理解;躺在小篱笆棚里动弹不得却依旧为更不幸的人们担心;对偶尔照顾自己的人抱有真诚的感恩之心……乐观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卢克丽娅的形象富有非凡的艺术魅力。一系列出身农民的动人的女性形象在屠格涅夫唯美的“永恒女性”画廊里熠熠生辉。
与屠格涅夫不谋而合的是,涅克拉索夫也对农村女性的命运给予了很大关注,写下了众多描写女性农民的诗歌,他也因此被称为“妇女命运的歌手”[4]XIII。作家在《在旅途中》一诗里描绘了一个被贵族生活方式惯坏了的女奴,她因无法适应农村生活而不幸死去;《三套马车》则讲述了美丽的“黑眉毛村姑”[4]141爱上了年轻的骑兵少尉但注定只能嫁给同阶级的庄稼汉,度过操劳艰辛一生的故事。涅克拉索夫的创作思想还体现在他将农民女性塑造成缪斯形象的写作范式中。作家早在1848年写成的八行短诗《昨天五点多钟……》中,在目睹了鞭打乡下姑娘的场景后写道:“她的胸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有皮鞭在挥舞,嗖嗖地响……/我对缪斯说道:‘看呀!你这亲姐妹的形象!’”[4]184这首短诗是涅克拉索夫第一次在诗歌中写到自己受苦受难的缪斯形象。而在1852年的《缪斯》一诗里,作家则直接将心目中的缪斯具象化了:“但那生来只知劳累、受苦和枷锁的、/忧愁的穷人们的忧愁伙伴,/……她在简陋的茅屋,面对烟雾缭绕的松明,/累得弯腰曲背、愁得五内俱焚,/对我歌唱着——她那纯朴的曲调/充满了忧愁和没有止境的控诉。”[4]208-209将女性农民为原型创作出神圣的缪斯形象更加印证了涅克拉索夫对她们劳动精神和不屈意志的肯定和褒奖。在两位作家笔下,承受生活重担、忠于爱情理想、饱受打击却积极向上的各年龄段的女性农民形象,展现出俄罗斯妇女勤劳、高尚和顽强的共性。
三、相同的写作视角
除了重审农民形象、格外关注女性农民的命运,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前的创作中描写农民的视角也如出一辙。屠格涅夫大多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描写农民。《猎人笔记》中的“我”虽出身地主,却没有沾染丝毫封建顽固势力的恶习。“我”热爱自然,充满求知欲,没有一点点老爷派头和对农民的鄙视与不屑。对“我”,即猎人叙述者来说,《猎人笔记》里的农民是由一群特定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我”细心地审视着他们,带着兴趣研究他们。而在这种旁观者的写作视角之下,作家本人的个性、世界观和思想立场便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猎人叙述者的形象和作家形象几乎融为一体。
涅克拉索夫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前也积极使用叙述者与作家融为一体的写作手法,从非农民的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俄国农村的生活,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给出相应的评价。例如,在《在旅途中》“我”通过与车夫聊天,让他“想个法子给我解解闷”“将你的见闻提一提”[4]105,了解到了他出身农民却被贵族生活宠坏了的老婆的悲惨遭遇。《大门前的沉思》中的“我”则因看到了千里跋涉向大官请求帮助却被无情赶走的乡下人而思绪万千,痛苦不堪。旁观者的写作视角体现出两位作家对农民阶层生存境遇的初步探索和他们二人深厚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以1861年农奴制改革为时间节点,屠格涅夫与涅克拉索夫的思想立场急剧分化。改革前,二人对农民主题的挖掘与探寻都流露着对农民的尊重与怜惜之情;而在改革之后,作为俄国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屠格涅夫颂扬沙皇的仁慈,对“解放”了的农村失去了以往的关注。而革命民主主义者涅克拉索夫则致力于揭露“解放”的骗局,号召广大农民奋起斗争,以求得真正的解放。他在生命尽头创作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里采用了新的写作视角,即从农民内部出发,探寻农民眼中的农村。通过用农民的眼光去审视各个阶级的喜怒哀乐,涅克拉索夫把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与真实全面的生动展示结合起来,揭示出农奴制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实质。苏联著名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曾对涅克拉索夫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立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地主习气在涅克拉索夫身上流露得比较少:涅克拉索夫的地主出身只是给他带来了深湛的农村知识,使他对农奴主产生了以牙还牙的憎恨,对浅薄腐朽的贵族自由主义抱着看透了底细的轻蔑态度”[6]。涅克拉索夫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战斗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责任感的诗篇也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壳,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7]尽管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出现了思想立场与写作视角的分化,但他们都在之前的创作中肯定和歌颂了广大农民是祖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表达了对俄国农民的尊敬与同情。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农民主题的创作深深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在客观上对当时扫清农奴制障碍和推进俄国革命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两位作家笔下那一系列正直善良、动人非凡的农民形象同他们敏锐的艺术感、流畅的行文、简洁凝练的语言一道载入了世界文学史册。
[1] 季莫菲耶夫.俄国古典作家论:上卷[M].程代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825.
[2] 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0.
[3] 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文集:第三卷:叙事诗[M].魏荒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8.
[4] 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文集:第一卷:抒情诗[M].魏荒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69.
[5]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M].张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93-394.
[6] 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52.
[7] 列宁.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