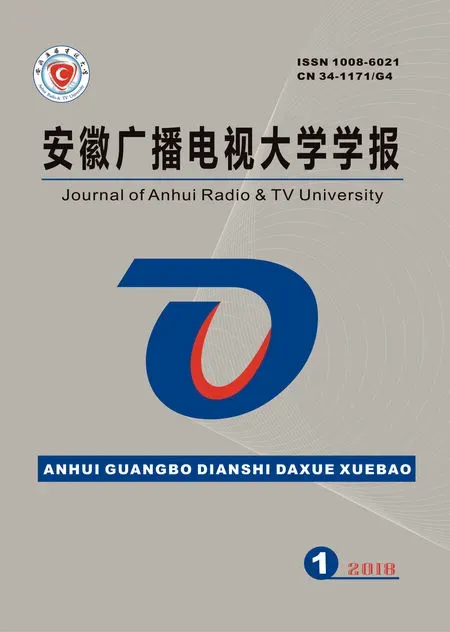杜甫诗歌中的“芙蓉园”意象价值探析
龚 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西安 710119)
在唐、宋诗歌形态的衍变史上,“尚情”“尚意”两种文学范式被视为“唐音”与“宋调”的重要区隔,而促成这种转型的诗学标志便是杜甫诗歌。诚如陈伯海在《“感事写意”说杜诗——论唐诗意象艺术转型之肇端》一文中指出的,在时代变迁和个人经历的共同驱动下,杜甫成为“感物兴情”到“感事写意”这一思潮流动的领路人[1]。事实上,正是杜甫以见证者身份,通过“时事化”笔法赋予客观物象以情感体验,这才使“普遍”物象一变而为“特殊”,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发凡起例”的影响效果。本文围绕杜甫亲观“芙蓉园”的时间线索,以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数次“芙蓉园”写作为考察对象,在归纳“芙蓉园”与杜甫的情感交流过程中,从“时事化”角度还原其作为意象空间在杜甫士人生涯中的意义,并由此管窥这一意象的更新所引起的“尚情”到“尚意”倾向转变的诗学效应。
一、“时事化”与“芙蓉园”意象本体
所谓“时事”,主要指的是在共时空间中所发生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事件,而诗学的“时事化”,则强调的是社会事件经诗人主观地选择过滤之后在文本中的呈现,暗示着某种倾向的发生或转变,这种诗学时间关系也进一步决定了其内涵外延上的两重性:其一是对当下情境的如实书写,其二则是对当下沉淀为历史之后的再度回想。从时间形态来说,前者是即时性的,后者则是非即时性的,非即时性中又可分为短距离和长距离[2]。关于杜甫诗歌的时事书写,最早记录追溯到唐中期元稹《乐府古题序》曰:“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在晚唐孟棨那里,甚至将这一品格有力地定型为“推见至隐,殆无遗事”[3]的“诗史”,此后更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定概念。
但从概念的产生来说,“诗史”也只是后人对杜甫诗歌与时事关系的一种认识,并不足以从心灵起源上解释杜甫如何认识时事并将其在文本中固定下来,而此时,来源于主体对情境主动认识的“时事化”特征恰能在纵横时空中更深入地剖析诗歌本质及作者内心。可以看到,“芙蓉园”首先是作为物质空间存在,但随着具体情境演变,它引起创作者即时或非即时性的感受。后一种感受方式更为复杂,表现为在转入时间沉淀后于稍后或久远的时间节点以重构的方式回忆,而这也正是“时事化”在情感归依到理性思考的变化过程。经笔者统计,杜甫有关“芙蓉园”意象空间描写的诗歌有六首,贯穿其仕隐出处始终,分别是《乐游园歌》《哀江头》《曲江二首·其一》《曲江对酒》《曲江对雨》《秋兴八首·其六》。
综观这六首“芙蓉园”意象诗,围绕“李杨故事”这一历史事件前后,杜甫在广阔时空中展开情感思考和历史体认。这一创作手法本身其来有自,从文学发展背景和内部规律来说,叙事和抒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驾齐驱,《诗经》风雅以下,次降骚赋,再到汉魏乐府,对生活中某一场景、事件发展过程的情节细加勾勒,进而阐发作者的议论或情感的作品屡见不鲜,但杜甫诗歌的独创性就在于他不仅继承了文学传统,更赋予其新变。新变的重要影响因素来自作者人生经历的变化,从时间线索来看,《乐游园歌》《哀江头》创作于入仕前,《曲江二首·其一》《曲江对酒》《曲江对酒》写于位拾遗之时,而《秋兴八首·其六》则作于他挂冠而去后,其间更有安史之乱,玄宗去蜀、肃宗收京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选择以“芙蓉园”为文学容器,从“李杨故事”展开讨论,不仅不停留于对史实本身的描述,且又将其从个体事件上升到普遍意义,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也反衬了作者的精神升华和心理变化。
前面提到了杜甫诗歌“时事化”的两种时间关系,“即时”和“非即时”,两种时间关系也决定了前者是“本体”,而后者乃是“变体”。作为“本体”的“李杨故事”首次出现在天宝十载(751)春《乐游园歌》中:
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
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百日雷霆夹城仗。
阊阖晴开昳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飞,缘云清切歌声上。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4]。
诗歌附录交代诗歌写作背景“晦日贺杨长史筵醉歌”,正月晦日乃唐时节日之一,每年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聚集曲江登赏跋褉,“幄幕云布,车马填塞,虹吸映日,馨香满路”[5]。于此佳节,杜甫在乐游园上亲见玄宗及达官贵戚帝王后妃从夹道入芙蓉园。那么,“芙蓉园”在这盛景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呢?至少在杜甫同期的宫廷文人看来,宫廷游苑之乐乃“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爱物华”(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6]、“睿藻天中降,恩波海外流”(赵良器《三月三日曲江侍宴》)[6]2117,“李杨故事”在此是“圣朝”情景,而杜甫却以“贱士”自居,睹此盛景哀年华不再,一如此前“有客虽安命,衰容岂丈夫”(《赠韦左丞丈济》)、“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杜位宅守岁》),从侧面反映了他深重的慕君恋阙之心。在参加杨长史寿筵之前,他虽曾献赋玄宗得以“参列选序”,但等了一年多音讯全无,“南山豆苗早荒废,青门瓜地新冻裂”(《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现实处境使他绝望,所以才有歌中自嘲。其中,个人事功之情显然更重于对“李杨故事”的议论,“芙蓉园”只是作为客观物象衬托了杜甫的失意,它虽然象征着某种“士道”寄托,但也并未与他有心灵上的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仍属于传统的“感物兴情”,但由于杜甫诗歌更新了传统“物感”的选择对象,由“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7]到人事空间,诗歌的“兴”“感”关系也变得微妙。
二、由“物”到“事”:“芙蓉园”的心理重建
“唐音”和“宋调”的区别在文学史上一直备受关注,而唐人“主情”、宋人“主意”也被视为诗坛公论,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肌理见胜”[8],即是前者重视情感的抒发,后者倾向于在诗歌中表示对社会宇宙、山川物理的看法。自严羽《沧浪诗话》后,宋人“重议论”这一诗评成为后世品评宋诗的出发点,也引发了宗唐、宗宋及二者优劣长达千年的争议,降及清代,叶燮在《原诗》中首次指出,“议论”这一倾向实在杜诗中早已有之,“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9],颇显公允。
《乐游园歌》后,铺陈故实、理性思辨的义理讨论在《哀江头》诗中就有体现。安史之乱爆发后,陷于京城叛军中的杜甫从“非即时性”的角度,在想象和回忆中对“芙蓉园”进行心理重构,使得恒定物质空间“芙蓉园”与象征时事的“李杨爱情”的情感弥合更具质感和沉重感。至德二载(757)春,杜甫作《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往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尘,欲往城南望城北。
“芙蓉园”在唐代又称“南苑”,《雍录》卷七:“曲江在都城东南,其南即芙蓉苑,故名‘南苑’”[7]762。“吞声”“潜行”首先暗示了时局艰危,与之相映的是“千门”的恢宏阔达,与《乐游园歌》中的“阊阖”双线呼应。“昭阳殿”借用汉代赵飞燕典故,“同辇随君”则是班婕妤以礼拒汉成帝同辇之邀,反讽笔法使诗对贵妃恃宠生娇及玄宗昏聩荒诞的理性批判更深一层。而“明眸皓齿”和“血污游魂”两相情境的反差,“清渭,贵妃缢处;剑阁,明皇入蜀所经”[5]763则道出了作者在目睹天翻地覆后的心理震撼。此时,杜甫“非即时性”体认中的“芙蓉园”对象指向更为明确,即唐玄宗和杨贵妃。
围绕这首诗主旨究竟是“悲”还是“刺”,历来有诸多争议,其中如王嗣爽《杜臆》中解道,“深刺以为后谏也”[4]282,又有黄生“若悲若讽”[4]282一说,今人莫砺锋认为是“对盛世的眷恋和国家的忧虑”[10],也可做参考。但与前面《乐游园歌》相比,理性思考成分已经非常浓厚了,杜甫在诗中首以记事手法列举帝王游乐与王朝兴衰的关系,对怀古情感的重新诠释已迥异于借奢华空间来以古讽今的同代诗歌,如骆宾王《帝京篇》、卢照邻《长安古意》类,这正是“芙蓉园”意象“时事化”的特异之处。对杜甫来说,今昔残酷对比促使一己功业理想被忧国的挽歌情调取代,其亲历者角色也使“芙蓉园”成为负载着盛世怀念的独特移情对象;而从写作笔法来看,无论是创作动机还是实际内容,“情”与“意”的二元互动,都反映了杜甫置身于历史时空的心理思考。
从“时事化”的概念本义来说,实际上,“即时”和“非即时”并不对立,情感的跳跃性和丰沛性往往决定文学空间的无限受容,尤其是当客体空间在往昔、今日的时事背景下再次与诗人发生心灵碰撞时,它的含义亦随之迁延。乾元元年(756),当杜甫以左拾遗身份随驾归京,作三首有关“芙蓉园”意象诗歌,《曲江对雨》曰:
龙武新军深筑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前两句,钱谦益《钱注杜诗》中解曰,“悲南内之寂寞”[5]1062,后两句,则是杜甫对昔日盛景的追怀。《杜诗详注》引朱翰语“上皇用万骑军平韦氏,改为龙武军,亲近宿卫。今日深驻辇,则不自临阅矣。又常从夹城达芙蓉园,登兴庆南楼,智久眺望。今日漫焚香,则无复游幸也。”[4]380关于此诗主旨意图,历代注家多谓有所寓指,有言玄宗者,如钱谦益、陈醇儒、朱翰、黄生、浦起龙等人;有言肃宗者,如顾宸、陈之壎等人。以上均为清人,而宋人无言及者,仅泛指时事。宋人所论较当,如近人郭曾炘所言:“此但寓抚今思昔之意,亦不必太泥诗中三字也。”[5]1062诗中,“龙武新军”“芙蓉别殿”是“芙蓉园”的过去记忆,而“深”“漫”又沁润了来自内心的情感力度,横跨时空直指衰败的现下。与之相协的是诗歌抒情体式由《乐游园歌》《哀江头》的七言歌行转向这组七律,抑扬有致到逐渐沉郁的抒情表达浓缩了个人思考,极简练的意象组合反映了作者的纵横诗思,此外,来自身心经历的“全息自叙”方式也勾连了“即时”和“非即时”时空形态,所以随之加深的“时事化”特征才能在对洞察自然和人世方面突出了杜甫的现实体会。
结合此时“芙蓉园”外部废弃,内部堂空无主的事实,一方面是“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曲江对酒》),仇兆鳌解“堂空无主,任飞鸟之栖巢;废冢不修,致石麟之偃卧”[4]375,“燕雀”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厅堂,石麟却废弃在路旁,正如此时朝中李辅国等奸人把政,致使贤人失位。杜甫身为谏官,谏争辅拂以匡正君德是职责所在,但从“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壁》)、“每愁海吝作,如觉大地窄”(《送李校书二十六韵》)来看,他的谏言并不受肃宗重视;另一方面,随着玄宗回朝,政治气氛更浓重紧张,肃宗先后或贬或免房琯、张镐、刘秩、严武、贾至等人官职,曾经试图救援房琯的杜甫自然不在恩庇之列,所以只能“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霏微”(《曲江二首·其一》),朱翰曰:“玩《哀江头》,‘忆昔霓旌’八句,苑中盛事,少陵所躬逢。今云‘苑外江头’,便知重门深锁,傍皇欲绝”[5]1053,实解老杜心事。
感性的“情”和理性的“意”的叠加,成就了杜甫诗歌二元思考机制,在时间距离拉开之后,个人记忆虽褪色为历史,心灵与时事的共振形态却被保留下来,这点在大历元年(776)杜甫漂泊夔州所作《秋兴八首·其六》中体现得愈发强烈:
瞿堂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处“芙蓉园”媒介含义在于,它一方面代表着盛世的寻常,上皇及王公大臣从夹道前往芙蓉园,欢歌笑语,歌舞不休,对杜甫来说,此时作为权利象征的芙蓉园,正是他理想的功名追求;另一方面,它又是乱世的萌发,“入”的本应是代表盛唐的稳定权利阶层,但却迎来了“边愁”,长安被安禄山叛军所攻据,帝王百姓皆因此流散四方。以一“小”字,拈出杜甫对“芙蓉园”的怜爱,不单是对功名理想的惋惜,更是遭家国变故后的情感共鸣。在自古而后的叙述方式中,“芙蓉园”作为杜甫情感投射的建构主体,承载着诗人对历史循环的体认,飞渡历史和现实的此在局限,实现了由纪实、想象再到自由思考的“时事化”演进。
三 、“芙蓉园”意象的诗学意义
我们已经对“时事化”概念和杜诗“芙蓉园”意象空间建构做了详细讨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宏观视域下,杜诗以“时事化”更新“芙蓉园”意象在“唐音”与“宋调”的审美风尚演进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
显在来看,杜甫的“芙蓉园”书写开拓了一类诗歌题材。以“李杨故事”为主体的时事性命题,其模范意义正在于奠定了咏史怀古新范式,诚如陈寅恪所说,“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连习诗文之题目”[11],尤其是目睹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朋党林立的政治乱象,他们追根溯源,诗中直陈明皇贵妃宫闱旧事,如白居易《长恨歌》“西宫南苑多秋草,宫叶满阶红不扫”[6]4819,张祜《邠王小管》“虢国潜行韩国随,宜春深院映花枝”[6]5839、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其五“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6]5950,等等,虽然议事角度不一,但内里议论角度多自杜诗“芙蓉园”续写而起。
从更深层意义来说,则是丰富了一种诗歌思维方式。首先,“尚意”的现实批判性逐渐包蕴了“尚情”的情感体认。杜甫的历史见证者身份决定了他对“芙蓉园”意象物质空间属性的情感寄托,而随着“芙蓉园”的废弃没落,其客体属性渐被忽略,唐人更倾向于在历史情境和文学想象中去阐释它的象征意义。他们直笔真实的书写实践,在宋人那里备受推崇。借用南宋洪迈的话来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宮禁嬖昵,非外间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不以为罪”[12],翻阅全宋诗,无论是北宋的新变派、荆公体、东坡体,还是南宋风行的江湖诗派,作品中都充斥着对时政民瘼的忧切,对于政治现象的道德批判更随处可见,正是在创作动机和实践上继承发扬了唐人关注时事的品格。
其次,仅就“芙蓉园”这一文学空间来看,宋人与唐人在“尚情”和“尚意”天平上实各有偏向。至晚唐文宗时,“芙蓉园”已零落衰败,《旧唐书·文宗本纪》有载:“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13]不久之后,一场宦官戕害朝臣的宫廷事变使得升平之思搁浅。可见,对于身处风暴中心的晚唐人来说,“芙蓉园”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文学空间本身,容纳着历史、现实以及想象的它不仅象征着李杨亡国的教训,亦代表着盛世的辉煌,二者交相刺激着唐人敏感的神经,所以士大夫们会被文宗有心改革鼓舞,发出“天荒地变心难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李商隐《曲江》)[14]的感慨,对于王朝崩塌所代表的社会机制彻底破灭的忧心,远远超越了“甘露事变”这一事件的伤感。相反,在宋代文人看来,帝王行为本身即是理性批判对象,他们将禁苑游乐回归了孔孟儒学之中文王“灵台”“灵沼”之乐与百姓民生矛盾调和的惯性思维,与苏轼苏辙等同时的孔武仲就曾曰:“自甫之殁,其诗愈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为改易,不见于政事,惟嬉游是广,台谢是增,是岂子美之意哉?”,结论是“观诗如文宗者,不知子美也”[15]。相较唐人,一方面,缺失的地理空间感受固然使得宋人“长安情结”并不深厚,考史实,唐末朱温挟天子迁都洛阳,长安全部宫室建筑都被强制拆毁,“芙蓉园”亦不能幸免,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杜甫将“芙蓉园”意象“时事化”更新,由本体意义上升到历史循环体认之后的议论范本更为亲近。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与其认为宋人以杜甫为“诗史”楷模,不如说是对他的“时事化”笔法的自觉传承。
再次,“时事化”也以“发乎礼止乎忠义”的方式为宋人接受。“怨刺”是文学功能之一,但“宋人更关心的是‘怨’中所体现出的符合君臣之义的伦理意识,而非仅仅着眼于刺世疾邪的政治功能”[16]。这组“芙蓉园”诗中,杜甫始终从个人忠君慕阙之心来体察时政,以《哀江头》的曲笔描写为例,第三人称视角的客观描写贯穿“芙蓉园”刻画始终,尤其是“记事”选择上,与宋诗中相辅相成的政治关怀与道德规范遥相呼应,如张戒、苏辙等人都曾以《哀江头》与“寸步不遗”的《长恨歌》对比,由此褒赏杜甫君臣之礼、拳拳之心。此外,杜甫还从个人的达观心态来稀释“时事化”讽刺力度,特别体现于在朝诗中,《乐游园歌》的“萋萋”之草暗示杜甫对于仕宦不能,转投山林的渴望,而在《曲江》组诗中,伴随着“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如此花鸟鱼兽、纤风细雨的山林之趣,他抒发及时行乐的达观之情;“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生”“吏情更绝沧州远,懒朝更与世相违”,虽从全文来看实是无奈之词,但“时事化”的矛头无疑有从外倾转向内省事功理想的趋向,从而模糊了针砭的尖锐性。正因此,忧国而不去国、辱国的理性政治品格不仅符合儒家诗教传统,也为宋人调和个人内心与社会时事矛盾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通过对杜甫诗歌中“芙蓉园”意象的细致分析,我们看到杜甫通过“时事化”使诗歌表达在“尚情”与“尚意”之间流转,从时间线索来说,“即时”和“非即时”为“芙蓉园”意象由“本体”到“变体”的更新提供了条件,直到这一空间由物质空间逐渐过渡到想象空间、议论空间,“时事化”也完成了自身演进。其意义不仅在于扩充了一类诗学题材,更发展丰富了诗学思维方式,它们逐渐被中唐以后文人们接受,最终在宋代文人处以成熟的议论形态凝固下来。“芙蓉园”一类的意象空间,在杜诗中还有很多,诸如“慈恩寺”“花萼楼”“大明宫”,等等,挖掘这类意象从而对杜甫凝聚记忆及艺术表达方式的还原,或有助于深化理解位于具体空间语境中的杜甫诗歌。
[1] 陈伯海.“感事写意”说杜诗:论唐诗意象艺术转型之肇端[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34.
[2] 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504.
[3]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
[4]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89.
[5] 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14.
[6]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95.
[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3.
[8]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9] 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0.
[10]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2.
[1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
[12] 程毅中.宋人诗话外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805.
[13]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61.
[14]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4-145.
[15] 王遽.清江三孔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2:281.
[16]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7:41.
——试论杜甫的曲江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