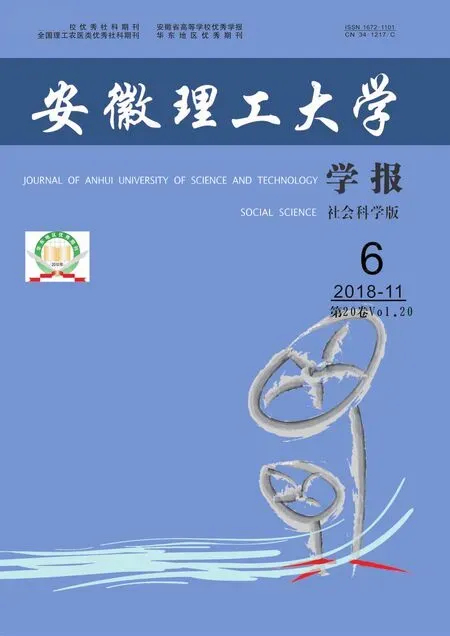抗战时期新四军对淮上地区红枪会的统战工作
王 琦, 朱广亮
(1.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2.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 232007)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1]。抗战时期,红枪会作为一种自发的民众武装自卫组织,广泛分布在北方晋、冀、鲁、豫、皖诸省,是一股强劲的抗日中间力量,也是中共重要的统战工作对象。
一直以来,学术界颇为关注抗战时期共产党对红枪会的统战问题,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梁家贵分析研究了抗战时期鲁、皖、苏三省红枪会的分化情况以及国共两党对其政策差异[2]。吴宏亮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河南红枪会的改造与争取[3]。袁岿然针对1913年至1953年河南红枪会的发展情况做了深入研究[4]。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基于省级区域的宏观研究,呈现出重冀鲁豫而轻安徽的倾向。红枪会作为乡村民众自卫组织,其形成与发展必然与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与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县域层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微观研究。抗战时期彭雪枫率领新四军三进淮上地区(指淮河凤台至怀远段以北的左岸地区,古人以左为上,故称淮上),开辟淮上抗日根据地,而其所下辖的凤台,怀远等县是红枪会在安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本文立足于个案研究,通过分析淮上地区红枪会的起源流变及其原因,探讨中共对其争取与改造的必然性,分析新四军所采取的统战策略,并总结其历史经验。
一、红枪会在淮上地区的发展历程及其原因
红枪会又名红会,淮上地区称之为“杆子会”,“红学”,是一种兼具自发性,革命性和落后性的民间自卫组织。学界普遍认为红枪会是由金钟罩,大刀会演变而来,“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5]。 红枪会发轫于1918年前后,20年代中后期在直鲁豫等省盛极一时[6]。 “豫南一带,凡有一村一堡,不论大小居户,每家须派一人为红枪会会员,每员皆备锋利之长枪,枪刺之末,结以红缨一束,以符红枪之名”[7]。之后豫南红枪会逐渐蔓延至下游的安徽沿淮地区,1923年,豫南固始县大刀会首领梅广恩到安徽六安,寿县一带开香堂招募学徒,“红枪会遂发展到淮河中游一带”[8]。
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方面宣布红枪会为农民自卫合法武装,鼓励其发展。之后不久北伐革命军挺进安徽,与直鲁联军在淮上地区发生激战。战争严重冲击与破坏了当地原有的权力格局,引发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与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发生了土匪绑架县长的恶性事件。据《申报》记载,“皖北凤台县知县在本年三四月间,系直鲁联军某军长所委,五月间,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到蚌,前知事闻风逃走,某政治主任遂委员署理凤台县矣,到任不到三月,而凤台县长忽经三十三军撤任,当局援例委洪某瓜代该县,不及一月,联军方面改委方某署理凤台(方某充其军秘书),接任不满一旬”,忽然被当地土匪绑架,后经“红枪会中人托话,要求速筹洋五万元,方能赎身,否则照章撕票。地方正绅闻之,恐得罪当局,遂凑现洋三千元,将方知事等赎回,现已逃至蚌埠,不愿再做此官”[9]。时局不靖,政权更迭,面对地方政府在治安管理方面的严重缺位,安徽沿淮地区各乡村纷纷自行组织武装进行自卫,“皖北年来因受军事影响,各县人民为自卫起见多入红枪会,练习符枪,以御匪患”[10]。红枪会势力随之迅速发展,“皖省寿州、怀远、阜阳等处,遍地红枪会”[11]。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土匪亦渐肃清、红枪会自无存在之必要”,开始着手对各地红枪会进行控制和改编。然而,1931年淮河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却中断了国民党改编淮上地区红枪会的进程。百年一遇的洪灾不仅造成凤台,怀远等县惨重的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而且进一步引发社会失序,导致治安情况严重恶化,“沿淮各县,灾情尤重,全国各地水灾,盖无逾此者,际兹水灾浩大之中,而凤台县境复遭股匪扰害,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大股悍匪五百余人,盘踞骚扰,截劫长淮商船,搜抢各村民食,劫掠之后,任意烧杀,夺去地方人民自卫团枪械二百余支,杀死绅士陈某及苏某全家,其他被害者甚多,长淮交通为之中断”[12]。面对严重匪患,地方政府却束手无策,“长淮水上公安局实力薄弱,县政府鞭长莫及,更无驻军可以要求救急。小轮公司以及行旅生命财产攸关,无力御匪”[13]。政府治理能力的软弱使得红枪会在淮上地区再次兴起,灾后官方在沿淮各县实施工赈时发现“凤(台)怀(远)灾工十九皆学过红枪”,“工人大半是红枪会中的成员,故在工棚的前面,常竖着几枝古时的红缨的铁枪以为自威”[14]132-134。1934年,安徽省政府内部就“如何使政治力量普遍达于乡村”的问题展开讨论。针对“目前政治力量只能至县而止”的情况,与会者一致认为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现时环境下,惟有实行保甲制度”,主张“办理保甲,以充实人民自卫之力量”,“办理保甲,为实施地方自治之先决问题”[15]。随后国民党当局在皖北地区强制实施保甲制度,推动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要求乡村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男子一律编入壮丁队,试图以此作为官方认可的乡村自卫武装去取代民众自发组织的红枪会。然而,在实际实施中,国民党当局却发现淮上一带“保甲长识字甚少,知识太低”,“政令由省到县,由县到区,即算完了,即传到保甲处,因不识字,亦是很困难的事”。究其原因,民国以来皖北地区农村经济凋敝,乡村精英大多选择离开故土,“知识分子,群趋都市而离开了乡村”,“在乡村中可以说全是农人,知识不开,浑浑噩噩”[16]。乡村社会结构的裂变,传统士绅阶层的流失,都使得国民党政权所设计的乡村自治与自卫方案丧失了主要承担者与推动者。因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弃以往依靠士绅融合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传统路径,转而借助于红枪会这一乡村底层民众的组织去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保甲制在皖北的推行不仅未能取代红枪会,反而出现了两者合流的情形,“皖北各地民智尚闭,政府法令也未能推及于乡区,乡保长之流如与红枪会没有相当渊源,无论如何休想立脚,因此,顺水推舟,堂长便往往由保甲长承兼”[17]。因此,从表面上看,保甲制实施后红枪会在淮上地区逐渐陷于沉寂,声势远不及东北,冀鲁豫等地。然而实质上红枪会并未消失,只是悄然隐身于保甲制之中,潜藏在了淮上乡村的田间地头。
抗战爆发后,淮上地区沦入敌手,国民党所主导的国家防卫体系基本瓦解,地方行政组织也随之解体,红枪会又迎来一个公开化迅猛发展时期。在怀远县,广大农民“纷纷参加红枪会,在短时间内入会人数占男性青壮年一半以上,新设红枪会堂三千多个,会员多达数万人”,其中尤以郑永才、朱世全、陶文彩等人以淝河区的蒲庄、赫庄、黄庄、刘小圩为中心成立的“蒲赫黄刘”红枪会势力最大。在上窑的泉源、马岗、上窑、外窑等村,红枪会先后分设十六处会堂,参加会员达七百余人[18]。凤台县有以王鹏飞、尚四猴子为首的红枪会,人数近二千人,主要在潘集、王圩子、平倭山等地活动[19]。从临淮关到浮山的沿淮两岸,红枪会办起了一百多个会堂,会员达两千余人[20]。
由此可见,红枪会在淮上地区的发展历经三起三落,其兴衰沉浮伴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乡村社会的扩张与消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当国民党政权试图重建乡村社会权力秩序,推动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下沉时,势必会压制红枪会在乡村的发展;反之,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收缩与缺位则是推动红枪会在淮上地区的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国民党政权未能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未能满足底层农民的利益诉求,因而未能获得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所以国民党主导下的国家权力始终无法下沉至淮上地区的乡村社会,实现对基层乡村的直接有效控制。加之淮上地区传统士绅阶层普遍“离村”这一地域性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当局愈加无力去重塑乡村权力结构,只得依赖传统力量,通过捏合红枪会与保甲制以实现对乡村农民的控制。因此,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缺位是红枪会在淮上地区发展历经起伏却绵延不断的主要原因。
二、 新四军对淮上地区红枪会改造的必然性
首先,新四军对淮上地区红枪会的统战工作是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要求。淮上地区红枪会成员多是贫困农民,怀有朴素的爱国热情,是一股重要的抗日民间力量。早在1932年,时人在淮上地区宣传“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军的种种暴行,红枪会“听者莫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识者认为红枪会这些钢筋铁骨的健儿,如果“加以军事训练,授以新式武器,晓以国家大义,然后驱赴战场,冲锋陷敌,必较他项军队来的勇猛而沉着”,“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前途一线的曙光”[14]133。抗战爆发后,淮上红枪会英勇抵抗日寇入侵,表现出了广大农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我皖北一带红枪会此次协同军队实行抗战,甚著功绩,敌军对之极为畏惧,常呼以铁人”[21]。 1938年3月,怀远县上窑镇红枪会3 000余人协助桂系三十一军刘土毅部对日作战,一度攻克怀远县城。宿县“四乡遍地有红枪会”,日军“每遇交绥,均大败而归,红枪会因历次予日军以打击,获枪甚多,现已多数均有枪炮(均系夺自日兵),实力雄厚,日兵三五在乡下失踪者,已属常事”,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支劲旅。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红枪会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称红枪会为“深藏在民间的武装”,称赞“他们为了自卫,在本地作战,常常表现出很大的力量”,认为“他们总是中国人,要他们抗日或者同情抗日总是容易些”,因此,要注意“要宣传引导他们积极起来抗日,打游击”[22]。因此,新四军贯彻落实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整合淮上地区的抗日力量,势必需要有效团结和改造红枪会这支本土力量。1943年淮北抗日根据地党委作出《关于加强统一战线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加强对会门工作”,要学会与红枪会等会门组织“交朋友”,认为“这关系于我们抗战工作的厉害,不可不慎”[23]。其次,新四军对淮上地区红枪会的统战工作是巩固和加强淮上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乡村社会的权力缺位是淮上地区红枪会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主因,而新四军在进驻淮上地区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政权建设,重建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权力格局与社会秩序,彻底消除了国民党溃败所产生的乡村社会暂时性权力真空状态。1941年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陆续作出《关于强化各县政权问题的指示》(1月31日),《关于加强各县政权问题的指示》(2月19日),要求“改造淮上办事处为边区联委会淮上行署,改怀远、凤台、宿县等办事处为各县县政府”,正式开展淮上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致力于将“政权改造为坚持抗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指示》要求成立区乡行政委员会为该区及乡最高办事机关,负责领导全区及乡抗战动员,武装自卫等事宜;对保甲制进行民主化改造,“乡保甲行政人员应实行民选,已民选而健全者,不必重选;民选而不健全者需要改选者,改选之;从未民选者,实行民选之”;对民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坚实的地方武装,将“动员(农民)参加主力军,成立自卫队,站岗放哨”等作为各县政权最中心的任务,要求县区成立常备队,“乡建立满三十人以上脱离生产之自卫队”,“务使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发展滋生”。《指示》还特别指出,“怎样动员广大人民武装起来”,是“摆在政权工作者面前的中心课题”[24]。经过有效的政治动员,新四军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与支持,重新构建淮上地区的基层政权体系,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自卫武装——自卫队,重塑了全新的乡村社会治理权威。这些加强政权建设的举措实际上已经彻底消解了红枪会存在的基础与价值,因此,新四军对红枪会加强控制和改造就势在必行了。之后,豫皖苏边区政府提出对红枪会等会门武装的统战对策,强调以宣传教育手段为主,“嗣择其有枪支且愿意脱离生产的须指定工作同志专门做工作,使之逐渐脱离迷信色彩,变成群众的自卫组织”。随着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发展,淮上地区的红枪会成员逐渐被编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民兵组织,最终被纳入到了中共领导下的基层乡村治理体系中。
三、 抗战时期新四军对淮上地区红枪会的统战策略
抗战时期,彭雪枫指挥的新四军三进淮上,创建了淮上抗日根据地,使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向东扩大到津浦铁路,向南延伸到淮河怀远至凤台段,向北发展到陇海路,成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取得如此赫赫的战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彭雪枫为首的党政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积极主动的统战策略去争取和改造了淮上红枪会组织,最大程度的调动了淮上地区一切抗日积极力量。
(一)高度重视对于淮上红枪会的统战工作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对红枪会这一组织的性质有了比较深刻准确的认识。1926年中共通过《关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提出“必须注意引导这种力量,并要努力使这种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主张引导各种性质的红枪会“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25]。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和侵华日军争相拉拢淮上红枪会,企图利用红枪会达到反共的目的。例如“蒲赫黄刘”红枪会中的路家云部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为第五战区独立第七游击支队,而陶文彩则可耻的投降了日本人,成为了“鬼变子”。
面对这样复杂严峻的形势,彭雪枫高度重视淮上红枪会的统战工作,他指出“对于会门武装,对他们应有正确的基本认识,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代,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更相信在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26]因此,在新四军第一次进驻淮上地区时,面对红枪会的不时阻挠甚至袭击,彭雪枫并没有盲目的对其进行武装镇压,而是把政治宣传战作为工作的重点,使党的理论和统战政策逐步为红枪会广大群众所接受,一方面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另一方面则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最终为淮上地区的抗战争取到了广大的同盟军。
(二) 积极灵活的争取红枪会的策略
彭雪枫的家乡——淮河上游的河南镇平县历来是红枪会活跃地区。彭雪枫在少年时期就曾接触并拆穿过红枪会“刀枪不入”的把戏[27]。1938年2月彭雪枫出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和统战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豫南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西北军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新四军挺进豫东地区,彭雪枫与永城彭姓红枪会头目认宗为亲,联络感情,最终争取到了这支500多人的队伍。可以说,彭雪枫同志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和策略,为争取和改造淮上红枪会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加强与红枪会首领的联络与合作。新四军一进淮上时,国民党怀远县政府给各区乡政府下了密令,不准与新四军接触合作,并煽动红枪会头目向新四军进行挑衅。彭雪枫聘请亳州红枪会师爷任义清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参议,并利用任义清的关系在怀远县龙亢西寨头铺南边公路上召开红枪会亮杆子会议。彭雪枫、钮玉书、任义清分别作了抗日动员报告,使得龙亢一带的红枪会转而拥护我党的抗战路线,积极支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其次是对红枪会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1940年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4日,受到国民党蒙蔽蛊惑和裹挟收买的红枪会众四五千人配合顽军保安团向我淮上抗日根据地的平阿山地区进攻。我军随即组织反击,并在战斗中击毙了红枪会首领汪海波。10月7日,红枪会首领汪海波送葬出殡,淮上总委会主任钮玉书亲自前往吊唁,并补发500元大洋作安抚慰金,在当地影响极大。彭雪枫认为:“红学进攻正规军而且又失败了,这在老百姓看来认为是件大事。根据过去的历史,红学和军队打仗以后,而军队又打胜了,那么,这些红学的村庄和人民都要被烧光杀完的,但是我们党的政策,既不杀,又不烧,后来红学给他们的首领出殡,我们的‘山西’部队反而派人去吊孝。这样一来,远近的百姓都交口称赞八路军,到处传扬。”[28]灵活斗争策略最终争取到了民心,取得了良好结果。
最后是重视对红枪会的政治改造工作。近代以来淮上地区乡间封闭守旧,“部落思想色彩浓重”,加重了红枪会的落后性,使得红枪会内部更容易围绕着权力激起争斗,成为乡村社会动乱之源。例如“蒲赫黄刘”红枪会内部郑永才等人与路家云的对立与武斗,相互厮杀,血流成河,最终一方投降国民党,另一方则投靠了日本人,沦为民族败类。因此,对于红枪会的政治改造工作也就势在必行。1944年秋,彭雪枫率部三进淮上,恢复了宿怀县抗日政权,委派任义清做蒲庄、赫庄、黄庄、刘庄四大派红枪会统战工作,举会首杨兆峰为总司令,编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民兵组织,最终将这一股重要的抗日中间力量纳入到了中共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中。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这是对统一战线90多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是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心聚力的重要遵循[29]。回顾历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包含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联盟,既在共同目标和最终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也因具体利益差别而呈现出多样性。辛亥革命以来淮上地区乡村社会面临着经济衰落、政治动荡、精英流失、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而国家权力的缺位与传统绅权的消解使得农民阶级只得依靠自发性的组织红枪会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抗战爆发后,淮上地区红枪会民众在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的团结对象,然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又使得红枪会具有一定的落后性。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挺进淮上地区后,积极开展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依靠爱国主义这个抗战时期最大公约数,包容、尊重、引导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采取积极灵活的策略对红枪会加以改造,最终将这一股抗日中间力量纳入到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去,从而实现了抗战力量最广泛的团结。从这点说,彭雪枫领导下的新四军对淮上红枪会的统战工作堪称贯彻落实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也为我们在当前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