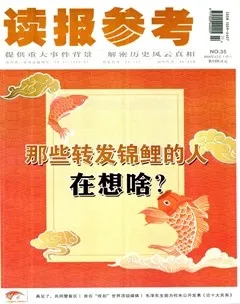走近一战华工后裔,追寻14万华工的背影
2018年11月11日,一个值得国人铭刻的日子。
百年前的这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与英法等国的战士一起欢呼这一胜利的。还有一群作为“战勤”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东方人——总数高达14万人的一战华工。
遗憾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在次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被漠视了。中国作为战胜国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被无情地拒绝。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百年过隙。一战华工群体已经鲜有存世者。近日,记者走近他们的后裔,触摸他们留下的珍稀物件,抚读他们在烽火岁月中留下的珍贵日志与记录,穿越百年去感受他们不朽的功勋……
90年后,孙女终于找到爷爷在法国的墓地
对于程玲来说。属于她与华工爷爷的有限物质存在感,只有一枚褪色的铜质勋章。勋章上一位勇士手执短剑,脚跨骏马,马蹄下踩着一个骷髅。勋章的侧面有一个编号——97237,这是爷爷毕粹德的“名字”。百年时光磨洗下,黄蓝相间的勋章丝带线已经断开。
在济南市信义庄西街附近的一个小区里,60岁的程玲告诉记者,她的爷爷毕粹德原本生活在山东省莱芜市牛泉镇一个平静的小村子——上峪村,可远在万里外的一战战火,让他背井离乡,前往法国在英国军队里当了一名劳工。
“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他走的时候,我的父亲才几个月大。”程玲说:“我们村里去了11人。只有爷爷没有回来。”
百年前的毕粹德,在迈出村子前往法国之前。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命运竟然会和波澜起伏的世界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以工代兵”计划。从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英法等国总计从中国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等地招募了14万华工漂洋过海到达欧洲,进行艰辛的战勤工作,华工中有近七成来自山东。
“我经常让父亲讲爷爷的故事,可他知道的也不多。多少年以来,这枚勋章是我们家人思念的唯一寄托。虽知爷爷早已命丧欧洲,下落概不知晓,但是1990年父亲去世以后。家人更加念念不忘杳无音信的爷爷,也增加了我们查找爷爷下落的决心。”程玲说。2007年的清明节,她曾在山东当地的报纸上发文,表露了这个家族心愿,文中写道:“爷爷,我该怎样祭奠远在法国的您?”
让程玲和家人没想到的是,正是她的这篇文章,让法国华侨和留法华工后裔了解她的故事,并伸出了援助之手。读到这篇文章的张捷哈是老华工张长松的第10个儿子,他的华工父亲一战结束后留在了法国,在二战时又成为军人,为争取法国自由而战,而他本人也曾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他的儿子也曾是法国军人。“他当时拿着我写的文章,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以三代军人的名义给前法国总理拉法兰及法国退伍军人部写信,最终促成了我们的法国之行。”程玲说。
2008年一战结束9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几经辗转,在英国墓地管理委员会的帮助下,程玲和丈夫、女儿终于找到了毕粹德长眠于法国索姆省博朗古村的华工墓地。摆上家乡的烟酒、点心、冬枣、高粱饴、芝麻饼,烧纸、点香、磕头,口中不断默念——程玲一家用家乡最传统的方式,告慰从未谋面的爷爷。
“即便已经找到爷爷的墓地。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程玲告诉记者:“当时父亲刚出生,家里条件也不算差,奶奶也多次挽留。为什么爷爷还要毅然决然去欧洲做劳工呢?我想找到尘封的档案,了解那段历史。”
开眼看世界的“艰辛之旅”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郊,57岁的马京东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钢管厂。在马京东办公室的书柜里,存放着一个不起眼的包裹。
“这是俺爷爷的照片,这是他的名片,这是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记日记的小本本,这是带回来的明信片,这是他写的《游欧杂志》,记录当时的经历。”马京东打开包裹,一一介绍着存放了百年的华工爷爷马春苓的遗物。
马京东10个月大时,爷爷就去世了。对于马春苓参加一战的那段经历,他是从这些老物件以及家人的口述中了解到的。1917年10月。临朐县胡梅涧村村民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报名参加英国招募华工活动。按照《招工合同》,工人们每月可以领到12块大洋,他们在中国的家属每月也有10块大洋的养家费。
对于那时普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很多华工寄希望以此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甚至改变命运。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是常年研究一战华工的权威专家,他介绍:华工主要来自农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淳朴老实、任劳任怨,渴望能到法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被招募的华工中有一部分是军人或当过兵;另外很大一部分是技术工人,包括木匠、铁匠、机械师等:甚至还有一部分华工曾在中国拥有体面的工作,如教师、文员等。这些人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盼望在西方世界获得一些新知识。
马春苓就属于后者。作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朝夕讲诵地理,而授者听者,皆恍惚无证”,去欧洲不仅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圆自己的“环游之志”。
同为乡村教师的华工孙干来自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和尚房村。在他8万多字的《欧战华工记》中也表达了他游历欧洲考察教育的初衷:“尤以非身临英、美、法、德其境,以观察之,不足以明其教育之真谛也。”
然而,想要成为英法雇佣的劳工,竞争异常激烈。据《纽约时报》1917年2月的报道称,只有“那些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留下的华工”才有机会前往法国。其中“大部分人”身高超过六英尺。
法国和英国都想招到身体素质最好的华工,因此都把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作为主要招工地。因为山东人体格强壮。吃苦耐劳,并且能习惯法国的气候。
经过体检、剪掉辫子、清洗全身、再次体检后,入选的华工每人领到一个刻有身份编号的铜手镯和一套干净的衣服。就这样,毕粹德、马春苓、孙干等14万华工开始了他们的“艰辛之旅”,一部分华工途经苏伊士运河或者好望角到达法国,而大多数则是跨越太平洋,穿过加拿大,再横跨大西洋前往法国。旅程充满艰辛,华工们不仅要忍受波涛汹涌的大海。还要面临德国潜艇的威胁,最终抵达一战西线战场。
西线战场上的“中国苦力”
1917年12月。在经历两个多月的漫长征途后,运载着3400多名华工的客轮抵达法国,马春苓很快被分派到了北部加来省一家工厂负责运输木材。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距离“战线尚百余里,故未冒子弹之险,未遭颠沛之苦”。即便是这样,华工依然能嗅到硝烟的味道,甚至面临来自炮击轰炸和毒气弹的死亡威胁。
尽管身在混乱、时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常常被西方人蔑称为“苦力”(coolies)“中国佬”(Chinks),,华工们仍然创造了巨大的功绩。一本由英国军方1918年编写的《关于华工的信息》的小册子称,中国人“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如果管理得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他们的能力令人惊讶”。
了解华工们的日常工作,英国人约翰·德·露西珍藏的照片更加直观。2018年10月底,一场在山东威海召开的一战华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见到了这位一战英国军官的后代。“我爷爷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是一名一战军官,他汉语流利,与中国劳工军团共处了三年。2014年,我在伦敦家中偶然发现十几张玻璃幻灯片,这些爷爷拍摄的照片上的主人公正是中国劳工。”露西说。
在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上,华工们在欧洲战场从事着多种多样的工作:挖战壕,修铁路,装卸货物,在火药厂、兵工厂、化工厂和造纸厂等地方工作,有的华工甚至成为修理坦克、飞机的熟练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大约1500天。但是对于许多华工来说,他们的战争记忆是更为漫长、恐怖的,因为他们战后还要留下打扫战场,埋葬死者。“战后有成千上万被废弃的炮弹。‘华工军团’的任务就是清除那些尚未爆炸的炮弹,这非常危险。”露西说。
许多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在法国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为法军服务的华工更是做到了1922年。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确定战时究竟有多少华工在法国为协约国的事业献身。徐国琦说,可以确信,由于敌军炮火、瘟疫和伤病,至少有3000名中国人在欧洲或是去欧洲的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华工参与并见证了一战,我们有话语权来探讨战争与和平”
“吾十余万华工,离祖国,涉重洋,冒锋镝,历艰险,出生入死,参加欧洲大战,以博无上之荣誉,此实为吾国外交一页光荣史也。”时任华工翻译的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自序中如此写道。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华工后裔以至于中国人应当如何看待一战华工?
2008年,程玲在法国为爷爷扫墓时,法国欧华历史学会华侨曾作诗:今朝祭拜了心愿,历尽沧桑友谊珍。喜泪飞流同振奋,中华崛起发豪吟。“在爷爷长眠的墓地里,华工墓碑上刻着‘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等字样,虽然我现在连爷爷的模样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捍卫文明和自由的经历已经被历史记住了。”程玲说。
“我认为爷爷他们那些华工是伟大的一代人,他们参与了一战,流血流汗地参与拯救了欧洲,某种程度上他们就代表了中国。”马京东说。
尽管华工被称为“苦力”,但是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仅吃了苦,还有巨大的影响力。徐国琦认为,因为华工,中国让英法等国免于人力资源破产的风险,参与拯救欧洲,向世界展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景和能力;同时,中国由此可以向德国宣战,名正言顺地成了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主持中国公道。
14万华工就是14万使者。美国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报》在1918年宣布,华工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西方一直认为一战奠定了现代国际体系,比二战都重要。一战结束后,西方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人类要爆发这么惨烈的战争?而中国华工参与并见证了一战,我们有话语权来探讨战争与和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张俊义说。
近年来,从学术界到政界,东方或西方,华工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受到认可,纪念华工的活动受到更多人关注。去年11月,欧洲首座一战华工雕像在比利时波普林格市揭幕;英国也在纪念一战停战99周年的正式活动中首次纪念一战华工;今年9月,一战华工雕像在巴黎里昂火车站落成。2018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一战赴法华工致敬,表示“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