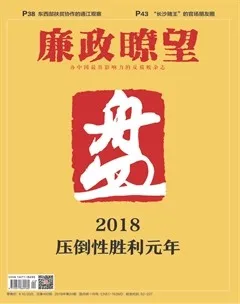探究曾国藩以索贿为荣的原因

个人操守难以抵御文化性的腐败
廉政瞭望:选择清朝这段历史,是因为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特殊性吗?
刘诚龙:努尔哈赤以“13副铠甲”起兵,建立了一个疆域阔大的大王朝,这不是蛇吞大象,算得上是蚂蚁吞大象了,可悲的是,推倒大清的也不过是一个连一个营的规模。
李鸿章将大清兴亡,呼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言不虚,这不是以前一个朝廷换另一个朝廷之变局,而是整个制度在翻篇,千年封建帝制被结束了,这对中国影响要有多深刻就有多深刻。
清朝离今不远,从读史角度来看,确实是一座富矿。大清官人千千万,大清官人做官法子万万千,贪官、清官、庸官、能官,循吏恶吏、良臣奸臣,组成了一副色谱纷陈百官图,确实有料。但是,百官做官法,不是我要说的重点,对宫廷斗争,我兴趣不很大,更多注目的是百官其做官,如何去影响一国之兴亡,这才是需要去思考的。
廉政瞭望:你在书中写到,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人,也免不了为别人题词之类的,拿不到钱还大发脾气,这种官场陋习古已有之,似乎一两个清官不足以改变这种体制性、文化性的弊病?
刘诚龙:曾国藩“中举”了,赢得了当官资格了,他就拿着这个“进士”名号,到处去吃大户,去打秋风,人家不给或给少了,他还大发脾气,这与曾国藩的理学代表及“曾圣人”形象大不符。但是,在当时这种变相索贿却不是“羞耻”,整个文化对此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历史上有些时期,官员将贪当一种能力,你能贪,是你有能力,你贪得多,你是能力强,笑贫不笑娼,史上很多时期,价值观真乱套了。
到了后来,曾国藩很少以“题词”之类手段去弄“灰色收入”、大搞“陋规”福利,个人操守树立起来了,但不意味着他彻底改造了官场,他对官场“潜规则”依然是俯首称臣的。比如,湘军剿杀了“太平天国”后,要向户部报销“军费”,不管什么名目,哪怕是将士流血牺牲,户部潜规则是都要给行贿,给“小费”,给“加班费”。这回,皇帝高兴,“亲自”批示财政,可以不用户部审批,直接报销。曾国藩高兴坏了。但是,曾国藩先前谈妥的8万两“贿款”,一分钱不少,还是给了户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个人操守难以抵御体制与文化的腐败。
起用一批批清官能官循吏良吏,也可以以量变促质变,若好官在数量上超了坏官,能赢得“少数服从多数”之“效应”。事实上,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有腐败,但不严重。
廉政瞭望: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名臣也相继在书中登场,如果按照你个人的喜好排序,这三名晚清重臣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刘诚龙:前人曾经点评过大清部分官员: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这个评论指定不对,塞了个人私货,端方算甚“有学有术”呢?按喜欢之由低到高,我自个这样来排列: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
李鸿章自称是大清裱糊匠,他做官确乎是很“浆糊”的。他在处理与列强关系时,也有其骨气,有其难处,但李鸿章做官,爱搞小圈子,多起用其乡党;李鸿章另一个问题是,他没有超强意志力,做一个承平宰相或可以,问题是他处于“乱世”啊,他做不了“救时宰相”。在与列强较量中,他往往自输阵脚,仗还没打起来,就“投降”,就“输诚”。
张之洞最先做的是“清流”,骨子里有一股书生气,是大清末年一位难得的明白人,武汉城市建设,应该感谢他。张之洞的明白也是有限度的,他任湖广总督,行政算得上比较开明,搞洋务,发展经济有他一套;晚清时候,uXBsHnReHYWnnz6Zo1SLwg==湖南成为“新力量”,跟张之洞也是很有关系的。当时湖南巡抚是陈宝箴,改革力度很大,张之洞多是支持的。但对湖南越来越呈现出的“赶超”姿态,张之洞却是压制的,对康梁思想在湖南的传播算是“始乱终弃”,他也没能成为“救时宰相”。
左宗棠在大清乃至在整个家天下制度下,是一个“异数”。他个性鲜明,为政强悍,是一头闯入“瓷器店里的公牛”。左宗棠有很强个性,更有很强的家国情怀,他跟曾国藩绝交,不是个人之间有私仇,而是对曾国藩甩“清剿乱臣贼子”之担子大不满。为家国计,曾国藩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左宗棠是抬着棺材进新疆,李鸿章从来没有过这种壮举。敢于担当,敢于亮剑,有个人操守,有家国情怀,官场最需要的是左宗棠。虽然他有他的弱点,如在培养官员上,他比不上曾国藩。
思想需要“杂交”
廉政瞭望:你写过一本叫做《民国风流》的书,如果说《一品高官》的属性是“冬天”,那么《民国风流》就属于“春天”,你推崇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精神和气质?
刘诚龙:我不把民国当天堂,同样,也不把民国当地狱,民国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过渡,远没有完成她该完成的任务。
民国知识分子有特立个性,有独立思想,有自由精神,我更想赞颂的,是他们有家国情怀,有天下担当,不管他们秉持甚思想,不管他们取何反叛姿态,他们都是在为国家前途想,为人民命运忧。这不比后来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忧职称,忧工资,忧自己位置,即使他们发宏论,内里也藏着“小九九”,这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民国人,或者思想不成熟,很粗粝。然则再粗糙的利国主义者,也强于与好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民国士子的成长,与以前大不同的是,他们既受传统浸淫,更接受外来文化熏陶,不管他们以多么激烈地反传统姿态示人,其实传统文化已烙印在其基因之中,他们比我们一些对国学推崇备至者,更富有国学底蕴。这一点非常重要,植物杂交有优势,能优产,思想杂交也有同样效力,比植物成长更有优势更能优产。
廉政瞭望:作家王跃文称你是潜伏在官场的“文学特工”、官场“深喉”,有人说你写的历史“好看”,你是如何在真实与好看之间平衡的?
刘诚龙:写得好看,并不是乱写。我特别看重历史真实性,包括细节,以前喜欢从野史里取材,现在多从正史,但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很大程度上,我是借历史之旧瓶,来装我思考之新酒。我常常最感觉脸红的是,文章中有硬伤,若有人指出,感激之余,立刻在自己原文中去改正。
历史上有很多故事是挺好玩的,本身情节十分生动而富趣味,我读历史,对这些故事最感兴趣,纳入文章中的,就是这样“微历史”与“趣历史”。我个人偏好,喜欢用“歪一点”的俚语、俗语、网络用语,去描述古人,去煮历史。自吹下鄙人作文,用词是“歪”的,用心是正的,虽无能却有梦——梦想世界变得更好。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本刊特约作家、历史学者刘诚龙的新作《一品高官》,以幽默生动的语言,聚焦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等清朝“大人物”。作者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寻出各有个性各有特点的人物,还原了当时的官场生态与社会背景。从这些高官的故事中,读者能够窥见历史的辛酸与无奈。本刊日前专访了刘诚龙,他希望在“颂清官、扬正气,又刺贪官、惩腐恶”背后,大家应有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