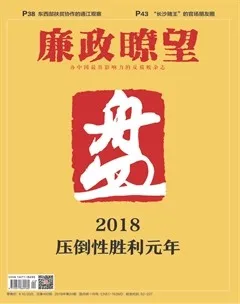映秀茶人蒋维明:一壶好茶 一道人生

蒋维明时常会想起1993年的那个夜晚。
那 年他二十二岁,和朋友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某天喜鹊落到头顶上,一天就挣下一万块钱。在普遍月薪两三百元的1993年,一万元无疑是笔巨资。年轻的蒋维明被狂喜击中,但在激动时刻,他没去喝酒吃肉,而是花七十块钱,买了一两茶。
多年后,蒋维明向廉政瞭望记者回忆起那杯茶,入口的淡然和涌上喉头的回甘已经变得模糊,但那细微的、绵长的恬适感却如同热茶飘起的袅袅青烟,还长久地留存在回忆的罅隙里。
“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那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蒋维明说。
茶祥子:涌泉之恩亦可滴滴相报
若是来汶川映秀,是一定要到茶祥子坐一坐的。
几方木桌,两壶黑茶,室外阳光和暖,室内茶香氤氲。在淡雅古朴的茶坊中品茶,满是宁静祥和。
在茶祥子喝茶都是免费的,借用蒋维明的话是“不论皮鞋、草鞋,草帽、高帽,端起盏喝茶、放下碗走人。”从2012年至今,蒋维明坚持每天给大家熬一壶茶,回馈着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
“实际上,不是我要做免费茶,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蒋维明介绍道。不仅在映秀,其实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朋友前来拜访,奉上一碗茶水是不可缺少的礼仪。当蒋维明来到映秀时,这里的老乡刚回迁一年,大家都处于高强度工作的状态,晚上吃完饭,就爱喝喝茶、聊聊天,后来人越聚越多,来蒋维明这儿喝茶,就逐渐成为了村民们约定俗成的习惯。
“喝茶都是免费的,平时没事就爱跑这儿来。”映秀镇的一名村民说道。
茶坊的落成也包含了蒋维明的感恩之心。蒋维明的父亲常年生活在映秀,住所离震中直线距离仅15公里。那年地震,他和邻居结伴逃到山脚,混乱之中,有人送衣服,有人施粥,都是不相识的人,一辆出租车见着他们,立马冲过来说:“我送你们离开。”他们这才得以逃生。而那位好心的司机最后也不肯收下一分钱。
当时,蒋维明还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那是他在北京生活的第十八个年头。每次过年回家,待不了四五天就要走,一切生活细节都模糊在父母渐渐斑白的鬓角里。直到他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地震的报道,“当时真吓惨了,心皱成纸,才明白什么叫生离死别。”安定之后,他急匆匆赶回四川,看到老父亲的那一刻,他决定再也不走。
人虽在,家园却满目疮痍。
某个晚上,蒋维明坐在床边,父亲在一旁整理相册,对坐无言。前面一摞略泛黄的照片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往下翻,却风云突变,父亲生活了九年的房子,经历地震摧残,只剩一地狼藉。
他端详着照片,禁不住泪流满面。
蒋维明从未见过父亲掉眼泪。父亲16岁参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是铁骨铮铮的硬汉。此时他的心里忽然被难以抑制的悲痛填满,埋藏的种子融化了,到汶川的想法悄悄萌生:他想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参与灾后重建,守住父亲心中的故土。
如此,便有了现在的茶祥子。
“房子是租来的,茶叶是老乡帮忙采的,茶坊也是有了大家才有了人气,我无以为报,只有把老乡交给我的茶叶炒好,给大家奉上一杯热茶。”蒋维明说。
蒋维明:我是映秀的亲儿子
1971年,蒋维明出生于苍茫空旷的西北戈壁滩,这里人烟稀少,不常见着人,邻里关系反倒格外亲密。蒋维明从小就吃百家饭,在长辈的关爱中成长。
2012年,蒋维明接受阿坝州文新广局的邀请,来映秀发展茶艺。刚来那会儿,全部家当就只有两口铁锅、一床被子,晚上就在马路边上铺席子睡觉。镇上的村民杨和江看到了,毫不犹豫地邀请他到自家客栈居住。不仅如此,杨和江和堂兄杨和祥忙完白天的工作,晚上还来帮忙揉茶、炒茶,常常陪到夜里一两点,直到三四个月后,蒋维明逐渐稳定下来,家人也慢慢搬到映秀。
在艰难的初创期,杨氏兄弟这般热情的映秀人给了蒋维明家人的温暖,一如当年在戈壁滩的亲人们。也是因此,蒋维明时常自称是“映秀的亲儿子”,每逢说到此处,被岁月垒叠的皱纹便伸展开来,泛着一股笑意。
做茶,离不开优质的茶源。平日里,蒋维明得闲就四处寻茶山、找好茶,村民也贡献了不少力量。从2012年至今,蒋维明收购映秀各村村民采摘荒荒茶叶、野生绞股蓝、野生金银花300余万元,直接让村民参与利润同享,方式是以高于市场价数倍的价钱收购新鲜茶叶:收购绞股蓝10元一公斤,高于全国平均收购价2至3倍;收购金银花40元一公斤,高于全国平均价4至5倍……蒋维明最爱见到的,就是村民们获得酬劳时的笑脸。大家的腰包鼓了,制茶坊做起来了,他的心里也变得踏实。
在他看来,高价收购是理所当然的。映秀四面高山环绕,悬崖绝壁,震后很多小路都已不在,且当地没有规模化的茶场,采茶十分费时费力。“如果村民采茶一天挣不了几百块钱,怎么对得起这份付出呢?”
一开始,采茶的村民大多是60岁到80岁的老人,后来,渐渐有了40岁、20岁……采茶的村民在年轻化,这也是蒋维明很乐意看到的现象。
“老乡把茶采好,我把茶做好,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蒋维明说。
自立自强的汶川精神也赋予了茶祥子新的意义。如果说以前的茶祥子是指“茶之韵,祥气和,子吾归”的匠人精神,而现在,它是在匠人精神的基础上注入了劳模精神:像参与灾后重建的人们一样任劳任怨,像骆驼祥子好好拉车一样好好制茶。
蒋维明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通过不断努力,“把农民变成农工,农工变成技工,技工变成教练,教练变成传承人”。他希望薪火相传,把这门茶艺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
茶文化:走向世界大舞台
1996年,对茶心驰神往的蒋维明曾慕名前往某茶叶产区,所见所闻却令他大失所望:不少制茶人脸热擦汗,头发油腻,做茶环境很不卫生。
基于那次经历,他认为,当前的制茶问题主要在于设施落后,管理意识落后。来汶川做茶,无异于一次大胆的冒险。“我借不到任何历史文化名牌,连文人墨客的笔墨都借不上,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一场持久战。”蒋维明说。
2014年,汶川提出“大美养眼、气候养身、生态养康、文化养心”的新型旅游发展战略,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茶树的生长也愈发旺盛,对于村民们采来的茶,蒋维明却从未放低标准。“茶叶不能经人工处理,必须是荒荒茶;雨天采的茶不收,茶叶的匀净度、高矮胖瘦,都有严格的标准……”他说,作坊里配备了电子显微镜、低温速冻箱,保证做茶干净卫生。“我坚决要把非物质文化的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管理结合起来,我做的茶,一定要做到全国一等一。”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2017年,蒋维明的茶叶作为唯一的中国茶登上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一带一路”沿海上丝绸之路、“盛世公主”号邮轮,沿途巡展10多个国家。春节前,“大土司”黑茶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展。
“这是一生值得回忆的经历。”蒋维明说。茶不仅仅是饮料,它更承载着一种茶文化,外国友人对中国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归根结底,是通过茶在不断了解中国,而中国则通过茶不断走向世界。
“我们通过一片瑞叶,带给大家健康,难道不应为祖先感到骄傲吗?”蒋维明说。
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走进了“茶祥子”制茶坊,察看传统黑茶制茶工序,体验酥油茶制作流程。“激动,太激动了。”回忆起当日场景,蒋维明难掩激动神色。
“做得很有文化。”习总书记对这款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走向世界的民族茶品牌赞赏有加,让蒋维明倍感温暖和鼓舞。
制茶二十多年,茶已成为蒋维明心中的一面明镜。“与茶相伴的时光仿佛一个重叠的虫洞,2018年和1993年的我的观念重叠了。”他说。
1993年,一两七十元的茶叶让蒋维明感到前所未有的恬适安然,岁月流转,而今他又用了七年,把茶作为一份瑞叶带给人安心健康的观念植入制茶工艺中,在一张白纸上构建出梦想,茶祥子制茶坊、大土司黑茶都是梦想结出的硕果。
“采好一份茶叶,泡一壶好茶,做一个好人,这是我的不忘初心。”蒋维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