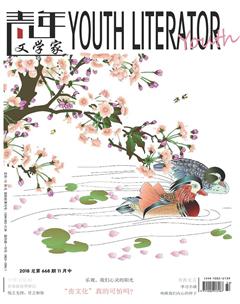蒲松龄的聊斋俚曲创作
卢梦雨
摘 要:蒲松龄创作的聊斋俚曲,是其在完成《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后的崭新尝试。他试图通过创作各种题材的俚曲并进行搬演,来实现自己回报乡里、匡正风俗的“救世”理想。在这些用淄川当地方言创作的俚曲中,即有对贪官污吏的愤怒揭发,也有对愚夫泼妇的奖善惩恶,可以说是一种可以表达作者“真性情”的俗文学。
关键词:蒲松龄;俚曲;俗文学;救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05
引言:
蒲松龄在国人中的印象是与《聊斋志异》这部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但他的著作并不仅有《聊斋志异》这一部作品。据清雍正三年蒲松龄生前好友张笃庆之子张元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记载,尚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另外该墓表碑阴还记载了14种“通俗俚曲”的名称[1]。人所共知,蒲氏生前偃蹇潦倒,著述无力梓行。除《聊斋志异》一书辗转抄录刻印,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外;由于蒲氏后代生活困窘,余著蚀毁散佚严重,以致“先生手泽十损八九”。当然,这些“俚曲”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在淄川及其周边地区博山、周村、明水等地被乡村戏班不断搬演,因而得以存留。经路大荒先生几十年的辛苦追访与整理,在他整理的《蒲松龄文集》中我们可以见13种。所遗之《琴瑟乐》,则见于日本学者平井雅尾所著《笔者所收藏之聊斋遗书》中。
现在的14种俚曲,从曲文内容来看,都是用明末清初的山东民间流行曲调和淄川本地方言写成,是不折不扣的“俗文学”。这些俚曲,与他创作的《聊斋志异》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知道,《聊斋志异》是用古雅的文言写成的,在他所处的年代主要的阅读传播对象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聊斋志异》在当时是贵族化的、文人化的。
《聊斋志异》成书后,首先就得到当时的诗坛宗主王渔洋的激赏,随即文名便在山东地方官员士大夫中不胫而走,甚至使蒲松龄成为济南臬台喻成龙的座上宾。《聊斋志异》的成功,使蒲松龄的文名流布海内,长舒一口多年来科场蹭蹬、屡试不第带给他的悒滞之气。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聊斋志异》这部作品也使蒲松龄跻身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小说家行列,成为其文学史地位的写照。与《聊斋志异》相反,聊斋俚曲是彻头彻尾“平民化的”的作品,是蒲松龄专门为当地百姓创作的。他不但使用淄川方言,甚至使用了当地方言中大量非常粗鄙的詈语、歇后语、俏皮话等。因此,我们根本见不到当时文人士大夫对这些俚曲有过只言片语的评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聊斋俚曲没有文学价值或者文学价值很低。聊斋俚曲在当地几百年的搬演传唱中,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恰恰说明了市井细民对这些作品的喜欢。时至今日,根据蒲松龄原作改编的吕剧《墙头记》依然是鲁中地区最受欢迎的剧目。
读《聊斋志异》,可以充分领略蒲松龄“文章经世”之“大雅”;看聊斋俚曲搬演那些乡村生活热闹场景,又可以体会一个乡塾先生“妇姑勃谿”之“大俗”。这“大俗”与“大雅”合起來,方才是一个完整的蒲松龄。那些对人物极度地夸张与丑化,那些对市侩风习不加任何掩饰地戏弄调侃,甚至于对民间言语“恶趣”的放浪表现,都深浸着作者骨子里对于民间原始艺术趣味的狂热追求。创作这些俚曲,实质上是蒲松龄对自己“借花鬼狐妖显名于世”的文学动机所进行的一种自我否定与批判。这些“其俗在骨”的俚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自己所塑造的“孤愤”形象,但又提供了全面认识和理解蒲松龄文学世界的新通道。
一、聊斋俚曲的创作历程
自明中叶以来,民间俗曲非常流行。俗曲多由农村的民歌衍变而来,经过酒楼茶肆演出艺人的再加工,又不断地衍变新声,甚至是组成集曲或套曲。在表演过程中根据场地和演出形式的需要,配以琵琶、三弦、檀板、鼓、筝等乐器,形成了大量形式规整、结构严谨的曲牌,比如“耍孩儿”、“驻云飞”、“寄生草”、“劈破玉”、“打枣杆”等。由于出现时间、演出地区、表演形式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民间俗曲也被称为“俚曲”、“时曲”、“曲调”、“小曲”、“小调”等。这一类民间俗曲,不但受到了市井细民的欢迎,还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关注、欣赏和推许。
嘉靖年间,李开先便搜罗正德、嘉靖年间流传甚广的“山坡羊”、“锁南枝”两种俗曲曲文,编成《市井艳词》一书,并称赞说,“真诗只在民间”。“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也称赞“劈破玉”、“打枣杆”之类的俗曲,为“真人所作,故多真声”。此后,更有冯惟敏、赵南星、刘效祖、薛论道等一些文人开始模仿民间流行的俗曲,创作具有文人气味的“俗曲”。这种“向真”、“向俗”,发掘民间艺术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的以李渔、袁枚为代表的一批文人。
山东是明清时期北方俗曲流传衍变的重要地区之一。搜集整理民间俗曲的李开先、模仿民间俗曲创作的冯惟敏等人,都距离蒲松龄出生地——淄川不远。从蒲松龄与其同窗好友张笃庆、李尧臣的诗词唱和、来往书信可以看出,他少年时期受乡村文化熏陶,爱听戏,会唱小曲。淄川名流唐梦赉弃官归隐后,折节与青年塾师蒲松龄交往,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华,曾作《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留仙》描述他们的交往,“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亦传觞”。“绰然堂”,即蒲松龄馆东毕际有会客、听戏的地方。毕际有的母亲王氏老太太(王渔洋的从姑母)非常喜欢看俚曲,为了孝敬母亲,毕际有长年雇佣戏班在家中演出。词中以柳永之字“耆卿”指代“柳泉居士”之“柳”,即指蒲松龄。“还度曲”说明蒲松龄不但能创作俚曲,而且其才能早为友人所熟知。
这种极其良好的俚曲流传环境,培养了蒲松龄的俚曲爱好,锻炼了他的俚曲创作才能。这正是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之余,还能煞费苦心地创作聊斋俚曲的心理动因。
(一)14种聊斋俚曲创作阶段考辨
蒲松龄从什么时间开始创作俚曲,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不过学界一致认为,其俚曲创作如《聊斋志异》的写作一样,并不是在短时间内集中写作的,而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时间跨度最起码在30年以上。
1964年,日本学者藤田佑贤根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俚曲抄本,对《琴瑟乐》、《穷汉乐》、《俊夜叉》三种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了推考。其中,对于《俊夜叉》创作时间的推考可信度较大。此抄本中有“康熙爷己卯年,宗亓人四十三,婆子大他一年半”一段表述时间的曲词,康熙皇帝当政期间的“己卯年”为1699年(清康熙38年)。藤田佑贤据此推断,《俊夜叉》应当作于此年或稍后,此时蒲松龄年龄在60岁左右[2]。
根据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的考证,蒲松龄大致于清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这段时间,开始断断续续地创作《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自康熙18年(1679年)前后进入创作旺盛期,继继绳绳、笔耕不缀,一直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康熙36年(1697年)或稍前,蒲松龄完成了《聊斋志异》初稿本16册中的前15册[3]。此后,虽然又增加了一些故事,但其创作热情已经消退,只是对其进行一些缝缝补补的更正、删定工作了。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此时蒲松龄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1697年,蒲松龄在自家院内为自己加盖了一个小书房,命名为“面壁居”,并赋七律四首以纪此事。其一有云:“搦管儿曹呈近艺,涂鸦童子著新书”。并自注其诗曰:“幼孙(长孙蒲立德)学著小说,数年成十余卷,亦可笑也”。此时的蒲松龄心情大好,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与儿孙辈的交流指导上,写了很多表现家族生活乐趣的纪事诗。另外,他辑《小学节要》,选宋人七律诗,明显是要用于指导儿孙辈的学问。此时,他已经不再执著于呕心沥血地构思“狐鬼故事”,开始乐于从事一些带有消遣娱乐性质的著述了。
1699年前后,蒲松龄创作了《俊夜叉》。这是个喜剧小段,写山东历城县宗亓人因喜欢赌博而输尽家产,被泼辣妻子张三姐好一通臭骂恶打,从而痛改前非、刻苦经营、重振家声的故事。这个爹娘老子都管不服的游荡子,却因妻子性情泼恶而自立成人。这令人忍俊不禁的戏谑,恰恰是蒲松龄此一时期课教儿孙、心情怡怡的典型写照。应当说,如何“诱化乡间痴顽不肖男女改恶从善”,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蒲松龄转向俚曲创作的心理动因。
1985年,辽宁大学高明阁教授在第二次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长篇论文《蒲松龄俗曲创作篇第考》,运用多种方法初步考定了14种聊斋俚曲的创作顺序。借助作者诗文中涉及的时事,能够比较准确考定创作时间的作品有三种:《禳妒咒》(1702年前后,作者63岁左右)、《磨难曲》(1708年之后,作者69岁以后)、《墙头记》(1711年或稍后,作者72岁或以后)。另外,他从聊斋俚曲中《耍孩儿》曲的运用、曲牌联套的形式、曲牌用字的形式,考定《慈悲曲》、《姑妇曲》、《蓬莱宴》、《福贵神仙》、《增补幸云曲》、《寒森曲》、《翻魇殃》这七种作品均晚于1699年,也就是《俊夜叉》的创作时间。
从藤田佑贤和高明阁对聊斋俚曲创作时间及顺序的推考来看,14种俚曲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创作于蒲松龄60岁以后。如此以《俊夜叉》为界,可将蒲松龄的聊斋俚曲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蒲松龄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上,俚曲的创作只是偶一为之。这一阶段创作的俚曲,多属应景之余,情节简单,形同小令,调侃逗乐的用意十分明显;艺术形式不完整,具有很强的尝试性。第二阶段,蒲松龄在完成《聊斋志异》的创作后,创作兴趣就转移到了聊斋俚曲的创作上。这一阶段的作品,蒲松龄完全立足于本地乡情民俗,力图把淄川农村生活景象的方方面面完整地呈现出来。他彻底抛弃了以前那种刻意保持的所谓文人雅趣,以一个淄川乡间老农的语言、趣味甚至是地域执念,任性挥洒,为本地乡人创作地方小戏,直至身体衰老到拿不动笔为止。
(二)《聊斋志异》故事情节的再创造
聊斋俚曲的体裁差异性很大。这14种俚曲,文本结构方式介于鼓词与戏剧之间,具有较强的随意性。首先,这些俚曲不像当时的戏剧一样分“场”、分“折”、分“出”,而是像长篇章回体小说一样分“回”。第二,无戏剧中的“科”、“白”,而是如小说叙述一般直接插入人物动作、语言、场景。第三、俚曲的人物性格刻画,往往通过作者直接的叙述和议论来完成,类似于鼓词。在这些作品中,只有《禳妒咒》、《墙头记》、《磨难曲》这三种俚曲具备相对比较明显的戏剧特征。
这14种俚曲的取材来源也比较复杂。其中,《琴瑟乐》写新婚男女鱼水欢合,语涉儇浅、旖旎放荡;《穷汉詞》写穷汉生活之困窘,诅天地之不公;《墙头记》写不孝子之粗鄙下作;《俊夜叉》写悍妇拯夫之殴打骂詈;这些情节显然来自于民间生活“本事”。《蓬莱宴》取自民间传说,写王母娘娘侍女吴彩鸾与凡间书生文萧之间的仙人之恋;然而不管是蓬莱岛的神仙大聚会,还是小两口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都带有深厚的淄川农家色彩。这说明,刨除了神仙道化的浪漫色彩,《蓬莱宴》所描述的图景,不过是蒲松龄自己心目中理想化的家庭生活。男女情事、穷困乡邻、对父母赡养不周、悍妇骂街、夫妻恩爱,作者随手采撷民间生活“本事”,了了数笔勾勒,即成鲜活乡野画卷。
《丑俊巴》是一个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再造型艳情故事,让《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来了场超时空孽恋。猪八戒取经回来得成正果,受封净坛使者;某日在闲观地狱景象时,忽然见到了被武松杀死的潘金莲亡魂,竟然害起了相思病,以至在梦幻中与潘金莲云雨情浓。
《快曲》则依据三国故事中“捉放曹”的相关内容改写而成。在这部作品中,蒲松龄改变了“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的情节进程。曹操虽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关羽,逃过一劫;熟料行至大路,张飞突然杀出,将曹操刺下马来,割去首级。诸将得胜回营后,便赌射曹操头颅,饮酒骂曹为戏,最终刘备喝得酩酊大醉,一脚跌在地上爬不起身。蒲松龄的改写,迎合了民间那种“奉蜀汉仇曹魏”的正统史观。
《增补幸云曲》即言“增补”,则必有所本。该作品取材于明代杂调传奇《嫖院记》或《正德记》,叙说正德皇帝朱厚照扮军汉去山西大同宣武院嫖妓之事。在这部作品中,蒲松龄以戏谑笔法否定了皇帝是所谓“真龙天子”的传统成说,第一回便说朱厚照是“觜火猴儿”下凡,此后在第四回、第六回又借不同人物指出正德皇帝是一个到处“闲游闲耍”的“混帐朝廷”,是一个“贪花恋酒”、狂嫖滥赌的闲汉光棍,跟在妓院里与他拼权斗富的纨绔子弟王龙是一丘之貉。
这三种基于经典文学戏剧作品的再加工再创造,完全仰仗蒲松龄扎实的经史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开阔的社会视野、纵横不羁的文学想象能力。这种“借他人酒杯消胸中块垒”的写法虽然可以翻空出奇、老树新花,但由于受到定型文学作品在人物、情节上的限制,很难创作出神采焕发、自出机杼的精品。
刨除這些“嫁接式”的尝试性创作,蒲松龄更多还是从《聊斋志异》中汲取俚曲创作题材。因为他自己那些最富有个性创造力的人物、故事、情节,都已经奉献给了《聊斋志异》这部巨著。全力创作聊斋俚曲时,蒲松龄已年过六旬,身体虽然健康但精力总比不过青壮年时期。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蒲松龄社会活动的减少,其汲取鲜活文学题材的渠道也在萎缩,这也是他那些现实性俚曲皆取自乡邻鄙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题材并不是作品优劣的决定性因素。《墙头记》所述张大怪、张二怪忤逆不孝之事,即源于蒲松龄亲见之人生惨剧。1711年,他有感于邻近一位80多岁的老翁由于一子一孙皆不尽养亲之义而至衣食无着、行将奄毙的情形,愤而写下《老翁行》以做谴责;并以此做为素材,创作了《墙头记》。这部作品是蒲松龄影响力最大的俚曲作品,在以后几百年内被不断加工改编,成为山东梆子、吕剧、五音戏等剧种的经典剧目。不过,从内容上看,俚曲原作人物、剧情都比较简单;从形式上看,所用曲调也少得可怜,从头至尾就是一个《耍孩儿》。
因此,蒲松龄更多还是从《聊斋志异》中选择那些含有广阔社会生活内容的篇目,来加工、扩展、改造为俚曲作品。使用这种方式来创作俚曲,蒲松龄不用耗费更多心力去构思新的故事情节,只需要按剧情演出需要,细化人物的语言、动作、情态、心理。减轻了内容方面的压力,蒲松龄则可以使用更多的曲调组合来丰富演员的唱词。既为俚曲,则需要按曲牌填词,这是一个需要耗费巨大精力的高难度写作。这些曲词是聊斋俚曲的精华,其别具一格的人物造型能力,直追“曲圣”关汉卿。凡从《聊斋志异》改编的俚曲,一般会长达二三十回,情节相当曲折;同时也会运用五六种甚至是十几种曲调来组成大型套曲,形成复杂的俚曲体式。
这14种聊斋俚曲中,有7种由《聊斋志异》的小说改编而成。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小说———————————俚曲
《张诚》————————《慈悲曲》
《珊瑚》————————《姑妇曲》
《张鸿渐》———————《富贵神仙》、《磨难曲》
《商三官》、《席方平》——《寒森曲》
《仇大娘》———————《翻魇殃》
《江城》————————《禳妒咒》
二、聊斋俚曲的“救世”情怀
蒲松龄的一生,孜孜于科举考试与文学创作,无暇他顾,故与其家人一直处于极度困窘的生活状态中。蒲松龄兄弟四人成家后,几个妯娌禀性泼悍,经常为一些琐事吵得鸡犬不宁,最后只能分家析产单过。不过,禀性良弱的蒲松龄夫妇分得的房产最差,“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随着子女的增多,这透风漏雨的老屋亟需翻盖、扩建。然而,蒲松龄一直到49岁那年才翻盖了房子,还是茅草顶的。康熙时期一间瓦房的价值大概是11两白银,差不多相当于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并不算贵。不过,对于不做官不经商的蒲松龄来说,瓦房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享受,终其一生也没能住得上。
蒲松龄19岁考中秀才,并以县、府、道试第一的成绩获得廪生资格,每月可以获得六斗米的政府补助。除此之外,便是耕种分家获得的20亩薄地。可这对于蒲松龄一家七口来说,只能勉强糊口。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蒲松龄只能四处奔波,四处应幕、设塾,直至40岁设帐于西铺毕家,才获得了相对比较丰厚稳定的收入。尽管如此,他依然又用了10年时间,才攒够翻盖老房所需费用。对于营造居所付出的辛劳,蒲松龄深有感触,“聚垤蚁为风雨计,衔泥燕作子孙谋。茅茨占有盈寻地,搜括艰于百尺楼”(《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然而,终年设帐于西铺毕家,一年之中仅能回家5次,每次不足10天。这种聚少离多的谋生方式,却淡漠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也影响了蒲松龄对于子女的教育。对此,他深感愧疚,“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子笏》)。所幸,蒲松龄的四子一女非常争气,有三人考中秀才并积极替父母分担家用。至50多岁,蒲松龄的家境大有改观。
正因为有了这段艰苦谋生的个人经历,蒲松龄深切理解农村民生疾苦。随着年事日高,家境好转,他早年那种由科举不遇所造成的孤愤心情渐渐平复,开始更多地去关注世态人心。在他年届花甲之际,淄川一带连续几年水旱灾荒交错,造成了农村生活普遍凋弊。庄稼欠收,春粮难继,恶役却不断下乡催逼赋税;贫民卖儿鬻女,中产者粥菜裹腹,富户卖地屯粮自保。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形下,世情浇漓,人心沦丧。逃荒者曝尸于道却无人殓埋,弃养老弱者却毫不愧疚,分家析产大打出手却理直气壮。水旱灾害、贫官恶吏的交互作用,严重伤害了支撑乡村社会稳定的人伦亲情,乡民们普遍向着自私、无耻、愚鲁、偏狭、粗野的“恶性”状态畸变。
耳闻目睹这些社会窳败景象,蒲松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文名和资深廪生身份,四处游说官员富绅开仓赈济、革除弊政,扶助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则使用本地方言创作通俗易懂的俚曲,来缮风俗、正人伦,力拯人心之溺。其长子蒲箬将蒲松龄创作聊斋俚曲的用意,讲得很清楚:
“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巿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陶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4]
(一)对“食民之狨”的揭露和规劝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用“狨”和“猕”的关系来比拟贪官污吏与老百姓的关系。贪官污吏就像“狨”,检视老百姓的肥瘦并作上记号,按记号把人撕开吞食;但老百姓就像“猕”一样支楞着耳朵跪在那里,任由他们吞食而不敢做任何反抗。蒲松龄不但描绘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而且一直在追问造成这种奇怪景象的原因。在《聊斋志异》中,他通过一系列篇目,描写了大量横酷贪暴的官吏形象,并对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并期望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比如,《潞令》中那位“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的县令宋国英,就遭到冥报,暴毙于公堂之上。或者如《席方平》中,那些勾结在一起徇私枉法的城隍、郡司、冥王,最后统统受到了巡检地狱的特使二郎神的惩治。在创作《聊斋志异》时,这种对于普通百姓的肆意凌虐,蒲松龄往往将其归咎于“牧民者”个人道德品质的败坏和封建官场“官官相护”的恶劣习气。虽然这种揭露非常有力,但仍处于一种浅层次的现象总结。
到了晚年,蒲松龄的仕宦之心逐渐冷淡,便不再为“中举人,做好官”的人生个人奋斗目标所遮蔽,对于“狨”、“猕”关系的思考,便上升到制度层面。他开始意识到,生民百姓所受的盘剥,是一种制度性的伤害,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官僚统治集团便是他在《聊斋志异》中所塑造的那个“食民之狨”。官员、军队、行政机构、司法体系,统统都是这个“食民之狨”制度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制度性力量,老百姓在遭受盘剥时,才如“群猕”一般,“戴石而伏,悚若木鸡,惟恐堕落”。这种思考在《寒森曲》、《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这两部作品,体现得特别明显。
对于皇权制度下“官”与“民”的关系,蒲松龄在《磨难曲》第十四回,借剧中人物方仲起之口,讲出了个人的理解:“牧是养,譬如人家喂羊,同是爱惜他,也望他孳生,也望他肥大,却也要杀他吃。托给那牧羊的,他也要偷着杀他。那县官就合那牧羊的一样,岂有全然不杀百姓的?”[5]这席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官僚统治的本质。在这种体制下,“清官”是基于个人品质的偶然现象,而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才是普遍现象;因为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官僚统治集团便寄生在生民百姓的血汗供养之上。满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给予官吏的俸禄非常微薄;为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便允许各级官吏在正赋之外以加征“耗损”的名义来自肥。这样一来,便将相当一部分官俸支出转嫁到生民百姓头上。蒲松龄所处的康熙时代,官吏征粮,要以鼠噬、雀吃为借口多征“折耗”;征收银两,也要以“铸损”为由多征“火耗”。這种制度型的公开“贪腐”,极大地刺激了官吏集团的渔利欲望,败坏了整个官场。《磨难曲》中的马知县讲得明白:“为甚人人望做官?三梆响罢面朝南。这班生意真真好,板上皆生银子钱”[6]。因此,在卢龙县旱蝗踵至、颗粒无收之年,为追逼钱粮便将四百名欠户活活打死公堂之上。秀才张鸿渐为生民鸣不平,越级呈状告马知县贪酷,却根本无法撼动马知县,因他是在替朝廷征粮。结果是不但自己被迫逃亡,妻子也被收监。最后张鸿渐的妻兄方仲起靠打通权臣严世蕃的关节,才将马知县处死。《磨难曲》虽将故事背景置于严嵩父子弄权的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实际上却是对清初黑暗社会现实的影射。
由于“食民之狨”的残暴,“群猕”必将觉醒、反抗。这种觉醒和反抗才开始是个人性的,就如《寒森曲》中的商三官、商礼二人,到阴间也要告状,最终“直踢倒森罗宝殿”。随着民众普遍的觉醒,就会不断涌现出《磨难曲》中任义那样的造反英雄“遍天下寻杀贪官”,而且会得到民众的响应:
“怕朝廷不肯体谅,不信俺但杀贪赃。指不的出马一条枪,百万兵才敢往前闯。八十万存孝,二十万张良,天下人民,才有个太平望”[7]。
(二)对待“母夜叉”的矛盾态度
蒲松龄自幼接受儒家正统伦理观教育,非常重视家族关系的和睦和人伦风尚的净化。从维护家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出发,强调长幼尊卑、兄友弟恭、养老护幼、夫妇和睦、邻里互助等传统社会伦理规约。他在自己的生活中,随时践行这些儒家信条,并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感化自己的乡邻。蒲松龄对自己的母亲极为孝顺,其母董氏病重,本来应由媳妇们轮流侍奉,但他却独任其劳,“四十余日,衣不一脱,目不一瞑”,直至母亲去世。蒲松龄与其兄弟感情很好,虽然由于其两个嫂子泼悍,在分家时多拿多占,他虽有怨言,但并未因此伤及兄弟情分。他的妻子刘氏虽性格内向、不善言词,但却勤俭持家、孝顺公婆;蒲松龄对内向的刘氏虽有一种缺少知音的遗憾,但却对婚姻忠贞不渝。他与子女的感情也很好,为了支持三个儿子的举试,一直到70岁才在家人劝说下撤帐归家。
在长期的家庭生活实践中,蒲松龄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传统男性社会中,妇女虽然依附于男性,但在家庭中却承担着养育子女、奉养公婆、和睦兄弟、友善邻里的重要责任。在他看来,一个“不贤德”的妇女,完全可以把一个大家庭搅得七零八落。当然,蒲松龄所说的“贤德”,无非是顺从、忍耐、要以个人的牺牲来维护传统大家庭的秩序。早年的分家经历,使他更加确认“不贤德”的妇人是人伦窳败之源。个人情感的伤害,使蒲松龄极为厌恶那些所谓的“悍妇”或“泼妇”。他在《聊斋志异》中便通过《江城》、《邵九娘》、《马介甫》等篇,列举悍妻虐夫、虐妾、虐公婆、虐子女的种种恶行,并通过《夜叉国》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体力、智力都远超男性的“母夜叉”形象,并在篇末不无担忧地说:“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在蒲松龄看来,女子强势便会致使男子“惧内”;男子一旦“惧内”,则家庭事务必为女人把持。一旦女人把持了家政,就极容易做出“不贤德”的事情。
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心理,蒲松龄不但在《聊斋志异》创作大量故事,抨击“母夜叉”;还在创作表现家庭伦理的俚曲时,加大对“悍妇毁家”的铺排力度,以此来训诫市井愚妇,万勿成为俚剧中的“母夜叉”。
在蒲松龄看来,《墙头记》中的大怪、二怪忤逆不孝,除去自身的悭吝、自私外,“惧内”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因为“惧内”,大怪好酒好肉地招待完岳丈后,本想把席上的残汤剩饭给张木匠送去;孰不料,其妻李氏连这也不允许,“那腥汤如今坏了吗?且是那狗这二日不吃食,留着拌点糖喂他喂。今早晨剩的那糊突,给他不的么?”因此,蒲松龄让虐待老人的李氏,在跟王银匠打官司时,受到了“拶手指”的酷刑惩罚。通过俚曲的搬演,那些不识字的农村悍妇即便是不懂王法,也知道不孝敬公婆的严重后果。这正是蒲松龄所要达到的目的。
《姑妇曲》中的臧姑,也是个虐待公婆、打骂妯娌的悍妇,但她的嫂子珊瑚却性格温和、知书达理、吃苦耐劳,对婆婆于氏的不公、弟媳臧姑的打骂处处忍耐,维持了家庭的和睦。通过人物对比,蒲松龄褒善贬恶,晓谕那些市井妇人什么才是女性的“贤德”。当然,这种“贤德”自然也包括“从夫”的自觉性。《禳妒咒》中的江城,性格率真刚烈,对其丈夫的种种恶习采取非打即骂的方式迫其纠正。其丈夫高生嫖妓、撒谎的种种行径,也是当时一部分仕人的恶习,显然亦不为蒲松龄认可,因而江城在其笔下并非全然的负面形象。然而,江城反对丈夫纳妾的行为,蒲松龄却认为是“妒忌”的表现,是为人妻者必须要去除的“恶德”。这样的女性品德认识,显然是一种封建男权主义的思想糟粕。
蒲松龄虽然强调女性应当顺从、忍耐,但又认为妻子又负有纠正丈夫恶习、促其立业向善的责任。这在《禳妒咒》中已有表现,在《俊夜叉》中竟大力奖掖起那位通过殴打、辱骂等非常手段迫使丈夫戒赌的张三姐来了。一方面大力抨击那些虐夫的悍妇,一方面又褒奖那些通过打骂来纠正丈夫恶习的女性,看似自相矛盾,其实这是以男性为家庭中心而衍生出来的悖论。对这样的悍妇,蒲松龄为其更名曰:“俊夜叉”。
结语:
在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后,蒲松龄的文学观念发生转变,开始关注本地的乡情民俗,开始为本地乡人写书。他不但写了《日用俗字》、《药祟书》、《农桑经》等生产、日用读物,以帮助本地农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开始用本地方言创作俚曲来愉悦乡民、淳化风俗。其实,这也是蒲松龄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经世致用”的一种体现。这时,他已经放弃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梦想,开始真正以一个淄川农村读书人的眼光来审视养育自己的这一方水土,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能够惠及乡邻、惠及后代的文化善举。不求阳春白雪,但求里人和歌,这样的由“雅”转“俗”,完全出于一种自觉的“真性情”。
当然,蒲松龄所讲述的那些淄川乡村“本事”,以及他所使用的淄川本地方言土语,会使本地人听起这些俚曲来,别有一番畅快,别有一番亲切,别有一份鲜活,别有一份生动。不过,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是一种障碍,因而极难像《聊斋志异》那样流播海内。在本地戏曲的发展演化中,随着曲调的不断更新,蒲松龄耗费大量心力填写的曲文也逐渐丧失了音乐性,这反倒成为改编这些俚曲的一种负累。因此,在几百年的流传中,只有像《墙头记》这样抓住“养儿防老”这个全民性社会问题的个别俚曲,才能得到不同剧种的不断改编,并成为戏剧经典。这是聊斋俚曲影响力远远赶不上《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
注释:
[1]这14种“俚曲”即:《墙头记》、《姑妇词》、《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在当地流传的《富贵神仙曲》与《磨难曲》,应是由《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演化出来,但该剧一开始就是二个关联剧,还是在流传中分开的,无法考证。故蒲氏所作俚曲有“14种”与“15种”两种观点,本文取“14种”之说.
[2]詳细推论见《聊斋俗曲考》译文,载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蒲松龄研究集集刊》第四辑,齐鲁书社1984年版.
[3]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17-18.
[4]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见《蒲松龄集》第18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蒲松龄.聊斋俚曲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753.
[6]蒲松龄.聊斋俚曲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711.
[7]蒲松龄.聊斋俚曲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727.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俚曲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2]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4]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蒲松龄研究集刊(一)[M].济南:齐鲁书社,1980.
[6]蒲松龄研究集刊(二)[M].济南:齐鲁书社,1981.
[7]蒲松龄研究集刊(三)[M].济南:齐鲁书社,1982.
[8]蒲松龄研究集刊(四)[M].济南:齐鲁书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