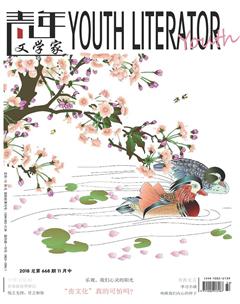梦彼岸
杜楚茵
他的这个梦很奇怪。
一般来说,在梦里是没有感觉的,他却紧贴着冰冷的湿手套;一般来说,在梦里是没有嗅觉的,带着焦炭气味的浓雾却时时缠绕着他;一般来说,在梦里听觉是不真切的,他却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老式火车的“况察”声愈近,似一命催一命。
他感到胸腔里的心快要蹦跃而出,耳听八方,可闻草动,警惕异常。这很奇怪,因为从未有过什么事需要他紧张至此,平日等候成绩,犯下错事,即使当时如临末日,却也不曾如这个梦一般,危险好似伏草之虎,待出之蛇,逼得他一动不动伏在覆满雪的枯草上,寒风如刀,雪水刺骨。
冷月在天,荒寂无人,火车“况察”声由弱至强,由虚至实,如从天边开来……
巨响骤至,热浪骤起,在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的心一定跳出来了,掉落在地随之颤动。白光一片,海浪一般将他从梦中掀起,身体回到他温暖的床上,气喘吁吁,惊魂未定。
窗外晓光已至,早霞千里,他转头按亮手机,整装上学,夜间种种不作他想。
他做了一个梦,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是个异常温暖的梦,梦中空间温度宜人,潮而不闷。虽不可视物不闻其声,但身处其中,如置云棉之上,阳光轻微,厚土暖烘烘地放着热,清风似水,划过皮肤。这梦中之地一定正处春天,他想,但他的家乡即使春天也不曾如此舒适,这里美好地不似人间。
一阵寒风如刀刃割来,虹吸般猛然将他从暖境吸出。眨眼轻辨,自己仍旧窝在土壕里,身上是薄袄,身旁是铁枪。月光寒厉,射在这一排夜宿荒郊的人们身上,白雪相掩,四下寂寥,适才的温暖,果然是梦。一九三六年的温暖,果然只能存在于梦中。
一定是白天爆破时靠得太近了,他这样想着,不然何来如此逼真的暖气。翻身阖眼,逼迫自己再次进入浅眠,身下硬石难适。朦胧之中,他忽然意识到梦境的不寻常:他竟然感到那样安全,全身满心只告诉自己两个字——太平。这是危险的,他已有五年不曾放下警惕深眠了。
他刚从一场烦人的堵车中脱出,想起繁重的课业,不由得低声诅咒一句,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愤而摔过书包,他仰在椅子上带起耳机闭目养神,却不想雪景重现。“我一定是压力太大了。”他自嘲道。一会儿工夫,白色世界的景象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加清楚,他看见有人影在争吵,听不见在说什么,只见嘴一张一合吵得厉害。不经意朝旁一瞥,枪支的铁光晃晃入眼,他差点跳起来——这可不似做梦。他意识清醒,感觉清晰,却不在闭眼前的家中,四周白雪覆盖,这到底是哪?
树枝横斜,树影绰绰,听着队长与谁气急败坏地争吵,他漫不经心地想,十几年前的林海可不是现在这样死气沉沉,鬼魅横行。那时的树林有肥兔蹿过,有鸟几惊飞,就连缠人绊脚的枝,一望无际的雪,都是他们无边的乐园。而现在,林海中危机四伏,无路无望。无路无望,正如現在整个东北——脚下踏着自己的故土,却实如漂泊异乡。
耳旁传来仙乐,不曾听过,却感觉异常平和。那是属于和平之年的仙乐,他想,而我,终是无福享受了。
摞残章于火中,他看着那打家书打卷变黑,化为灰烬,心中寂然依旧。
他明白自己的归宿。
而他也终于明白了。
血流进他的眼中,也映在他的视野里。他不顾一切地跑出家,跑向最热闹的中心地带,跑向最繁华的街去。“你看……”他难以控制颤抖的声音,像个疯子一样拼命转头,妄图用眼收尽此间繁华,“你看啊,太阳出来了……”
无法阻止血液从伤口流出,他的身体逐渐冰冷,视线开始模糊,却在恍惚中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熟悉的土地上,人往熙熙,车水马龙——这果然是梦。
“你看啊,你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胜利了……”
意识再感受不到任何联系,眼中最后一点血色和白色也退去,他站在街中央,茫然四顾,只余攘攘。
城头云高飞际,声钟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