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一次约会多数应由男人付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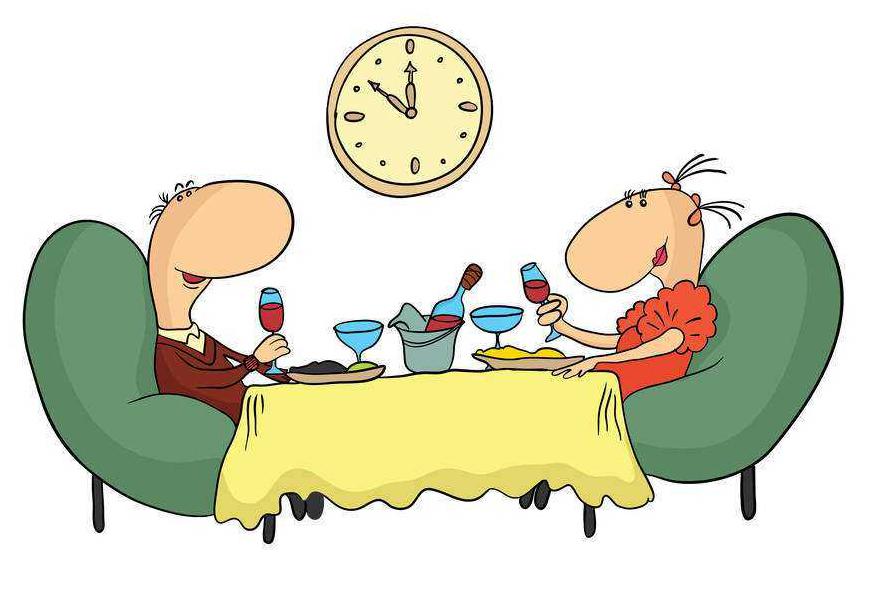

安妮·鲁凯托

安妮认为,社会结构内在的不平等意味着,AA 制并不公平
我刚开始和人约会的时候,妈妈就警告过我,这世上“没有免费喝一杯”这件事。
她接下来说得更具体也更严重:“男人会觉得,你欠他点什么。”
我知道妈妈并不是故意想吓我,但是她这一番话,令我每次结识一个新的人都会感到困扰。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摆脱掉那种男人请我喝了五塊钱的啤酒我就觉得自己有所义务的观念——不过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没回头。
作为一个14岁就开始约会的人,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想、去谈如何找到一个好伴侣的问题,还有初次见面应该关注哪些行为。
这年头,找约会对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能想到的所有选择、身份和背景的人,都有相应的应用程序和网络分众来满足需求。
不过,第一次约会谁付账这件事,总是能引起一番激烈的讨论。
我曾经信奉的逻辑是,女人如果要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我们就应该付自己的部分,和约会对象AA制。为了确保不出现问题,我总是建议去负担得起的约会场所——便宜而热闹的餐厅、社区酒吧、演唱会、公园等等。
大约在五年前,我的朋友和老师们让我认识了一些观念,令我开始质疑过去的做法。
我发现了,像格罗丽娅·金·沃特金斯(更为人所知的是笔名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这样的女性主义作家,令我开始思考,在现行的社会结构当中,谁是获益者。她和其他一些人令我开始想,权力在每一个层面上的运作方式,包括最小的个人互动。
“我们活得更贵”
在现行社会结构基础上,人们的得益并不一样,因此不应该期望双方付一样的钱,这取决于我们在与谁共度时光。
平均而言,女人比男人挣得少。加拿大男性在工作中每挣一加元,女性平均才挣0.69加元。

安妮和现在的男友扎克已经在一起超过一年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成本比较低廉——在很多时候,它可能更昂贵。
社会对于女性外表和行为的期望,是有物质和个人成本的。人们对女性的外形持有不可理喻的高标准;且从娱乐产业到白宫,它都能成为日常嘲笑的对象。
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家庭、工作、恋爱关系和友谊当中,对我们的期望都是比男人更冷静、更关切、更善解人意、更能屈能伸和随遇而安。要达到这些要求,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成本是昂贵的。
而且,谁付账不能简化到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问题。基于我们的性别、社会与经济地位、种族、国籍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
最终,平等并不是相等。相等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平等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一双适合他们的鞋。在良好的恋爱关系当中,人们追求的是平等。
有一次我和一个男人初次约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吹嘘自己的跑车和旅游行程,当他想要AA付账的时候,我就迷惑了。奇怪的是,经常是这些条件优越的男人会向我或者我的朋友说:“我是个女性主义者,所以我们要各自付账。”
无论男人是否认为女人的劳动报酬过低,事实的确是这样。而且,无论男人是否同意女人报酬过低的事实,他们也直接从中得益。
这并不是说男人工作就不努力,或者永远应该由男人来付账——在我遇到自己明显比约会对象挣得多的情况时,我很乐意AA或者由我来付账。
如果我感觉一个男人初次约会付账之后就觉得我“欠”了他什么的时候,我会坚持由我来为两个人买单,并且断绝一切进一步联系的机会。这样一种原始老派的思维显示了对方缺乏眼界、尊重和换位思考。
“挑战不平等”
我和男人、女人都约会过,而有趣的是,每一次我和女人或者性别多元人士约会时,我们最后都会抢着买单。
现在,我和我的男友扎克在一起超过一年了,我当时对他有好感,是他告诉我说他喜欢动物,表达他对朋友的欣赏,还分享了他对劳工权益的见解。他付了初次约会时的账,而我则付了第二次约会的账。
现在,我们在一起出去或者去对方家里时对于消费的划分,是基于我们各自能负担多少。这在未来或许会改变,不过我们已经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我们双方都能感觉受到尊重,任何一方都不会感觉付出不被欣赏或者被占了便宜。
初次约会是一个小小的机会,去认识到人们在社会当中有不一样的资源获取途径。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好伴侣,那么挑战权力上的不平等,就是每一段关系当中的重要部分。
谁在初次约会中付账,并不能决定这段关系的性质。
随着关系的建立,人可以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相处方式。不管我们对于初次约会应该(或不应该)由谁付账,考虑周全总是好的。(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费勒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