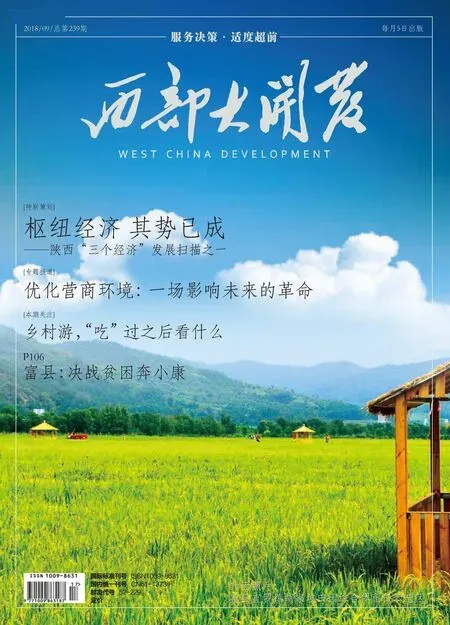陕西话剧舞台的发展与走向
——观外事学院话剧《白鹿原》有感
文 / 周昊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创作中心

近期,观看了西安外事学院改编创作的话剧《白鹿原》,这应该是国内非艺术院校演绎名著的第一部,相信以后会更多。
从北京人艺和陕西人艺演出的《白鹿原》到西安外事学院演出的《白鹿原》,我观看了A、B、C三个版本对具有典型地域代表性的名著演绎,感受到话剧舞台对经典名著改编的魅力和神韵,一看,都是下了大功夫、大力气了。这三部话剧存在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缺乏名著的气质。这气质,是特殊的,是地域的,是独有的,引发了我对陕西话剧的启发和思考。
名著《白鹿原》是植根于陕西这片土地上的文学经典,搬上话剧舞台,是当代舞台艺术的一件幸事,具有划时代的使命和意义。观看这三个不同版本的《白鹿原》,让我联想到北京人艺、上海人艺曾经演绎过的经典话剧,触动我对陕西话剧未来发展和走向的勾勒。
一部名著的改编,往往关注作品本身的内容展现,过多强调手段、技术、表现形式,而容易忽视作品真正的味道和实质性的生命质感。
名著改编话剧,是话剧创作的捷径,尤其《白鹿原》这样的经典,既有典型的地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A、B、C三个版本改编的《白鹿原》,恰恰突出了其共同的缺憾。
地域是有明显差异的,表现在不同民族、种族、文化、语言等方面,形成不同戏曲、唱腔、流派等,且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百十年的历史了,话剧艺术最大的特质,就是跨地域性或无地域性,表现形式上,基本以普通话为主。话剧艺术,是一个舶来品,简单回顾中国话剧发展的历程,从“五四”前后的文明戏,到今天的话剧,成为最普及的舞台艺术。

陕西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
北京人艺和上海人艺演绎创作的《雷雨》《茶馆》《骆驼祥子》,或者《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榆树下的欲望》等经典名著,其它省市的话剧团体也在一一改编上演,其内容和形式,基本上以北京人艺或上海人艺的改编为标准,若有若无地显示出北京人艺和上海人艺的话剧创作有着不同的气质和神韵。
中国近代话剧舞台的农村题材,因特有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陕西题材的话剧占全国话剧的主导地位,如《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郭双印连他的乡党们》,到今天的《白鹿原》等等,厚重、古朴,并依存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不同的是,这些揭示陕西题材的话剧,整体舞台内容和形式都有相近之感,千篇一律之感,有地域无差异,缺乏整体演艺特质,相比较成熟的北京人艺、上海人艺的话剧风貌,让我感受到陕西话剧应有陕西话剧的风貌,这也是我今天提出“陕派”话剧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陕西话剧的未来该往哪条道路上发展,很值得探讨,因为话剧本身就有许多可挖掘的东西。今天,随着话剧民族化的发展,话剧艺术的广泛普及,以及由高雅艺术走进校园到走出校园的普及,中国话剧乃至陕西话剧到了新的裂变时期了,所以,应有新的发展定位。
说到“陕派”话剧,需要参照中国话剧史上因地域文化而形成代表性的两大流派,一个是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京派”话剧,一个是以上海人艺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从西安话剧院排演的《郭双印连他的乡党们》和今天我们提到的话剧《白鹿原》的三个版本,其大的风貌,已经渐渐显露“陕派”话剧特有的气质。因此,中国话剧具有地域性的创作,在未来的话剧舞台上,将有更清晰的艺术形态。
陕西的“陕派”话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文化的先天条件,三秦大地,孕育着独有的神韵,足以支撑“陕派”话剧的形成。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不是在一部戏里面说说陕西话、吼吼秦腔,就具备“陕派”话剧特质,这些手段,是外在的点缀,“陕派”话剧追求的是精心提炼剧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以及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习俗、习性、个性,以及对身边事物的态度、观点、表达方式,所呈现的人物与人物气质,都与京派、海派所表现的气质有强烈的反差,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是独有的、典型的、个性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演员的人物塑造,不单单是完成一个人物的表演,更重要的是揭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气息。

西安外事学院版话剧《白鹿原》
还有,要在导演观念上加强叙事理念,强化一部作品的整体气质,进而增加表演上的要求,演员不能够单单完成人物塑造就够了,还要挖掘人物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融入人物与规定情境之中,在典型环境下所生发出来的、与众不同的乡情乡韵;“陕派”话剧,应该是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从剧本、导演、表演、服化道,以及音乐,都应是完整的、贯穿的,有它特有的调调或者味道。关于西安外事学院演出《白鹿原》话剧的音乐部分,本人以为,此剧应该减少或减弱对音乐的依赖,远离音乐对剧情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渲染,音乐的作用在话剧舞台上非特定故事情节,会令一个严谨的叙事,失去其特有的交流氛围,会令观众的观感间离,造成碎片式的破坏,这是我对外事学院版《白鹿原》提出的一个建议。
北京人艺版的《白鹿原》,在音乐的处理上,不仅选用了“华阴老腔”作为贯穿,还把“华阴老腔”的原班人马入嵌在整台话剧的叙事之中,起承转合,既有间离,又有叙事,还强化了陕西特有的文化氛围,似乎令人耳目一新,我认为仍然有缺憾之处。
陕西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我尤其喜欢整部舞台音乐的选择及运用,有醍醐灌顶、画龙点睛的神韵。
舞美设计,我也偏重于陕西人艺版的《白鹿原》,以宗族祠堂为演出的重要场景表现,既有象征,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北京人艺版、和西安外事学院版的《白鹿原》,在舞台设计方面,比较相近,直白地给观众展示“原”的地域形态,缺乏视觉内涵的扩展。

北京人艺版的《白鹿原》,选用了“华阴老腔”作为贯穿。
话剧植根于中国大地,还没有形成其更为广袤的风韵。为什么这么讲,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就有五十六个民族习性和民族文化,这其中还包括文化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如果在这些方面深入探索,进一步发掘和创作,应该有更大的话剧舞台。“陕派”话剧更是如此,不仅具有丰厚文化底蕴、鲜明的地域特征,还有《白鹿原》这样的巨著,很值得独树一帜,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绽放应有的艺术魅力,并且会引领其他地方话剧的突破和发展,比如,将来会出现“粤派”、“闽派”等地域性话剧,会把中国话剧这个特有的艺术形式,完全融入于民族,完全融入于时代。
我想,如果上海人艺对名著《白鹿原》进行创作和改编,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回到这次陕西外事学院版的话剧《白鹿原》,这是地地道道的陕西故事,如何完成这样的一个具有陕西地域特质的话剧,陕西外事学院在未来的话剧创作上,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曾经这三个不同院团,三个版本的精彩呈现,由于“陕派”话剧的理念尚不够清晰,存在的遗憾就在于此,有陕西的调调,味道不正;有陕西的情怀,艺术性不够鲜明、不彻底、不纯粹,也许,我们到了真正下功夫去思考、去创作“陕派”话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