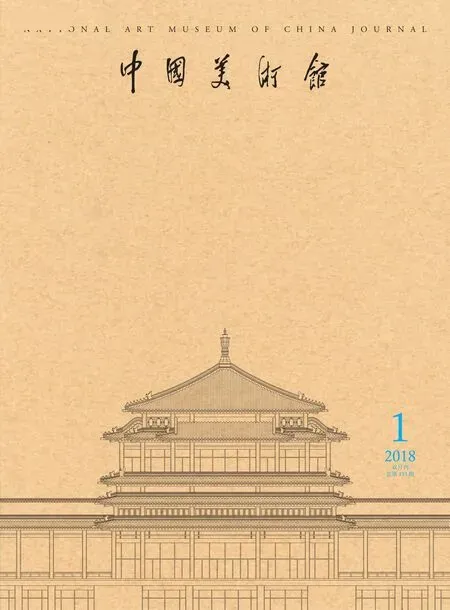再谈中国艺术史的编写问题
吴士新
在过往的中国艺术史写作中,通常使用“美术”(fine art)来替代“艺术(art)”一词,而“艺术”的概念则涵盖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曲、电影、曲艺等更为宽泛的学科领域。从词源学来看,“美术”(fine art)是“美的艺术”的中文译词,词根是“艺术”(art)。也正是因此,中国艺术史的写作核心似乎始终围绕着审美来进行,这一点从20世纪以来诸艺术史家撰写的艺术史著作中可窥见。从姜丹书编写的《美术史》被教育部批准作为师范美术专业教材开始,后续出现的艺术史著作几乎很少使用“艺术”这一称谓,而是习惯地沿用了“美术”这一名词。
在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审美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但是,从审美的角度看,以往的艺术史更多是从艺术作品的欣赏、鉴赏的角度来进行撰写,而忽略了艺术作品背后的创作因素。显然,这样的艺术史如同隔靴搔痒,难以触及艺术的本质。这种过度依赖美学研究而撰写的艺术史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令艺术史成为鉴赏史。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使用“艺术”来替代“美术”一词更为科学。众所周知,“艺术”一词是舶来品,但是其当代意义的指向是明晰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art”一词更偏重于“工艺”的意义。由“art”作为词根演化出的“artifact”一词,意为“工艺品,人工品”。“艺术”这一概念,更侧重于观念借助技艺的表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艺术的核心不是审美而是观念。
“艺术”一词的核心意义在于,并不是再现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关注的是人类将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艺术赋予形象以什么样的精神存在更为重要。在中国艺术史中,左右人们观念的不是审美,而是能够趋利避害的“凶”“吉”观念。这一观念从中国最早的汉字艺术的创造和使用中便可以看出。作为人类象形思维智慧的结晶,汉字的产生就先天地带有“吉”“凶”的神秘的时空观,由此衍生出“福”“祸”的自然观,又演化出“善”“恶”的道德观。这里的时空观、自然观、道德观反映出我们先民最初的生命意识,而由此演绎的三观(时空观、自然观、道德观)也构成了儒、道、释三家的观念基础。从这个原点进行研究,我们便可以找到艺术史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
对于人类而言,对万物的敬畏之心不应该磨灭,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时候,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是无法超越于生死的。一切艺术形式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在生死之间的某种表达。当我们拆毁一座老房子时,我们是否感觉到它在诉说着什么?当我们重新建立一座新的城市时,我们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所散发的一种灵魂?人类为什么需要敬畏万物与自然,在我看来,并不是自然要给人类什么样的惩罚,而是人类在敬畏自然的同时感到自己内心世界的安宁与纯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自然世界的变化往往令人类内心有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在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的主人时仍是如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改造的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对于人类的精神和人性而言并没有本质改变。人类社会以文化的诞生而文明,而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却是文明和战争的交替。显然,这是人类的理想和人性之间的冲突。对于每个时代、每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国,他们怀揣自己的理想,却生活在严酷的现实之中。然而,正是他们的理想国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每个人内心的强大和人类的希望——柏拉图、苏格拉底、老子、孔子……之所以他们为圣人,是因为他们洞悉到了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只有人类的灵魂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能超越人性的弱点。
对于中国的艺术史究竟怎么来写,是以目前中国的地理版图来写,还是以历史上中国的版图来写?是以汉族人的历史来写,还是以所有民族的历史来写?这些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或许并不难以解决。因为,不论是现在的中国地理版图,还是历史上的中国地理版图,不论是汉族人的历史,还是所有民族的历史,我们对艺术的认知似乎有某些共同点。
首先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是,艺术到底是什么?对于个体而言,艺术是人类个体通过想象发现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然而,艺术又不限于此,艺术可能成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象征,并能持续传播下去。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在不同的时空、创造着那里产生新的语言、形式。这种流变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变异。例如,同样是佛教题材的雕刻,山东灵岩寺塔基基座浮雕和重庆大足石刻的浮雕在风格上却有着巨大差异,佛教故事的地域化和本土化特征十分明显。山东灵岩寺塔基基座浮雕的风格样式明显受到当地画像石风格的影响,而重庆大足石刻的浮雕则明显受北魏时期石窟造像的影响。这些雕刻艺术在题材的选择上也已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之所以列出以上两个例子并不是为了单纯比较两者的差异性,而是我们应该通过更多的图像比较,梳理出一些经典题材(保留剧目)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呈现出的观念差异、风格差异以及审美判断,从而建立一套中国方式的艺术史模式。就艺术而言,应该有原创性和复制性之分,这涉及对某一样式最初的意义的追踪。这也是我们的艺术史所要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艺术的原创性和复制性就像一条流淌的河,要想找到它的发源地就要追溯这个地方的气候、地理等因素。
其次,艺术的问题既与艺术的创造者有关,又与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认知有关。在一个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之中总有一种文化占据着主流。这种文化也是特定时代、地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一种体现,它同时体现在艺术之中。对于个体的人而言,这种关系无疑是简单的,因为艺术思想的传播借助的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别的。离开对艺术作品的梳理和认知,艺术思想也不复存在。可惜的是,近代以来对于历史上艺术作品的认知更多地出自于考古学的认知,而不是艺术学的角度。作为一种依靠想象、虚构对空间进行可视化创造的艺术形式,它的内在动力来自于艺术家自己。从创作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只能取决于自己这个单个个体。对于“他”而言,他认知和表述世界的方式不过就是“我”“你”“他”三种。
再次,艺术史要面临的问题便是,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的语言叙述。我们应该看到,特定的艺术种类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才能留存下来。例如青铜器艺术在商周时期流行,画像石在两汉兴盛等等。我们如何在这些材质不同、风格语言差距巨大的艺术种类背后寻找它们流变的发展关系。这种流变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技术进步、政权交替、战争、文化交流等。但是,我们从这些差异中要找出驱动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因——人类的审美变化。因为这才是推动艺术史前进的动力。在此,认真区分“美术”与“艺术”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关系两个词汇所涵盖的内容的不同,任何一个概念的组成都应该有一个结构。
20世纪以来,在中国艺术史的书写方法中,考据学与考古学是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其中,又兼容了图像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方法。这些方法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史著作中有不同的呈现。如陈师曾(1876—1923)的《中国绘画史》,郑昶(1894—1952)的 《中国画学全史》,滕固(1901—1941)的《中国美术小史》,潘天寿(1897—1971)的《中国绘画史》,傅抱石(1904—1965)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俞剑华(1895—1979)的《中国绘画史》,秦仲文(1896—1974)的《中国绘画学史》,胡蛮(1904—1986)的《中国美术史》,王逊(1915—1969)的《中国美术史讲义》,李浴(1915—2010)的《中国美术史纲》,阎丽川的《中国美术史略》,阿尔巴托夫的《论中国古代艺术》,王伯敏(1924—2013)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8卷)和王朝闻(1909年—2004年)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12卷),毕克官(1931—2013)、黄远林(1940—2005)合著《中国漫画史》,张少侠、李小山合著《中国现代绘画史》,薄松年《中国年画史》,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田自秉(1924—2015)《中国工艺美术史》,王子云(1897—1990)《中国雕塑艺术史》,陈少丰(1923—1997)《中国雕塑史》等。上述艺术史的书写,无论是鸿篇巨制的艺术通史,还是专于一科的专史,似乎都难以摆脱思想陈旧、方法落后的窠臼。上述美术史存在的编写问题笔者已经在《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编写及其运用的史学方法之思考》1一文中做了详细的阐述 。在艺术史写作中,考证、考据方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可信的史料,但同时缺点也显而易见,它只是史料,还没有上升到艺术史的逻辑演化之中。
事实上,确立艺术史书写究竟为谁?艺术史书写的对象、内容、方法,从构筑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艺术史的角度出发,艺术史著作才不会落入就史料论史料的平庸的、尴尬的书写之中。考据,即“考证”,是在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的治学方法。考证是中国学术史上,史学家最主要的学术方法。1887年,法国人波西尔出版了“在巴黎美术馆中,称为美术工艺书中最善本” 的《中国美术》。该书以博物馆馆藏实物和考古实物作为著史依据。具有留德背景的滕固则是当时最早将考古实物引入美术学的学者之一。在此之前,依据考古学方法书写美术史是对依据文献考据作为美术史书编写方法的颠覆。可以说,这两种史学方法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编写的主要方法。
第一,建立艺术史的研究书写对象,并将之科学分类。
目前艺术史的写作对象比较清晰,主要可以分为建筑、雕塑、雕刻、绘画、书法等。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艺术”一词中包含的“技艺手法”。而我们看到,在以往的艺术史写作中,这种研究对象的概念是混乱的。例如“画像石”“画像砖”在诸多美术史版本中被作为专业术语所使用,但是作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专业术语这种使用并不规范和科学。严格意义上来说,“画像石”应该是一个考古学的术语,而不是艺术学的术语。在艺术学中,“画像石”“画像砖”应该归属在雕刻门类之中,而现代流行的美术史编写却常常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显然是不科学的。
第二,打破以阶层作为艺术史书写分类的标准,建立以现代公众为核心的艺术书写模式。
艺术史书写的最终目的是写给当代人的,其宣扬的思想观念应体现公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审美判断。当前,在中国艺术史中,艺术史家们习惯把绘画分为“宫廷绘画”“文人绘画”“民间绘画”三类。事实上,这种划分和表述并不科学。在以往艺术史的表述中,绘画甚至其他艺术门类被按照阶层来加以划分,虽然能够借此更为清晰地区分绘画因为创作原则的不同而呈现出的差异,但是这种划分将会带有先天性的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应该看到,“宫廷绘画”“文人绘画”“民间绘画”的创作者在艺术面前并没有歧视褒贬之分。在艺术史中,艺术学科的原则是原创与复制,而不是阶层划分。
我们看到,这种分阶层的观念和方法已经为艺术史书写树立了天然的观念对立与隔膜的障碍。正是基于此,过往艺术史书写过于注重统治阶层的艺术史的写作,注重皇家艺术史、文人艺术史的写作,而忽略了民间艺术史中蕴含的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对这些艺术作品的分析恰恰可以弥补过往艺术史的缺憾。尝试去除艺术家的身份差异,将艺术作品放置在视觉文化的阐释之中,似乎更符合艺术史的现代标准。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抹平”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艺术史上,一些艺术作品的视觉结构会呈现出与纯粹的视觉图式结构迥异的面貌,这些作品常常会受到视觉造型之外的干扰。在我们解读这些作品时,作品图像信息有时会变得模糊不定。例如传统文人绘画对诗歌、书法、绘画、刻印在同一画面中的融合,构成了一种“综合的艺术”。这种“综合艺术”,从整体上反映的是汉字艺术(语言、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特殊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类似于“综合艺术”的文人绘画虽然能够流露出特定时期文人的心理特征,却难以在绘画图式上具有普世的研究特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人绘画又带有天然的局限性,绘画往往成为他们私人发泄不满的方式。
我们应该从艺术史的创造者——艺术家不同的时代背景、个人因素、创作动机等方面寻找艺术创作的共性,寻找艺术所表达的文化理念的共性,寻找在艺术流变中原创、继承与再创造的变化规律。唯有如此,中国的艺术史书写才能触摸到艺术史发展的规律。
第三,建立以作品为写作对象的艺术史。
首先在艺术史中,我们应该明确,艺术史书写的核心是艺术作品而不是文字数据。事实上,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传统考据与考古方法并不总是十分可靠,对中国历史而言断代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过去的艺术史的书写,也将困扰未来的历史书写。因此,我们可能会对这些不确定的艺术的书写进行取舍。幸运的是,在中国艺术史的发展中,能够体现中国艺术特性的最重要的部分还是比较清晰,可以描述的。建立以作品为书写对象的艺术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一种视觉谱系,进而剖析可靠的文化心理的结构方式。对于艺术史而言,历史的书写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核心应该是关于艺术在时间中的发生和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艺术史的核心应该首先找到中国艺术的特性。艺术史的书写不应该只是审美史的表述,而更应该有深度和广度。
总之,当前的艺术史需要重新梳理、研究和编写。一部好的艺术史不仅让公众了解艺术史发展的规律,更为重要的是,让公众通过艺术史形成审美共识、社会价值共识以及精神价值共识。
注释
1.参见吴士新《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编写及其运用的史学方法之思考》,载《云南艺术学院院刊》,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