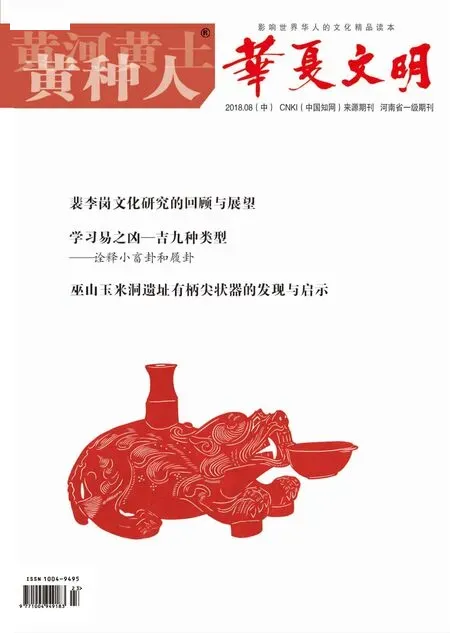朝阳袁台子周边文化遗存考略
□刘超
袁台子村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城南约13公里处,大凌河南岸,松岭山脉柏山北麓。此处周边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依据现有相关史料记载及最新考古发现推断,自远古以来,人类文明便在这里萌发。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存,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上层文化遗存,战国及汉代文化遗存,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遗存等的广泛分布,都较为充分地证明了袁台子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 周边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一)旧石器时代
大凌河流域孕育了人类文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定居于此,处于河谷台地的喀左鸽子洞便是例证。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丰富的打制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等,还有大批脊椎动物的化石。不仅如此,1979年和1983年在该溶洞内还相继发现了一颗儿童牙齿化石和一块人体髌骨化石,这就更加证实了早在10万年前,人类就已在此处繁衍生息,并且有可能在大凌河流域这一广阔区域内活动,就此形成大凌河谷古道。2012年至2013年间,相关学者实地调查,在同样处于此流域下游袁台子境内的东沟及大柏山上的鼻子洞、獾子洞、老虎洞等地点,先后发现了部分动物化石和大批打制石器,主要有砸击器、多面体石核、有肩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所以,无论是从山河走势,还是从自然条件等因素分析,这应该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二)新石器时代
袁台子周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在2008年的“三普”工作中,在其附近发现了早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该遗址位于大凌河边一处低缓的山坡上,遗址西高东低,呈正方形,边长约60米[1]。其中,发现了具有兴隆洼文化明显特征的石质砍斫器和夹砂刻画几何纹筒形罐残片、夹砂饼状器及打制和磨制的石器等。筒形器陶片较为厚重,一侧磨出平面,正是这一文化的典型器物。2013年,在袁台子南大柏山发现的打制如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亚腰形石斧、骨匕等遗物,也是内蒙古兴隆洼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物。
距其2.5公里的腰而营子境内就有小东山遗址[2],在此处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10座房址、20个灰坑、1条灰沟。房址分圆形与近方形两种,灰坑为圆形或不规则椭圆形,灰沟则呈东西走向。此处属聚落遗址,而且不同功能的遗迹分布有序。从出土遗物看,多为陶制生活用具,如罐、钵等。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赵宝沟文化遗存,其中一处赵宝沟文化的房址与一处红山文化房址紧紧相邻,距离不过几十厘米[3]。
在袁台子东王坟山山顶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积石冢,有石头堆和红山文化陶片,部分与牛河梁第Ⅱ地点二号积石冢周围出土的筒形器相同,属红山文化中期偏晚。红山文化多玉器,在1986年牛河梁遗址还发掘出一枚仿贝玉币,其玉石材料属千里之外的辽东岫岩玉,当时的运输势必要沿天然河谷前行,而在这一时期通往辽东的主要路线多经由袁台子。这也证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袁台子就已在大凌河、西辽河流域与外界交往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二、周边青铜时代文化遗存
1979年,在辽宁省开展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袁台子周边共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4处,包括十二台村下洼遗址、南大营子村王坟沟遗址、叶家村水泉遗址和大杖子村红石砬子遗址[4]。小东山遗址中还包含有魏营子文化遗物及凌河文化遗存,其中出土一柄状陶饰件,类似青铜短剑剑体柄部,上部类枕状器,两端凸起,中间凹,中部有一周凹弦纹,似表示枕状器嵌于盘中。其下为柱状柄,中空。通长8.7厘米,顶部宽3.9厘米,柱径1.3厘米[5]。在袁台子周边还曾发掘有青铜短剑墓群[6]。这都充分表明该地点与凌河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在2006年,相关部门还发掘了袁台子村东约5公里的罗锅地遗址[7]。该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遗物,部分陶器富有龙山时代的特征,如甗、腹饰多道附加堆纹的瓮、肩附双鋬耳的绳纹加划纹大口盆等。其特点在于,既吸收了邻近地区同期遗存的先进因素,同时又保存了本地的传统文化和风格。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的出现,相应结论的提出[8],更能印证这种传承和融合的观点。这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区域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和密切程度。
三、周边战国及汉代文化遗存
朝阳地区行政建置始于战国时期,属右北平郡、辽西郡辖地。考古工作者曾在袁台子村东北的王坟山北侧发掘一座战国墓,出土了带“酉城”戳印的陶量器,有学者就此推测,战国时期,柳城被称为酉城[9]。
秦朝推行郡县制后,郡下开始设县。到了西汉时期,袁台子附近始有柳城县设置。这一结论已被相关考古发掘所证实。1979年文物普查期间,在袁台子村发现一处古代遗址,由于该遗址包括很多战国时期燕文化遗存,经历了战国中期到西汉末的400余年时间,为概括全面又将其称为“袁台子遗址”。在该遗址中相继采集到印有“柳”和“柳城”字样的汉代板瓦90余片,还在周边发现了烧制此类瓦片的窑址和工具陶拍,此遗址即所谓的西汉辽西郡属县柳城遗址[10]。这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相吻合。
在西汉遗址东西200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分布有序的水井、土窑、陶窑、粮仓等遗迹,其中粮仓的规模比较大,共计3座,且两仓并列,总容积约为33立方米。按现存粮食计算,每仓可储存谷物约2万公斤,如此大规模的粮仓不可能为个人所有,应为官方或集体的储粮设施。加之出土了大批的铁制农具和手工工具,这表明袁台子在当时不是一个普通的村落,而是一座具有较大规模的城镇。
东汉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崛起,柳城则被乌桓所占据。所以,在袁台子遗址与王坟山墓群的中间地带存有少量的东汉乌桓墓,这时的柳城文化面貌已大有改变。
秦汉之际,柳城的交通地位也非常重要,与之有联系且又产生重要影响的道路主要有卢龙道、傍海道等。卢龙道的东段走向为:出卢龙塞沿滦河西岸北行,向东转入滦河支流即沿瀑河再向东北行,进入青龙河流域沿汤道河东行,过大煤岭垭口,再东北行沿大凌河支流渗津河谷,经桃花池、黄道营子、沿大凌河谷古道直达十二台子乡袁台子,这是古柳城越卢龙塞入中原最为便捷的天然通道[11]。傍海道始见于《三国志》,柳城南抵傍海路途经南双庙乡、羊山镇五佛洞村、六家子镇、建昌县药王庙乡等地,柳城傍海道远在2000多年之前就已经形成[12]。可见,袁台子在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周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遗存
这一时期,中原战乱不断,柳城地区则先后被乌桓、鲜卑等占领,并成为其活动中心。曹操为了统一中原曾亲自北伐乌桓。据《三国志·田畴传》记载,曹操“令田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堑山堙谷五百余里,越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而其进军路线分为两条:一条沿努鲁儿虎山与大青山之间的峡谷长廊经建平南部扎赛营、喀喇沁、老虎山向柳城挺进,目的是为断乌桓退路;另一条,是从白狼堆沿大凌河谷直捣柳城,途经喀左东山嘴、水泉、乌兰和硕、黄花滩,达柳城。曹操取得全面胜利后,不但恢复了“陷坏断绝”二百余载的卢龙塞道,而且还打通了被乌桓“遮守蹊要”的柳城通往傍海的重要道路。由此,足见柳城地区在统一北方、沟通南北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
1982年发掘的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13]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文化遗存,墓室内壁上的狩猎图、牛耕图、甲士骑马图、四神等形象生动,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绘画水平。经过比较分析,其与中原及河西地区的魏晋壁画墓[14]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这也证明了东北与中原的文化进一步融合,联系更为紧密。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载:“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福德之地也,乃筑龙城,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号曰和龙宫。”至此柳城渐卑,少见于史。然而,袁台子位于龙城南道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仍不可取代。在其附近就发现了大量的三燕时期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二台乡砖厂88M1遗存[15],出土了装饰精美的马具,其中甲骑具装实物为国内首次发现,填补了关于重装骑兵考古资料的空白,对研究三燕文化及马具、甲骑具装的产生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这进一步证明了辽西三燕文化通过高句丽,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文化的某些方面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6]。此外,袁台子发现的汉魏鲜卑牌饰陶范也说明了这里不仅为东北军事重地,而且也是慕容鲜卑活动的重要区域[17]。
通过对上述各时期相关史料和考古遗存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袁台子在历史上曾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还需依靠新的考古遗存的发现及学者们积极的关注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