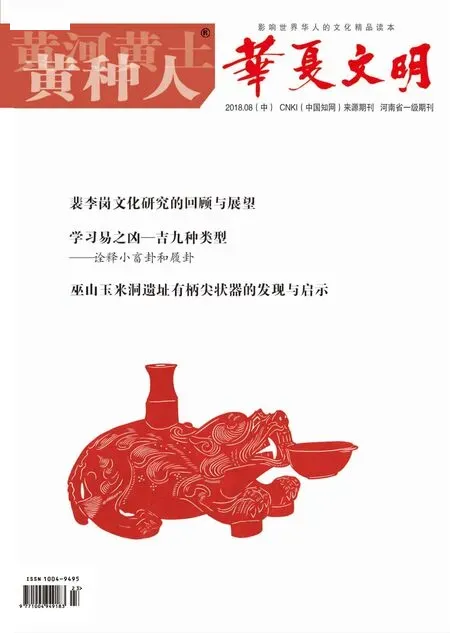裴李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袁广阔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河南省开封地区文管会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于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河南境内,分布范围西至洛河上游的三门峡卢氏,北到黄河以北的安阳、濮阳一带,东抵颍河流域的周口项城,南达淮河以南的信阳潢川一线[1]。裴李岗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陶器和石器方面。陶器中泥质红陶占绝大多数,夹砂褐陶次之,泥质灰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陶胎厚薄不均,火候低,泥质陶多素面,纹饰主要有附加乳钉纹、篦点纹、压印纹、划纹、指甲纹等,最有特色的器类有三足钵、小口双耳壶和侈沿深腹罐等。石器制法有打制、磨制和琢磨兼施三种,器形主要有石铲、石斧、石磨盘和锯齿石镰等。
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已经初具规模,遗迹如房基、墓葬和灰坑等较为常见。墓葬已经有专门的公共墓地,墓坑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墓中不见葬具,唯随葬品较为常见,主要是生活用具,贾湖等少数遗址的墓葬中明器已经出现。裴李岗文化农业开始发展,这点可以从遗址内出土大量的石铲、石斧、石镰等生产工具中得到证实,另外还在部分遗址内发现了粟作和稻作植物遗存[2]。裴李岗文化的制陶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家畜饲养业也已经出现,如贾湖遗址发现了已经驯化的猪和狗。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填补了河南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段空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新石器考古的重大突破。它的发现使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年代至少提前一千多年,为探寻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以及社会复杂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一、考古发现状况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9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配合漯河翟庄电厂的基建发掘中发现了含有裴李岗文化内涵的石磨盘、舌刃石铲、三足钵、小口球形壶等,另外还发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灰坑。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偃师马涧沟发现一套石磨盘,1964年在密县(今新密市)东北角、东关、青石河等地发现了较多的石磨盘、石磨棒。20世纪70年代初,在郑州、尉氏、长葛和项城等地又发现了许多形制相似的石磨盘、石磨棒。由于没有见到其他共存物,上述发现均未引起重视,曾一度将其划入仰韶文化范畴而未能辨认[3]。
1975年夏,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登封县(今登封市)告成镇双庙沟一带发现了比仰韶文化稍早的新石器时代陶片、兽骨和木炭等遗物,其木炭碎块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5071±170年,即距今7000年左右,从而表明这是一处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4]。1977年春,裴李岗村的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人骨、石磨盘、石磨棒和陶器等文化遗物,这一发现立即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同年4月,开封地区文管会和新郑县(今新郑市)文管会联合组建考古队,开始对裴李岗遗址进行发掘,揭示墓葬、灰坑等遗迹多处和小口双耳壶、三足钵、侈沿深腹罐、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等遗物数十件,通过研究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文化遗存,暂称为“裴李岗文化”[5]。
1977年11—12月、1978年3—5月,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对新密莪沟北岗遗址进行发掘[6];1978年4月和1979年4月、9月、10月,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分别对裴李岗遗址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7];1982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了长葛石固遗址[8];198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舞阳贾湖遗址[9]。这几次发掘极大地丰富了裴李岗文化的内容,结合碳十四测定的年代,证明了这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定名的惯例,将其正式命名为裴李岗文化[10]。
二、研究状况
在裴李岗文化中,经过重点发掘的遗址有舞阳贾湖[11]、新郑裴李岗和唐户[12]、新密莪沟北岗、长葛石固、郏县水泉[13]、汝州中山寨[14]等等。其他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淇县花窝、登封双庙和王城岗、巩义铁生沟和瓦窑嘴等等[15]。
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和以磁山遗址为代表的磁山文化的命名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引起广泛讨论,并主要形成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裴李岗类遗存和磁山类遗存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共同性表明它们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差异性则是表明它们不同阶段的表现,以许顺湛、李绍连、陈旭、魏京武等为代表的学者称其为裴李岗文化[16],以严文明、唐云明等为代表的学者称其为磁山文化[17],夏鼐称其为磁山·裴李岗文化[18]。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不确定这两类遗存的差异性是由于它们从属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所致,还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所致之前,最好将其分别命名,其中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以磁山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磁山文化[19]。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如杨肇清、赵朝洪、戴向明等人[20]认识到,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区别于以磁山遗址为代表的另一类遗存,二者应当分别命名,这种观点逐渐得到考古界的普遍认可。
学术界对裴李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分期与年代、类型的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来源流向、与周边文化关系以及科技考古等几个方面。
1.分期与年代。缪雅娟、杨育彬将其分为三期[21],丁清贤将其分为三段七期[22],张江凯、靳松安将其分为三期六段[23],孙祖初将其分为五期[24],方孝廉、曹桂岑等分为四期[25]。
绝对年代方面,对裴李岗文化的10个遗址40个标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排除有误差的数据,纵览校正后的年代,在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500年[26]。但贾湖遗址年代无疑更早一些,发掘者把贾湖遗存分为三期九段,根据碳十四测年,三期的绝对年代为:第一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600年,第二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6600年—公元前6200年,第三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800年[27]。
2.类型划分。主要有裴李岗、贾湖、中山寨、花窝等几个类型。
裴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嵩山周围的浅山丘陵地区,如新密、新郑、登封等,典型遗址有新郑裴李岗[28]、沙窝李[29],新密马良沟、莪沟北岗等等[30]。
贾湖类型:因贾湖遗址而得名,这种类型的遗址多在丘陵与平原地区的过渡地带和平原地区沿河两岸的台地上,包括淮河上游的支流沙河、洪河流域,最北可达汝河、颍河流域。主要遗址有漯河翟庄,舞阳贾湖、郭庄、阿岗寺;许昌丁庄,鄢陵古城、南关、蝎子岗,长葛石固等。贾湖遗址发掘以后,张居中先生认为贾湖遗址应为裴李岗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31]。后来在发掘报告《舞阳贾湖》中提出了贾湖文化的命名[32]。
中山寨类型:目前发现的遗址不多,主要分布在伊洛河及其支流和淮河上游支流两岸,如汝州境内的汝河及其以北的支流黄涧河、洗耳河岸较高的台地上,伊河东岸的伊川白土疙瘩遗址出土的裴李岗遗存特征与中山寨遗址接近,表明该地区也为中山寨类型的分布区。
花窝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的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一带,有焦作、济源、新乡、濮阳、淇县、辉县等地,经过科学发掘的有辉县孟庄[33]、淇县花窝[34]、濮阳戚城[35]。
实际上,每个专家对裴李岗文化类型的认识都不一样,如赵世纲将其分为裴李岗-莪沟和翟庄-贾湖类型[36],郑乃武分为裴李岗和中山寨类型[37],丁清贤分为裴李岗、莪沟和石固类型[38],孙广清、方燕明、孙祖初、王吉怀等人[39]分为裴李岗和贾湖类型,杨肇清分为裴李岗、贾湖和中山寨类型[40],李友谋分为裴李岗、贾湖和花窝类型[41],靳松安分为裴李岗、贾湖、花窝和班村类型[42]。
3.社会发展阶段和性质。裴李岗文化的社会性质目前学术界认识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裴李岗文化处于母系与父系氏族社会更替阶段,如张长安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属于母系与父系氏族社会更替阶段,此时男子开始处在社会统治地位[43]。有学者根据裴李岗文化墓葬反映的情况,认为当时应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44]。有学者认为当时私有财产已经产生,墓葬中的随葬品应是私人财产,是死者生前最珍贵的物品[45]。还有学者认为当时并未出现私有财产,如马洪路认为裴李岗文化仅有简单的社会分工,但由于在各个遗址内均未明确见到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交换现象,所以讨论私有财产为时过早[46]。
在裴李岗文化早期墓葬中,随葬品主要有石斧、石铲等生产用具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生活用具。随葬石斧、石铲、石镰等生产用具的墓主多为男性,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等生活用具的墓主多为女性,且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具一般不同出于一墓,这表明当时已经存在针对男女身体属性的社会分工,墓葬中的随葬器物,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们看重的是影响未来世界的生存手段,而非社会地位[47]。另外,裴李岗文化男女墓葬的随葬品数量早期差别不是很大,到晚期男性墓随葬品多于女性墓,这种情况从侧面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中即将有新的社会因素萌生。
裴李岗文化的墓葬多数都有随葬品,种类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等,有的墓还随葬有装饰品、粮食和兽骨等,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要将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带到死后世界的丧葬观念,并且多数人死后实践了这种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墓葬中发现了一些规格较小的陶器,制作粗糙,很像是专门制作的明器,而更为普遍的现象是随葬残损的陶器和石器,在有的墓地,这种残碎陶、石器比例可达50%,这说明,裴李岗文化的丧葬观念已经具有高度的仪式性和象征性了[48]。
4.文化源流。目前中原地区早于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仅有郑州李家沟、许昌灵井等遗址,这两处文化遗存早于裴李岗文化1000~2000年,与裴李岗文化之间缺环较大,且陶器发现较少,难以进行对比分析。有学者另辟蹊径,跳出中原地区的范畴,转而从整个中国来探索裴李岗文化的来源问题,如张弛先生从陶器群、绝对年代和经济形态三个方面着手,认为以角把罐和有鋬的钵为特色的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其内涵不同于裴李岗文化,年代早于裴李岗文化,大体与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和小黄山文化同时,其来源应在南方地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际开始向黄河流域推进和扩展,在与北方新石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催生了裴李岗文化[49]。
关于裴李岗文化的流向,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向后发展为河南仰韶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裴李岗文化为豫中地区仰韶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河南汝州中山寨、长葛石固等遗址发现了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从器物形态学角度观察,裴李岗文化的钵、鼎、罐等器类与登封告成八方和双庙沟仰韶文化早期同类器具有较为明显的传承关系,与大河村前三至前一期、中山寨二期也有较为明显的传承关系[50]。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烧造、制作技术、陶器器类造型、纹饰等特征都被本地区仰韶文化继承和发扬。
5.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裴李岗文化时期,嵩山地区周边分布有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顺山集文化、后李文化等,其中裴李岗文化最成熟。裴李岗文化在中原地区形成以后,开始向外传播,渭河流域、汉水上游、黄河下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都可以看到裴李岗文化的身影,这反映了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辐射作用。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裴李岗文化与同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向西南传播。笔者曾根据南阳一带的大张庄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如双耳壶、深腹鼎、石磨棒等器物,认为南阳大张庄遗址正是裴李岗向下王岗过渡的重要遗址。裴李岗文化的一支经南阳盆地到丹江下游,然后沿汉水先传入汉中盆地及渭河流域的宝鸡地区,在那里与当地老官台文化一道发展,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半坡类型文化[51]。张居中先生认为,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晚期一支向西发展,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下王岗早期文化[52]。
二是向西渗入,促进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前,不少学者对典型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认为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是半坡文化的源头,但不少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缺环。随后,考古学者在对河南新安荒坡、陕西零口、晋南枣园等遗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地区有一种统一的考古学文化——枣园遗址一期文化与半坡文化关系紧密。在枣园一期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折唇双耳壶,双耳壶壶口的折唇样式与半坡文化的小口尖底瓶如出一辙。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枣园一期中的小口平底瓶应该是裴李岗文化中蒜头壶和双耳壶相结合的产物,因为从瓶腹部、肩部和耳部的位置变化来看都与裴李岗的两种壶的演变规律一致。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临潼零口遗址发掘,发掘者认为零口遗址二期遗存可以称为“零口文化”,可能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前身,而且与庙底沟类型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发掘者还特别指出,零口文化的形成曾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应当是同祖同源。
三是裴李岗文化与江淮地区龙虬庄文化关系密切。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江淮流域存在着一支文化面貌独特、文化序列完整的原始文化,即“龙虬庄文化”[53]。研究者认为江淮东部不见距今7000年的文化遗存,而龙虬庄文化正处在贾湖文化的衰落期。从稻作农业来看二者继承发展关系明显,如贾湖的骨环等器物在龙虬庄遗址沿用,二者埋葬习俗一致,不少陶器存在渊源关系。
四是裴李岗文化向东北的推进与北辛文化的形成有关。高广仁、张居中、栾丰实等都认为北辛文化是后李文化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形成的,两者存在共同因素。例如,在两支文化的石器中均发现数量较多的大型石铲,在陶器上两者均存在一定数量的乳钉装饰以及乳头状足器物,小口双耳罐、三足壶、三足钵等器物的形制较为接近。栾丰实先生明确指出,“裴李岗文化是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54]。
6.科技考古。主要集中在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人类食谱分析等方面。张永辉等人通过对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遗物进行淀粉粒分析,发现石磨盘表面的淀粉粒,包括橡子、小麦族、粟或黍或薏苡属和根茎类四大类[55]。刘莉、陈星灿等人在研究孟津寨根和班沟两遗址石磨盘功能的过程中,通过对微痕和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两遗址的石磨盘表面有小麦族种子、薏米的颖果和栎属橡子等,也可能有少量小米,其中块根和橡子占大宗[56]。贾湖遗址浮选结果显示该遗址有十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这些植物包括稻谷、栎果、菱角、莲藕等,但稻谷遗存比例较低[57]。以上发现显示出裴李岗文化食物生产行为的存在,植物栽培在许多遗址内均有发现[58]。
裴李岗文化已经出现了动物驯化现象。渑池班村遗址发现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家犬个体2只[59],发现家猪比例较高,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57.57%,这一比例接近该地区仰韶时期遗址的同类数据[60]。贾湖遗址同样发现了驯化猪、犬现象,贾湖一期遗存即已出现家犬,并且还发现墓葬和居住区有埋葬家犬现象[61]。贾湖发现的家猪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家猪遗存[62]。
古人食谱分析是生物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裴李岗人群的食谱分析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目前只有贾湖遗址工作做得较多。胡耀武等人利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对贾湖西区墓地人骨进行了微量元素分析[63],结果表明贾湖早期居民以肉类食物为主,植物类食物为辅。随着贾湖居民对稻谷的驯化和长期食用,居民体内Ca的比例增加,而对猪和犬等动物的驯化,稳定了人们的肉类食物来源。用于检测贾湖居民微量元素的人骨样品随后被用于C、N稳定同位素分析,通过对比人骨的骨胶、C及N含量后,研究者发现贾湖居民主要以C3类植物为食物来源[64]。尹若春、张居中等人通过对贾湖人骨和猪骨牙釉质的锶同位素分析,发现14个人骨样本中有5个是从外地迁入的,这一发现不仅证明了锶同位素在研究古人类迁移方面的作用,而且还用技术手段论证了古代人类的迁徙行为[65]。
三、裴李岗文化研究展望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的核心文化,并具备农耕、文字、历法、祭祀等早期文明的重要因素,同时期相毗邻的其他考古学文化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它的影响,从这个层面观察,可把裴李岗文化视为中原文明产生的基础,同时也可把它视为中华文明产生的基础,也因此,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入选“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回顾过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裴李岗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关注。
在文明起源研究方面,对已有资料的分析研究有待深入。以墓葬为例,贾湖墓葬的规模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寡一致,规模较大的墓中有龟甲、骨笛、叉形器等成组出现的现象,当时社会分层和分化可能已经开始。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先发生社会分层和分化,从而迈开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当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66]贾湖遗址出现了文明要素的萌芽,骨笛的出现是由于巫术礼仪表现形式的需要。遗址共发现25支笛子,早期为五六孔居多,晚期多数有规整的七个音孔,每孔各发一音,加上七个音孔全闭合发出的筒音,正好为八音,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音阶。巫师用来占卜的龟甲和算筹的发现是巫术礼仪的另一种表现,贾湖遗址少数墓葬有随葬龟的现象,这些墓葬中出土有背腹甲扣合完整的龟壳,其中大多数龟甲内还装有深浅颜色不同的若干石子。
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刻画符号,在龟甲、石器、骨笛、陶器上发现刻符近20个,其中刻在龟甲上的符号,有的上下、左右对称,这些刻画符号的样式、书写载体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如出一辙,可以说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字的探索。贾湖遗址出现了祭祀现象,遗址发现有龟、狗等祭祀坑,还发现了酒等,使我们更加重视早期祭祀体系出现的时间。文明社会一些要素开始闪现,使我们认识到贾湖遗址应是裴李岗文化南部的一个中心性遗址。石兴邦先生指出:“舞阳贾湖遗址,是淮河上游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曾以其蕴藏之富、价值之高和意义之重大而被称为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67]石兴邦先生的话表明,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
聚落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过去认为裴李岗的聚落面积一般不超过10万平方米,但新发掘的新郑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遗址。聚落外围发现有较大型壕沟,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窑、灰坑等。唐户共发现房址22座,按其分布地域可分成4个相对独立的单元[68]。唐户房屋布局具有明显的规律,该遗址对研究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心聚落的出现以及社会组织结构和家庭形态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因此值得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裴李岗文化亟待解决的是来源问题,中原地区早于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仅有郑州李家沟、许昌灵井等遗址,以此为线索,对早于裴李岗文化1000~2000年的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势在必行。
多学科合作是考古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今后在裴李岗文化的研究方面应重视多学科合作的应用。多学科合作贯穿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各个环节,古环境考古、人类食谱、人骨DNA分析、动植物遗存的分析研究虽然取得了初步成绩,但相关数据太少,科技考古的任务还比较艰巨。
目前,裴李岗文化的相关考古资料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且具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为进一步提高史前区系考古的整体认识水平和研究深度,今后裴李岗文化的研究应当跳出地域樊篱,转而从华夏文明起源的宏大视野去考察,以推动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