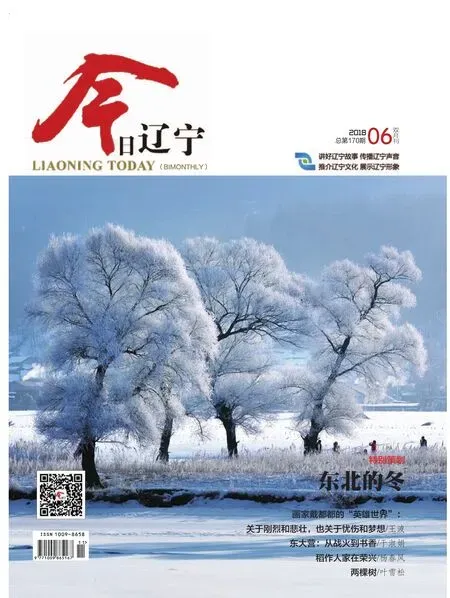画家戴都都的“英雄世界”:关于刚烈和悲壮,也关于忧伤和梦想
◎文 / 王波 Text by Wang Bo

戴都都
1963年出生,沈阳人
198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
曾任:
第六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第六届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辽宁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
现任:
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
辽宁画院名誉院长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其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美术大展并获奖

《向大师致敬》油画210×450cm
“从精神上讲,画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命运。他受到命运的驱使,只能成为画家。”
“画家的一生是一片片感动累积起来的。”
“站在画布前像国王,得意忘形、随心所欲地去创造;走在人群中是平民,脚踏实地、自由自在地去生活。这就是画家——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与国王和平民不分高低的人。”
“我真诚,有时也虚荣;我追求完美,也不拘小节;我尽量从容自在,也有忧郁和沮丧。”
酷爱读哲学的都都,每每语出惊人,他画画,他思想,很享受眼下这种守着同样是画家的漂亮妻子和被他称为“小太阳”的叫来来的小女儿的平静日子。他说,这足以抵御人生的各种欲念、狂妄、艰难和疼痛。

《满江红》油画175×175cm
像许多有才华、有作为、有无限潜质的画家一样,戴都都以其狂放不羁的艺术语言和作品所展现的激情和思考赢得长久不衰的喝彩与追捧。
在众多好评中,大画家宋惠民的感慨恐怕最能恰切地说明他的风格和品质:“在他的画前,你不能平静地走过,因为在他的画上跳跃着最激情的绘画语言。一种灵动、激情、冲动、挚爱而且燃烧起来的语言。”他说“仿佛人们都要被感化、被烘热。”
圈里的人都知道,都都长得帅气,穿着也时尚。才气十足的一个人,年轻那会儿都难免张扬甚至荒唐过。岁月过滤下来,接人待物更加彬彬有礼、热情周到外,个性上有棱有角、爱憎分明却没有变,做人的原则上总有股宁折不弯的劲儿。
全身心扑在画画和主持画院工作上,不喜应酬,可遇着对劲儿的朋友聚一起,还一个文艺青年似的,能喝个翻天覆地,全不拿身份和架子。
继他一举成名的《梦中的小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之后,二十多年来,《满江红》《与但丁讨论神曲》、“青铜时代”系列的《勇敢颂》《飞扬的心》《把酒论英雄》,直至后来被赞为“堪称当代中国油画的巅峰之作”的《向大师致敬》,他创造了一个个惊喜,每次画展都令人眼前一亮,深深攫住人们的眼球和关注,并以此巩固了其在关东油画界的领袖级地位。
如果说当年一举夺得全国美展金奖的《中国故事》表达了第一次美术大潮中,戴都都对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的发现与饥渴,那么在其后渐行渐远的创作实践中,则实实在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日渐清晰、日臻完善、坚实饱满而且始终如一的主题,那就是英雄主义。
戴都都的英雄世界不独有刚烈和勇敢,而且充满了诗人般的忧伤和梦想,那是一种贯彻始终的经由美术而阐述的哲学思考和人性关怀。
《勇士》在金黄苍凉的色调中,一位古代勇士手持长矛傲骨铮铮地骑跨在战马上,雄视着狼烟凄厉的战场,你不难联想到血腥和命运。
《满江红》一片晕红夺目的色调中,隐约看到虚幻的岳飞,壮怀激烈的英雄气概中,还隐隐散发出被“莫须有”罪名残害的忧伤和未竞的梦想。
《与但丁讨论神曲》更是跨时空地集合了古今中外100位惊天动地的豪杰和枭雄,真诚地讨论了人类进步的苦难而惊心动魄的历程。
采访都都的那个下午,偌大的画室透进暖暖的阳光,大小参差、层层叠叠的画面和生意盎然的绿植光影斑驳,贴满老照片旧海报的墙上,有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那是四岁时的都都,手握一本红宝书,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
都都在一个父母都是军人的家庭中长大,加之他成长在四十年前那充满着如火如荼地崇尚英雄的时代氛围中,骨子里的刚直坚韧和社会的陶冶养成,就这样延伸到他成年后的整个创作中。而那一幅幅萦绕着英雄情结的画作就像他生命中一路绽放的花朵。
变化来自2005年相继推出并给他带来更大声誉的以“青铜时代”命名的系列作品。我们可以看作戴都都的“后英雄主义时代”。作品加入了更为丰富、更多内涵的题材元素,从《把酒论英雄》里的奥运冠军,至《飞扬的心》里的残疾音乐家舟舟,到《向大师致敬》里的艺术家,进而到《十大元帅》那基于身世背景和命运的悲剧色彩,这种蜕变让我看到,戴都都的内心里对英雄的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层和宽泛,已从单纯的强悍、悲壮,转向于生命的奇迹、终极的关怀和人性中深藏的追求美好事物的勇气和担当。人们能感受到“青铜时代”的创作,技巧更自如娴熟以外,内在表达上也更加丰富、饱满和厚重。
戴都都不大关注什么学院、草根、流派,也不大关注什么写实和抽象,在他眼里绘画就是一个人生命的自然呈现,画家看到的、感受和理解的事物的本质的形象外化。他说,人们可以给一个画家冠以各种流派和风格的标签,但在画家,那是一种唯一对的方式,就应该也只能那样呈现,像诗人写诗,雕塑家塑像,不那样呈现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都都的画始终有一种不竭的热情,色彩纯粹饱满,笔触生动有力,画面洗练写意,我们能体会他豪情迸发、灵感突至时,不能自已、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灵魂战栗、快意淋漓。
《向大师致敬》最明白无误地向我们坦白了都都创作上的真正师承。这幅画里的七位大师,从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到“画不惊人死不休”的达利、毕加索,再到仙风道骨永不媚俗的齐白石和用几近一生的苦难和精力来表达人性思索和心灵感悟的罗马尼亚大师柯尔尼留•巴巴,无一不是对艺术创作充满激情的巨匠。人类艺术史上无人能及的巨匠米开朗基罗的创作以力量和气势见长,具有一种雄浑壮伟的英雄气概,而巴巴坚持认为“美术是一种只服从内心绝对主观原则的内心创造行动”,奠定他世界级大师地位的作品奔放恣肆,几乎能找到现代艺术所要求的单纯、概括、变形、写意等一切重要手法……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都都作品的令人震撼的风格,更不难理解都都尽管有足够娴熟的造型能力和写实功底(《祈祷》《中国故事》等),画面却越来越单纯,越来越情绪化。即便是形象比较写实的作品,如《与但丁讨论神曲》和《向大师致敬》等也更多地贯注了现代的元素,无中生有的情境,时光的交错,笔触的夸张,形象的变形,以及力求神似的写意。

《雄心百年》油画 210×600cm

《宠辱不惊》 油画 165×205cm
画家的艺术表达,说白了就是用色彩、线条、结构留给世人的内心印象,这印象泄露着画家的人性、状况和世界观。
著名词人化方最近在抨击艺术界急功近利、沾满铜臭的可悲现状时说,艺术家应该很纯粹,一心一意做自己内心里的事情,对艺术都很虔诚,并有敬畏之心。我们相信,都都呈给世人的那些纯美的画面就来自这种内心的干净。
这些年,与其说戴都都在画画,不如说他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不断亮出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都都说,“英雄很勇敢,但英雄也会疼”。近几年他经历得太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在中国画坛赢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声誉;他号召并创立的当年鲁美同学的“约定”艺术展,已成功地举办三届,成为传承和弘扬鲁美精神的一大盛举;他也经历了母亲、父亲相继离世的刻骨的悲痛。这对格外敏感的艺术家来说,不啻一种极为严重的打击和震撼,他真切地看出了生命的残酷和无奈。
都都崇拜充满革命精神和悲悯情怀的托尔斯泰。他以前画过一次,托尔斯泰怀抱公鸡,表情凝重而柔情,充满对世界的关注和对美好的向往。而最近他画的托尔斯泰,则目光坚定而决绝,将公鸡像火炬一样高高举过头顶。仿佛是表明对生活中的种种误解、委屈、无奈的抵抗、隐忍、坚持,俨然一副不屈的挑战的姿态。而都都最新创作的色调凝重的自画像,眼神里也放射出经过生命的悲喜境界后那种淡然和刚毅。
王波:请你谈谈自己的创作分期,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都都:一个艺术家一生追求的创作应该是一个整体,无论从思想上和艺术性来说,米开朗基罗说他的作品早就存在,他一生都在完成它。所谓的阶段和变化其实是整个创作的一个过程,技法娴熟思想成熟的过程。每个画家一生都在完成他认为有最大价值的一个主题。
王波:那么你在塑造的主题就是英雄主义吧?
都都:青少年时代很长的时间我想的就是当兵、当英雄,这个理想后来就反映到我的画中。当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英雄会有更多层面、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表达,相信人们会在我的作品中看出。
王波:你曾说过“反对画家除了画画一无所有”,那么现在你觉得除了绘画上的成就,生活中你还有什么收获?
都都:能从事自己特别想做的事,这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做到的。我作为画家能随心所欲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你想一下,其实生活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业不发工资你都未必去干。这是我收获的最大幸福。
王波:以前采访时你说反对画家用一种手段画画,你尝试过什么手段?有何体会?
都都:我作画比较喜欢强烈的色彩,喜欢放射性的笔触,这不是设计的手段,而是由画的内容决定的。有人为了追求所谓个性,机械地寻找一种区别于别人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刻意去标榜什么流派,我觉得是创作上的一种偏离。
王波:你画画通常很有快感吗?有没有压力?主要是技法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都都:画画的过程肯定是辛苦的,但乐在其中。这有点像爬山,有时找不到达到目标的手段,瞬间就会有压力,很苦闷。当手离心最近的时候,表达得很畅快,就会体验到豁然开朗、瞬间释放的快感,应该说正是这种快感诱惑一个画家愿意一次次地去开始画下一幅作品,明知道这个过程还会很痛苦。
王波:听晓非(都都爱人)说,一次你要画刘关张三结义,半夜还在画室里苦思冥想,不曾想,第二天早晨,她竟看到你画完了整个结构和人物?
都都:有时候我也惊异于这种神奇的事,画家很多时候是焦灼不安的,无数东西想要表达却无从落笔。也突然会有一个时刻,灵感突至,停不下笔来,我觉得有种一泻千里的快感,那是对画家最好的奖赏。很公平啊。
王波:青铜时代有哪些系列作品?你当初确定和命名是想要创造新的画法和倾向什么流派吗?
都都:画《青春》的时候,人都像飞起来了,有腾飞的感觉,像《把酒论英雄》《爱书》,画舟舟的《飞扬的心》,还有《勇敢颂》,都属于此。我想不能用主义、画派去给作品归类。有人说画法上倾向象征表现主义,但毕加索、德库宁的是完全舍弃了形,我的画只是略有夸张,强调一些变形,色彩上追求金属那种质感,根据内容去处理一些虚实的关系。那样命名主要是因为青铜能赋予画面和人们联想一种雕塑性和厚重感。
王波:请你谈谈现在中国的油画市场和辽宁油画的现状。
都都:我对市场不是很了解,也不热衷。
王波:外面有人传说戴都都的画很值钱,你怎么解释?
都都:有一天你的画舍不得卖的时候,你就能卖了。不用你画家去宣传去秀。有些画卖了,心里很失落,不愉快。我的《爱书》,我商量着加价买回来,人家没答应……有人问我,什么画值钱,我说你喜欢得舍不得卖的,或者卖了还挺伤心的画。
王波:作为辽宁画院的名誉院长,请你谈谈辽宁的油画。
都都:作为画家吧。辽宁是美术大省,辽宁的油画其实很厚重,很有实力,当然这跟市场毫无关系。特别执着的画家不会去迎合市场,从历史上看,一幅画的质量和价值与经济价值往往不成正比,像许多艺术大师,包括毕加索。
王波:如果让你试着说出你最崇拜的三位艺术大师,你会怎样排?
都都:我有三句话:崇拜米开朗基罗,羡慕毕加索,喜欢巴巴。蒙娜丽莎达到一定技巧和成熟你可以画,米开朗基罗你临摹都做不到。那是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峰。我羡慕毕加索的得意忘形、随心所欲,而且很早被世人承认。至于巴巴,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我从他那也得益最多,他的象征表现主义,很现代。当然,画法之外我更喜欢他对生活和精神上的苦难的不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