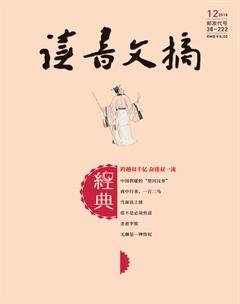不要教下一代做人
王烁

“弗林效應”讲,过去100年来,全世界人的智商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以美国为例,平均每年智商上升0.3个点,已经持续了50年。如果100年前的美国普通人穿越到今天,其智商比今天的美国普通人低30个点,基本是弱智。荷兰人更夸张,从1952年到1982年,智商30年涨了22个点,平均每年超过0.7个点。弗林认为,智商提升的终极原因是工业化,而直接起作用的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整体变化:更普及的学校教育、日常工作乃至生活对认知能力要求提高、家长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等等。
智商只是可测的指标,真正重要的是想用它来反映的智力,特别是通用智力,简称“g”。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很行但做别的不行,那么他只是擅长做某件事而已,人不见得聪明;但如果他做什么都行,那么他多半比较聪明,就是说“g”值高。同一人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有一半左右可用“g”值来解释。
没有谁是天生的音乐家、棋手、数学家,或者其他。这些技能出现得太晚,时间太短,进化还来不及重新搭建专门的大脑回路。这些人有天生的高“g”智力,但不是必然只能在特定的领域里成功,换个领域,努力程度不变的话,一样成功。
智商测试有多个模块,对通用智力的要求有差别,分解“弗林效应”,发现其主要发生在对通用智力要求不太高的模块里,而对通用智力要求较高的模块影响很小。智商研究界由此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百年来人类智商涨分没有实际意义,因为通用智力没有变化。弗林代表的另一派则这样回应:如果问题是“我们出生时的大脑是不是比祖先的更有潜能”,答案是“否”;如果问题是“我们是否面对比祖先更宽广的认知挑战,并发展出新的认知技巧以应对这些挑战”,答案是“是”。
弗林说,人类百米短跑早已跑过10秒大关,跳高则几无变化。人的体质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社会更重视百米跑,所以成绩主要出在这里。但难道破10秒就没有意义?同样,智商提升的那些测试模块,对应着人们抽象能力的提升。我们的先辈习惯具象,较少抽象。今人则不然,对抽象思维的训练和挑战不仅在课堂,早已渗透到社会与家庭的所有方面: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电影、电视和电游也是这一代人智商提升的重要环境因素。几十年前的经典电影,回头看常常会觉得太幼稚,并非偶然。
所以说,代沟是真实存在的,坚实地存在于代际之间的认知能力差别,不是说一代人如何调节对另一代人的态度就能化解,我们觉得上一两代人像弱智,下一两代人觉得我们像弱智,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代沟最好的尊重,就是对上一代人好一点,因为他们智商比你低;不要教下一代做人,因为他们智商比你高。
摘自《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