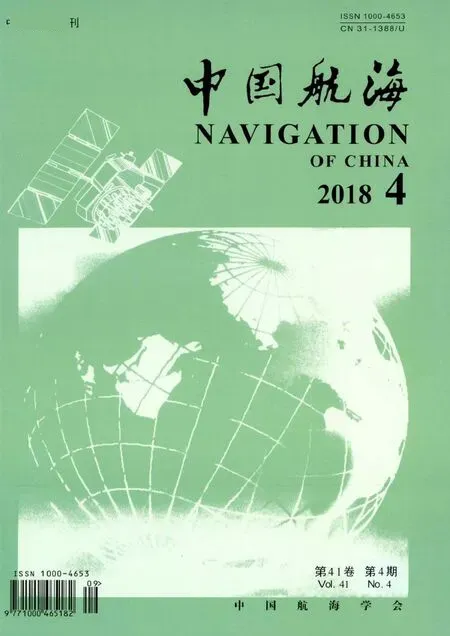论海上人命救助搜救国协调权
李志文, 冯建中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海上人命救助中搜救国的协调权是指在海上遇险事故发生时,搜救国为尽快拯救海上遇险人员而对其他相关国家所实施的指挥与调度的权利。搜救国的这一协调权是一种笼统性的权利概称,它既包括搜救责任区的缔约国对前来参与救助的国家所进行协调的权利,也同时包括一国基于本国领海主权对其他搜救国之救助船舶在本国领海进行无害通行行为所实施的管理与安排的权利。[17]搜救国的协调权在《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以下简称《1979年搜救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中都有着规范上的体现,是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海上救助合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家之间所缔结的相关协定,都未涉及搜救国在依法行使这一权利时所产生的竞合问题。在搜救责任区缔约国数量众多,或在其他船舶不可避免地进入本国领海从事救助活动时,缔约国或沿海国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必要的合作,并让这种指挥和协调权利真正地为救助海上人命这一目的而行使,成为现代海上人命救助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研究搜救国的协调权,首先要厘清这种权利产生的根源,并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行使这一权利时所面临的对峙情形和可能产生的冲突,进而提出缓解这种冲突的方式和相关建议。
1 搜救国协调权的理论权源
研究搜救国协调权之前,应首先分析该权利产生的理论权源,明确该权利派生的依据。搜救国协调权的理论权源是多元和广泛的,主要有3个方面。
1.1 主权论
在海上人命救助中,搜救国为尽速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可能会通过其他国家的领海,而在通过之时也可能会从事定位、搜寻乃至探测等其他活动。[2]这些活动都可能对沿海国的领海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对沿海国正常在本国领海内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负面的干扰。基于此,沿海国可根据本国领海主权的排他性,协调并指挥其他搜救船舶无害通过本国的领海[3],这被称之为由主权而派生出的协调权,其理论范畴尚在本国国内法的宽度之内。
1.2 契约论
这里所谈及的契约,实质上即是国家之间所缔结的搜救协定,从术语上讲它可被称之为constituent instrument。同时,除了调整并规范缔约国的行为之外,一旦它同时具有形成某种组织的功能,那么这种契约还会被称作为rules of the organization。[4]相比于抽象的主权论而言,契约论所赋予的“协调权”会体现得更加直接,且往往会在条约或协定中给予直接的表达和体现。[5]在海上救助中,国家与国家之间会根据所缔结的协定成立某个救助组织,而在该协定中明确搜救国协调权的行使规范。
1.3 道义论
在海上人命救助中,对人命进行救助的主体并不单单是海上搜救责任区的缔约国,还有可能来自于参与救助的人道主义救援国。当人道主义救援国进入到其他国家之间所形成的搜救责任区时,责任区域内的缔约国会对人道主义救援国的救助行为进行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以保障其救助活动能够助力于搜救责任区内的缔约国。在这种情形下,协调权就会存在于海上搜救责任区的缔约国与人道主义救援国之间,从而使道义论成为协调权的权源。在现代海上救助活动中,不宜苛求或死板地按照公约或协定作为协调权行使的唯一来源,这种基于道义而产生协调关系在海上救助活动中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鼓励。
2 搜救国协调权的竞合
搜救国协调权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同时任何一国也不会无故从国际法上获取更多的协调权以对其他国家合理从事救助活动而进行不正当的干涉。然而,基于平等状态下的搜救国之间可能会在执行某项具体的救助任务而同时行使这一协调权时产生一定的竞合。基于协调权权源的差别,这种竞合可以分化于3个范畴。
2.1 主权与契约权源间的纵向竞合
主权与契约权源间的纵向竞合表现在海上救助的通行问题之上,且在领海通行中激化并伴随着搜寻这一情形。
1) 当条约或协定赋予搜救责任区内缔约国行使这一协调权之时,该国可能会基于搜寻航线和路程的需要指挥救助船舶无害通行至其他国家的领海,此时领海国同样享有协调或指挥权,以管控或规范救助船舶的通行,两者之间就表现出一种基于主权下的协调权与基于公约下协调权之间的纵向竞合。[6]
2) 在救助实践中,救助船舶无害通行权成立和行使的困境、救助船舶进入领海搜寻之禁止、救助船舶越过他国领海所必须履行的通知义务并接受沿海国合法的管理与安排等情形都是这种纵向竞合的直接体现。
3) 在特征上,主权和契约权源的纵向竞合包含两种不同属性的协调权,两者产生的法律和理论的依据都有差别,故而会存在明显的顺位。这表明在特定的情况下,契约权源下的协调权应该让位并遵从于主权权源下的协调权,只是在何种情形或程度下才能体现并运用这一顺位,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分析。
2.2 契约与契约权源间的横向竞合
与纵向竞合不相同的是,搜救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或协定之中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明确这一协调权行使的主管机关以及行使的必要规范。然而,无论做何种规定,这种协调权都不可能逾越条约或协定,产生出另外一种不同维度的权源。在同一协定之中,国家可能根据实际的救助需要组建一个合作组织,并规定缔约国协调权限的范围。一般而言,这种协调权均是平等地、无差别地赋予条约或协定内的任何一个缔约国。例如,《1979年搜救公约》和《北极航空和海上搜寻与救助合作协定》的行文都使用了“各缔约方应”或“各方应”这样的词语,表明从事海上救助各方参与的平等性。[7]
2.3 契约与道义权源间的一般竞合
海上救助离不开人道主义救援国的配合与加入,为有效整合救助资源,搜救责任区内的缔约国往往也要协调并组织前来进行道义性援助的国家,以保障它们顺利从事海上救助。然而,即使是出于道义上的帮助,人道主义救援国本身也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参与救助且享有协调权。当这种权利面临搜救责任区内缔约国的协调权,且人道主义救援国是有意进入他国责任区内进行救助时,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配合与被配合、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需要明确的是,这两种协调权的竞合往往是随机、临时的,而并不涉及主权或是条约和协定的遵守等问题。因此,契约与道义权源间的竞合具有一般性和机动性。
主权、契约与道义权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是搜救国协调权竞合的直接体现。如果搜救国之间并没有通过演习或是其他方式形成一种相互的默许,那么协调权的行使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从而阻碍海上救助的进展,延误黄金救助时间。
3 搜救国协调权竞合下的冲突
搜救国协调权间的冲突根源于该权利的竞合,并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3.1 搜救权与领海主权之间的冲突
这一冲突是主权与契约权源间纵向竞合的结果。海上救助活动的目的是拯救遇险人员生命,理论上应尽量便捷救助船舶的通行,或至少在排除救助船舶进入他国领海进行搜寻的前提下保障其领海无害通行权的行使,即迅速、不停、无害地驶过其他沿海国领海。然而,根据《1979年搜救公约》第三章3.1.3的规定,除有关国家之间另有协议外,缔约方的当局只是为搜寻发生海难的地点和救助该海难中遇险人员的目的,希望其救助单位进入或越过另一缔约方领海或领土者,须向该另一缔约方的救助协调中心或经该缔约方指定的其他当局发出请求,详细说明所计划的任务及其必要性。换言之,公约已经明确即使越过另一缔约方领海,通行国也要承担相应的时间和沟通成本,其并不可能完全享有《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无害通行权。该冲突实质上是搜救国协调并指挥救助船舶抵达涉事海域从事搜寻救助活动的权利与沿海国协调并指挥他国船舶越过自身领海权利之间的冲突。
3.2 各国搜救计划或预案之间的冲突
这一冲突是契约与契约权源间横向竞合的结果。国际公约的目的是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合作,然而,由于搜救公约与救助技术分别体现法律和技术两个不同维度,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并不代表技术水平上的平等,而国家搜救计划往往反映的是本国的救助技术水平。[8]公约或协定不可能从法律上区分缔约国本身行使协调权的差别,从而在制度上直接或间接地限制缔约国中的某几个国家的权利。但是,如果公约或协定之中就某些问题并没有明确进行规定,那么搜救国之间往往要根据本国的搜救计划或另外达成某种其他协定来解决。如果各国搜救计划之间存在冲突,例如搜救责任区涉及争议海域,即使存有公约或协定,协调权的行使也不可能在一个完整的顺序链条内,很可能会出现混乱乃至冲突的情形。[9]
3.3 条约约束与非条约约束之间的冲突
从契约与道义权源间的一般竞合上看,搜救责任区内的缔约国与人道主义救援国之间都存在协调权的行使问题,只不过前者源于契约或协定,并在所缔结的搜救责任区内行使,而后者单纯地源于人道主义救援国以及搜救责任区内的缔约国各自的搜救计划或预案,甚至是人道主义救援精神,不受任何公约或协定的影响。然而,海上救助的顺利进展来源于力量的整合而不是分散。因此,如果不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有机配合,反而让这些国家各行其是,单一地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协调处理,这些协调权之间不但会产生摩擦和冲突,对救助目的的实现也无帮助。
搜救国协调权竞合下的冲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和立法原因,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 效率优先还是程序优先的问题存在争议。沿海国协调并指挥他国船舶越过自身领海的权利与搜救国协调并指挥救助船舶抵达涉事海域从事搜寻救助活动的权利之间的冲突才会凸显出来。在海上险情发生时,遇险人员的生命安全是头等重要之事,在遵守《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海上救助活动应该首先考虑遇险人员的安全情况,并基于海上救助的客观状况进行合理的布局。具体而言,这些布局需要考虑到遇险人员落海之时能够维持的时间、不同搜救责任区内海洋洋流的循环状况以及不同区域海水内的实际温度等,注重合作程序的有效性以及时效性,从而体现出海上救助活动中国家合作程序以保障遇险人员的生命权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因此,若要解决协调权纵向竞合所引发的冲突,必须要在效率与程序的价值位阶上进行必要的选取,以调和因竞合行为所引发的冲突而带来的不利后果。
2) 国际法维度上的协调权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这是对横向竞合所引发冲突的原因解释。由于公约或协定在赋予各国相关权利时往往要考虑到分配的平等性和均衡性,加之搜救国协调权的行使是一种动态的且负有技术性意义的权利,因此,这种权利的行使往往不能直接从公约或协定之中得到充分的依据,反而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救助技术、能力和信息等其他非法律因素而确定。既然从法律的角度对其进行规制的力量有限,那么这种协调权的对峙就会变成搜救国之间救助力量的横向对峙。从救助技术及国家主权的含义出发进行考量,一国很难在国际法维度之外对其他前来协助从事救助的国家实行技术上的指挥,其他国家也没有足够的法律上的理由信服这种协调和指挥权对自身的规制,因此难免会引发协调权之间的冲突。
综上所述,国际法维度下搜救国协调权的冲突根源是理论上的对峙及立法上的宽泛,然而,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并不必然需要从这种对峙及宽泛之中寻求一条直接且明确的路径。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调和这种理论上的对峙,并在实践中回到技术范畴内寻求国家之间的深入合作,才是搜救国协调权得以顺利行使的重要解决途径。
4 搜救国协调权冲突下我国的调和方式及应对
我国作为东亚最大的沿海国家且作为《1979年搜救公约》的缔约国,参与海上救助活动自然也是十分频繁。面对搜救国协调权间竞合及冲突的状况,我国必须要明确自身应对权利冲突下的调和方式,以保障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海上救助合作的顺利开展,及时救助海上遇险人员。[10]
4.1 理论
在保障沿海国根据《海洋法公约》享有权利的基础上,坚持人命救助效率优先。在海上人命救助中,将效率和程序之中的任何一面进行绝对化的思考,片面强调某一项的做法是有害的,但是完全将两者不分场合等同并且丝毫不做任何区分也同样是不利的。为确保及时、有效地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在实施海上救助活动时应坚持效率优先:
1) 应该首要地注入“保障遇险人员人身安全,及时救助海上遇险人员”这一理念,同时要以此为轴心采取救助行动,在程序上应尽可能地便利对遇险人员的尽速救助。
2) 在实体制度上应该肯定其他缔约国救助船舶无害通行沿海国的基本权利,避免繁冗的通报、批准等程序从而延误海上救助时间。据此,搜救权与领海主权之间的冲突就能够迎刃而解,并朝着搜救国协调和指挥救助船舶抵达涉事海域从事搜寻救助活动的权利方向靠拢。
4.2 实践
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救助演习的力度。这里的合作对象不应局限于周边国家,更应重视与已经或即将同我国缔结海上搜救协定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围绕着搜救国协调权的行使冲突,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
1) 有利于各国就协调权的行使达成良好的默契。既然搜救国协调权本身并不单纯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权利,那么实践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海上救助中行使及运用这一权利时就需要相互之间的默契和配合,而建立这种默契和配合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国家之间的救助演习,其中包括制定相对完备的救助合作计划、进行实战操练等。
2) 有利于各国重新检视搜救公约或协定与搜救国协调权行使之间的空隙。尽管搜救国之间订立的公约或协定并不能赋予搜救国协调权行使的全部所需规范,但是它确实是这一权利行使的重要依据和实际来源。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救助合作演习的进行与互动,能够使搜救国之间重新审视公约或协定实施的可行性,避免公约或协定的规定落空。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协调权的分配和行使等问题,搜救国之间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以尽可能地明确这一权利的具体行使方式,从而避免因契约与契约权源间的横向竞合所引发的冲突。
4.3 立法
在我国未来的海洋基本法等相关立法中明确海上人命救助的相关规范。从我国自身的角度出发,协调权的行使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同时,针对如何与其他国家合理地进行沟通,并正确分配和行使这一权利,也需要我国在相关立法的涉外部分做出规定。包括主体上要明确涉外救助协调权行使的主管机关,内容上要明确这些机关参与国际海上救助活动时的决策范畴、事项以及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这一权利时所应该遵循的平等、适当原则。同时提倡并鼓励我国与周边国家从事海上救助演习活动,规定我国主管机关应制定相对完备的救助合作计划,并加强与合作国之间的救助合作演习,从而有效地完善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救助合作内容,依法行使搜救国协调权。
4.4 机制
建立与不同救助主体的多层次沟通机制。国家之间在海上救助的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救助数据和信息需要在救助方之间进行传递,比如救助现场的信息、可提供的港口及补给能力的详单、救助人员培训方面的信息等。这些信息之间的互通过程都必然会涉及到协调权的行使,从而正确地处理并运用这些信息,以及时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因此,建立与不同救助主体的多层次沟通机制,能够给国家之间协调权行使的摩擦增添更多的“润滑剂”。
1) 建立信息共享中心。可在所确立的海上搜救责任区内设立信息共享中心,各救助方共享海上险情信息,协调行动,及时做出应急处理。各缔约国可以指定国内相应的救助机构作为信息联络点,并向海上信息共享中心派驻协调员,负责与本国的救助机构联系,共同承担海上人命救助责任。
2) 定期开展交流活动。以会议、多媒体乃至救助机构之间互访等多种形式与其他国家交流救助经验及技术,分享救助合作海域的环境、气候等信息,借鉴别国先进的救助理念以弥补本国管理机制中的不足,为具体的救助合作实践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通过完善这两方面的沟通机制,为搜救国协调权注入更多“软性物质”,将因协调权竞合而产生的冲突降到最低值。[11]
5 结束语
海上人命救助中搜救国的协调权是一种多权源之下的、旨在尽速拯救海上遇险人员所实施的行动上的指挥与调度的权利。当多个国家参与海上人命救助并共同行使这一权利时,就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权利竞合,在沟通不畅或合作实践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相应的冲突,阻碍海上救助合作的顺利开展,延误海上救助的最佳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应以及时、有效地救助海上遇险人员为导向,在保障沿海国根据《海洋法公约》享有权利的基础上,坚持人命救助效率优先,在实践上加强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救助合作演习,并同时做到立法和机制双构建,以缓解因协调权共同行使所产生的摩擦,提升海上救助合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