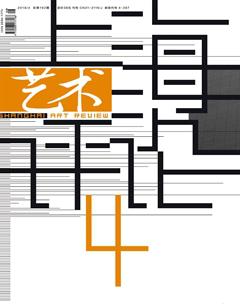“一带一路”视角下乌兹别克斯坦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现状
于蒙群 文婷婷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日益紧密,笔者于2017年10月跟随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团队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考察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通过集中的非遗田野调查、采访非遗传承人等方法初步归纳了乌兹别克斯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模式与发展现状,并进一步提炼相关问题,试图通过乌兹别克斯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察与研究为我国非遗保护提供案例及解决方案。
考察背景
处于“丝绸之路”要道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习俗。从公元1世纪开始,即与中国保持着持续密切的友好往来关系。7~8世纪,并起称雄的“昭武九姓”几乎都集中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并与当时的唐王朝往来频繁。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文化城市撒马尔罕是当年丝绸之路的重要汇集点,不同方向的商人在此集聚、贸易。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绘撒马尔罕:“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鬱,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1在公元7~8世纪玄奘所处的时代,撒马尔罕以“机巧之技”等手工艺蜚声一时,这些手工艺中的一部分保存到了今天,成为乌兹别克斯坦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考察了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区,针对当地以手工艺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希冀能够对国内非遗发展提供參考作用,并以助力 “一带一路”重大文化战略活动具体、深入的实施。
乌兹别克斯坦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与发展现状
在笔者调研的三个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中,塔什干作为首都,无论是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层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聚集方面,均能够反映出该国境内非遗保护的现状及与非遗相关的产业发展情况。而撒马尔罕、布哈拉两城作为该国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城,手工艺都保留着较为系统完善的传承体系和手工艺人聚居地,是研究非遗人才流派、分布区域、传承体系、延续现状不可或缺的重要区域。
1.塔什干
塔什干主要的手工艺基地位于哈兹罗提伊莫姆广场(Hazroti imom),这里由几座清真寺及神学院组成,现在成为当地传统手工艺人及工艺品集中制作、展示、销售地区。这里集中了木雕工艺、金属錾刻工艺、陶瓷彩绘烧制技艺、细密画绘制技艺等10余种传统手工技艺,分布在30多个制作作坊,这些手艺人年龄范围包含十几岁至六十几岁的老中青三代。通过采访手艺人,发现当地非遗主要通过家庭关系传承,其中一位漆器细密画家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人。他向笔者介绍了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支持方式:“政府将他们聚集起来,减免部分房租费用,并给予一定的补助,色彩颜料等手工艺原料有些也是政府提供”。笔者认为当地政府通过集聚非遗传承者,起到一种粗放的保护作用,如果任由他们散落乡间,结果只能是逐渐消亡。
另外一个手工艺聚集区是塔什干最大的集市—楚苏巴扎(Chorsu Bazaar),这里是纺织品、铁器、金银器皿、地毯等商品的集散交易地,更加贴近市场,其他城市或乡村的手工艺人将作品在这里集中出售。笔者在一家综合性的手工艺店铺中采访到了一位来自布哈拉的金属盘錾刻彩绘工艺传承人帕西姆(Paxnm),他自称是第七代传承人,并向笔者介绍了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金属盘錾刻彩绘工艺的保护发展情况,他们的工艺依旧延续传统时期的纯手工制作,但为了更好地销售,在图案纹饰上根据顾客的倾向进行了一些变化与创新。在传承方面,学徒们能够得到免费的手工艺教育。在布哈拉有手工艺传习所,学习时间也较长,仅图案就需要1年,但徒弟只要学成就可以单独发展。目前全国能够熟练掌握所有金属錾刻彩绘工序的手艺人只有20多个,是一种较为珍稀的非遗品类,国家对他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提供部分制作材料、补贴并帮助寻找销路。
塔什干的手工艺生产及销售多集中于市区,在郊区村落存在个别特色的非遗案例,其中以塔什干乌尔塔契尔契斯克区东干村为代表,居住在东干村的东干族是中国清代时期回民的后裔,他们的族群可以说是清代回族文化的活化石,语言、民俗、刺绣工艺、烹饪技艺、儿歌口诀等非物质文化形态均保存下来。其中代表性的手工艺是传统服饰,通过传统刺绣技法,将中国传统刺绣纹样绣于云肩、袖口之上。至今这些传统服饰还应用于他们的节庆仪式、婚丧嫁娶及日常生活中。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承载单位,乌兹别克斯坦回族文化协会会长、东干村前村长白东山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非常重视,撰写过大量东干族文化书籍,但由于大部分东干族后代移居城市,东干村也有类似中国“空巢村”的危机。中国大使馆给予东干村大量援助,包括资助东干族后代赴中国留学,并出资帮助白东山出版书籍,此举有益于大中华文化圈的非遗保护链条建设。中国的非遗并非只存在于本土,中亚、东南亚等地都有大量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如何保护这一部分非遗,将其与国内相关品类非遗共同保护形成大范围的中华非遗链条是相关部门应该重视的举措。
2.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古城,也是文化遗产最为集中的城市,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The Registan)既是撒马尔罕的文化遗产中心,同时也聚集了部分手工艺人,包含丝绸刺绣艺人、陶瓷匠人等。
笔者在雷吉斯坦手工艺聚集区发现一位正在刺绣的女手艺人,她正在绣一件石榴纹饰的披巾,以棉布为底,用丝线刺绣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刺绣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有纯粹丝绸的刺绣。已经传承了三代的女手艺人工艺熟练,也注重培养后代作为技艺的传承者。乌兹别克斯坦的手工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丰富的装饰图案及鲜艳的色彩使丝织品极具装饰性。太阳、生命之树、花卉、水果、攀缘植物等装饰母题体现了乌兹别克斯坦民间文化丰富的诗意和民俗意象。
在聚集区的另外一边,一对受过系统美术教育的兄弟向笔者介绍他们自己设计的陶瓷盘,陶瓷盘在乌兹别克斯坦既可以用来盛放抓饭,同时也可以悬挂于墙面作为装饰,是必不可少的手工艺品。两兄弟同时也向笔者介绍了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陶瓷工艺的危机,乌兹别克斯坦的陶瓷制品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变化。为了寻找市场,许多手艺人调整风格以适应低级品位的游客,这常常会导致失去基本的传统和风格的特殊性,陶瓷艺术也变得更加程式化。培养陶瓷手艺人并不容易,传统的陶瓷制作系统与流程现在已经变得过于简化。因此,当市场腐蚀了传统的高技能大师的训练体系时,也就降低了乌兹别克斯坦陶瓷的整体标准。
在撒马尔罕,政府设立了手工艺研究中心,一座两层的老建筑里聚集着木雕、陶瓷、传统服饰、刺绣、纸艺、首饰等手工艺门类,与雷吉斯坦广场喧嚣的环境不同,这里更加幽静,手艺人们也能更多的投入到设计和制作中,在延续传统手艺的同时,一些手艺人也进行了部分创新,例如在纸艺工坊中,手艺人用传统纸张制作成了各种适合现代人携带的卡包、信封等物品,颇受消费者欢迎。
3.布哈拉
布哈拉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的手工艺集聚地,保留了伊斯兰与中亚传统文化与技艺的精华,这里分布着木雕、金属錾刻、挂毯制作、细密画技艺等多种传统手工艺。旅游与非遗在这里结合得更加紧密。古城和清真寺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地区。17世纪的清真寺改造为布哈拉手工艺中心,集结了30个手工艺作坊,是手工艺人展示技艺、销售作品的集中地,也是手工艺品与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种买卖店铺和作坊按种类分布在不同的街道或街区内;行业的集聚便于手艺人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在这些各类手工艺行业中,形成了由手工业者组织的行会:手工业行会由一位资深师傅担任会长。布哈拉手工业行会组织具有严密的行规,对工艺严格保密,这些工藝就像现在的专利权和版权一样,也是一种财产。行会师傅会对该行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以保证达到公认的标准,还要管理税金的分配、征收及工艺品价格的调整。
如今,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手工艺受到了巨大的关注。政府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审慎态度使其进入国家政策的第一梯队。手工艺传统的复兴源于独立后维护民族文化的美好愿景。在过去几年中,政府通过了几项有关复兴国家手工艺和传统的法律。一些国家艺术家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应用艺术学院的院士,建立了全国艺术家和工匠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分散运行。这些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被遗忘的部分艺术史,并协助制造和销售产品的手工业者。
整体来看,乌兹别克斯坦手工艺保护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集中管理,政府为这些手艺传承人提供场地,集体规划,并在原料、房租等方面给予补助和支持。这种集中化的管理延续自苏联时期的集中化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简单粗放,仅仅能够维持现有的非遗样态,手艺人集中于各个城市中心的清真寺或神学院来展示、销售手工艺品,形成非遗+旅游的模式。这种模式使手工艺过于靠近市场,消费者的喜好势必会影响工艺的发展。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在传承过程中具有生产性、生活性、创造性、独特性等特征。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已经开始行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非遗+旅游的集体扶持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但在笔者看来,如长期持续下去,其中存在着不少隐患与问题。
第一,乌兹别克斯坦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体系,自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获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非遗名录中有54项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文化体育部共和民间艺术中心批准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国家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最佳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与相关非遗对应的只有掌握各自技能的手工艺者或表演者,这些人有时会被政府授予“大艺术家”之类的荣誉称号,但没有严格认定的传承人体系,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只能像撒胡椒面一样平均分配,无法精准扶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者,这势必导致保存下来的非遗技艺存在良莠不齐的局面。
第二,建立手工艺中心等形式的非遗传承集中地对保护非遗有一定的作用,但据笔者观察,聚集起来的手工艺,其技艺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减少,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程式化的工艺流程,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传承及保护不利。
第三,手工艺的程式化转变一方面与聚集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旅游业相关。手工艺中心作为一种集制作、展示、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场所,大多建立在市区中心位置以吸引外国游客。虽然此举对手工艺者的生存有一定帮助,但外国游客对乌兹别克斯坦手工艺的精髓不甚了解,往往追求廉价,这就使手工艺者将工艺简单化、批量化,价格下来了,但技艺的精髓丢失了,搭载丝路文明的各类手工艺品开始沦为旅游纪念品。
结语
乌兹别克斯坦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虽有起色但总体经济实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具有强烈的非遗保护意识,并将手工艺等非遗品种集中管理,提供原始材料与租金减免的优惠,“努力维护手工艺品的地方特色,恢复被遗忘的形式和图纸。”对于政府来说,这样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其中也有值得我国学习的地方,但粗放型的管理扶持政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还远远不够。要更好地使非遗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名片,首先,明确各级传承人体系,并对部分濒临消失的非遗进行精准扶持与大力保护;其次,传统师徒培训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与提升,并建立非遗传承培训机构,让非遗传承者的“个体经验”真正转化为“国家记忆”。最后,以文字、录音、视频等方式对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和技艺进行原真性记录,建立非遗数据库,更科学地保护非遗。
于蒙群 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博士
文婷婷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博士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