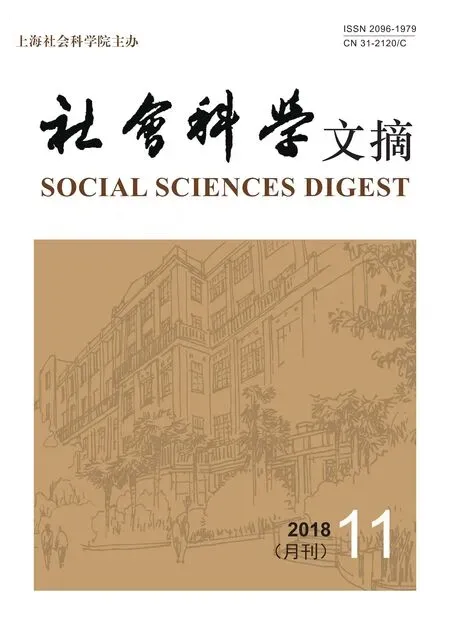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
——从流行语“万元户”看改革开放40年
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更是一种“述说”。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流行语是什么?何以认为其“最重要”?这是谁的“述说”?“述说”了什么?其意义何在?
所谓“流行语”,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某一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语汇”(《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辞学立场上,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形式),更是一种“述说”(行为),即“一种语言生活中,其语言社团集体借助某个表达式的不断高频和广泛的转述而表达出特定时期焦虑、紧张、兴奋、无奈或需求的群体性述说”。
“万元户”:一个语言事件的兴衰
在汉语词汇史上,改革开放40年是新词新语“创造主体”最为多元、词语数量最为丰富、词语形式最为多样的时期。那么,改革开放40年中,这一时代的最典型最重要最深刻的语言流行“事件”,即“流行语”是什么?
毫无疑问,首先自然是“改革开放”这一表达式本身。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空前深刻而又重大的转型,其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不过,这应该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这一“言语社团”“有意使用某一表达式并有计划地加以推广,触发群体性转述,以建构某种社会现实”的一个事件。对于这样一个言语事件,已经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做过论述。
如果就“某人无意中使用了某种表达式,触发了社会的关注和集体性转述,形成流行从而建构出新的社会现实”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中,这一时代“集体述说”的最重要最深刻的流行语言“事件”,即“流行语”又是什么?
真正使得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从内心深处产生重大触动,“强烈有感”的,我们认为应该是“万元户”这一事件。
在1980年前,“万元户”最初不是一个单词,它的出现和“事件化”有着特别的社会条件。
“万元户”在当代汉语中成为流行语事件,最初出自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6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1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做‘万元户’。”
这尽管最初只是一个官方媒体的为追求形象化的词语,一旦出现,却立刻不但成为一个流行全国的词语,而且家喻户晓,几乎成为民间人人聊天必定会时常提及的话题。即使今天百度检索“万元户”,我们依然还能获得4,340,000个网页。根据对于《人民日报》数据库的检索,作为“发财致富”符号的“万元户”,在1980年还是特例,只有短短三四年,到了1984年就迅速到达峰值。仅仅《人民日报》一年使用量就达113词/次,平均每三天就会有1词/次,是前一年的4倍。不过,随后就开始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2001年降到了10词/次以下,而且这时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回顾。
“万元户”语言事件的兴衰与中国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万元户”表达式出现的1980年分别为477.6元和191.2元,如果以1户4口计,分别为每户1910.4元和764元;到了199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577.4元,户均过万;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达到2622.2元,户均也已经过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作为“发财致富”的符号标记,在20世纪80年代末迅速变成年收入“十万元户”;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杨百万”;而到了2000年代则开始使用“亿万富豪”,21世纪10年代,按胡润财富榜资产过亿的有6万多人。昔日万元户今天特困户,“万元户”作为“发财致富”符号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万元户”的兴衰不只是“叙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最具改革开放标志性的“叙述”:这一流行语曾经诱发了极其巨大的社会想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动能,也遗留下巨大的社会问题。
“十字架身份体系”崩裂的标记及其意义
要真正认识“万元户”叙述的价值,就需要从对于“文化”的核心问题的重新考察开始。
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并且以非生物性方式传播与演化的、制约群体的行为与思维方式的信息结构”。在这样一种信息结构中,基本问题就是“我是谁”“从哪来”“到哪里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我是谁”,也就是“我(你/他)的文化身份”的问题。
身份是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身份的划分与流动直接标志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形制和格局。整个40年来最大的变革是什么?有人说是“钱多了”,有人说是“开放了”,等等,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未必准确。我们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身份系统”的彻底变革,因为“人”首先要回答“我是谁”,“我”所有的情景、所有的行动都要根据“我”的身份来决定,是改革开放推动了被禁锢的身份系统的消解。
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身份系统到底是怎么构建的?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身份系统是被紧紧地钉在一个层级化的十字架上,是一种“十字架结构”。之所以称之为“十字架结构”,是因为这一固定国人的身份系统是严格依据横轴、竖轴建构的。
这一身份系统的竖轴,依据政治身份简单地分为“左右”,形成不可逾越的“敌我对立”。从1949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身份系统在政治上就分为两个部分:左派和右派,也就是“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同志”和“敌人”。其中,“我们”包括“工、农、兵”,勉强加上“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同盟军,兵是工农的子弟兵。另一派很简单,是“地富反坏右”,到“文革”开始,又加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还包括“资本家”。即使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也最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依然打上深刻的既定身份烙印。
这一身份系统的横轴,是依据经济身份确定是否“农业户口”,由此形成“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城乡对立”。这一身份标记区分可以直观地分为有无“粮票”,国家向“非农业人口”发放每月定额的“粮票”,保证口粮供应;“农业人口”则不但所有的口粮由自己负责,还必须“缴公粮”,所有的收成在缴纳完“公粮”,留足“种子粮”以后,才可以用作自己的“口粮”,只有遇到大灾荒,才可能获得国家的“返销粮”。“饥饿”几乎是当时所有“农业人口”的主题。要改变这种身份的路径只有两条:一是读书,考大学,考中专;二是参军,争取提干后转业。
就这样,“敌我城乡”构筑的十字架,竖轴是左右对立,两大块身份,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横轴是城乡对立,不是“农业人口”就是“非农业人口”。政治上绝对分成左右两块,经济上绝对分成上下两块。全体国民都被钉在了这一身份的“十字架”上。

这个身份十字架系统里面,就政治地位而言,是“N”字形结构,即依照左上角-左下角-右上角-右下角,从高到低排列;就经济身份而言,则呈“Z”字形序列,即依照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从高到低排列。对于“非农业人口”中“敌人”的最常见惩罚就是把他们个人或者全家“赶到农村去”,如果说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那么,其中的“地主”“富农”则处于整个社会身份系统的最底层。
更重要的是,这一身份都是先天设定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强制性的设计。在改革开放之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确定的身份标记,“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的身份标记决定了一个人在整个社会中的现有地位和未来可能。这是很固化的一个制度设计。身份一旦确定,什么都受它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设定、所能做的事情,就被这个身份系统框进去了。如果父母是工人,本人是学生,那么肯定吃公粮的。读大学也同样如此,地主的孩子、反革命子女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其偶然的机会才能上大学,即使上大学,绝大多数的专业也是不让他们读的。这是由先天的身份设定。
身份认知是自我对于一切行动认知的基本依据,而这身份认知并不是简单的自我设定的过程,更可能是一种制度的内化,而显示出系统性的“主体间性”和“集体无意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就是这个社会的群体性认识的直接表征。
“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是中国1949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个人生活的社会依据,简单地分为“敌我”两大阵营和城乡两大系统,在政治上“敌我”不可混淆,在生活上“城乡”不可混淆。没有这一系统的真正破裂,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展开。
那么,这一“十字架”等级制的身份系统是什么时候发生破裂的?回答:从“万元户”语言事件的出现开始。
首先,这是因为“万元户”第一次超越了同时也就是破坏了这一“十字架”等级制的身份系统的“系统构成原则”。“万元户”的身份很难归于“十字架”中上下左右任何一个方位。理论上讲,农民可以成为万元户,工人也可以成为万元户,其他人群也可以成为万元户。它无所谓“左右城乡”,与现有的所有身份设定原则都不兼容。在它出现之前,落实政策、平反等,都是恢复原来的身份地位,身份系统没变,是个人身份的变化。它的出现意味着既有的身份系统开始垮塌。
与此同时,“万元户”的出现第一次超越了同时也就是破坏了这一“十字架”等级制的身份的“个体生成方式”。身份不再是一种“家庭出身”先天性的继承和“本人成分”永恒性的规定,而是一种可以自主创造的过程。一个人无论原先是什么社会地位,都可以自己做主决定是否构建新的社会身份。
更重要的是,“身份的向上流动”不再是一种“层级式”缓慢爬楼过程。“身份的向上流动”不但是可以自己掌控的,更是可以立刻发生的,甚至可以是立刻“翻天覆地”的。整个身份系统和经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但在原来的身份系统中,全国8亿人民,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年收入不过6000多元;最高的教授一级还不到4000元;最强的技术工人一年不超过1000元。与此同时,由于公私合营遗留的“资本股息”制度已经结束,稿酬制度又刚恢复(每千字一般3到8元)。这样,全国8亿人口的年收入几乎很少能够高于6000元。突然有人能够收入上万,这对于长期得益于城乡分裂的“非农业人口”,固守8级分层最高年收入1000元的“工人阶级”、12级分层最高年收4000元的“知识分子”,24级分层最高年收6000多元的“国家干部”各大群体的刺激都是可想而知的。
原本基本固化的社会结构突然发生崩塌,向上流动的可能几乎在瞬间变成为一个巨大现实,而且这一流动的幅度又是如此巨大,突破了所有人的思维惯性。“万元户”这一身份想象几乎同时与每一个人的自我身份设定和他人身份想象发生了强烈的碰撞。
也就是说,“万元户”带来新的身份系统信息,冲破了所有人对身份系统的想象,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身份流动的可能性;“万元户”真正开始消解城市乡村的对立,也消解了“敌我”的对立;“万元户”构建了“发家致富”的具体样本,个人财富的创造和追求有了确实的标准;同时,“万元户”也预示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甚至从消极意义上说,今天世人普遍只关注到赚钱本身,全社会“一切向钱看”,跟它也不无关系。
印度思想家阿马蒂亚·森曾经指出:身份源于一种想象,“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的一个显著的用途,就是成为‘文明的冲突’这个受人关注的主题的基本分类框架”。其实,依我们看,这种“单一身份”的“显著用途”还可以构成一个文明内部斗争的思想资源。“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以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和背离。群体内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以至于“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由此而论,改革开放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建构了“十字架身份体系”,而“十字架的身份体系”的持续发展,更内化为全体国民的“阶级斗争”思想意识,二者互为因果。进而言之,单一的固化的身份系统与“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同样也互为因果。
出于同样的原因,“万元户”这个概念一旦诞生,经历了无数国民的不断“转述”和“默念”,也就直接推动了当时整个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社会转型,推动了全社会从“个人迷信”向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转型。
从“万元户”到万种身份:“解放”与“继续解放”
时至今日,中国人的身份系统已经极其多元化,依据《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的考察(苏向红,2010),身份形式多达2000多条;而据金志军先生的调查(2017),近年使用的身份形式更是已经超过10000种。在这里,人们日益自觉地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多重性亦即它们具有的不同含义”,身份成为“人类生活丰富性的源泉”。
所以,“万元户”真正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第一流行语。它标记了中国一个当代的、全新的、多元的身份系统构建的开始,宣告了旧有的、十字架式的、层级式的身份系统的垮塌。一种新的“真理”以整个社会几乎猝不及防的方式立刻现实地站立在全国所有人的面前。“思想解放运动”从一种理论口号立刻成为一种全社会可以触摸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话语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
不过,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历史的印迹却不会轻易消失。尽管作为“发财致富”符号标记的“万元户”早已被“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豪”所替代,但是,现代性的身份体系建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在目前的流行语中,“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负二代”“农二代”等提示我们,经济地位的固化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在高房价等因素的影响下,还有日益加重的可能;而“五毛党”“带路党”与“美粉”“米粉”“日杂”之类的流行,“敌我”身份的对立也在似乎重现江湖。沉重的“十字架身份体系”的阴影似乎又开始若隐若现。
“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