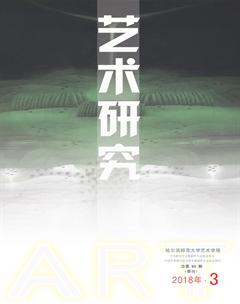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刘嵬
摘 要: 隋唐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建立起多民族、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之间方法交流与合作,并在相互融通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音乐文化发展的繁荣局面,丝绸之路便是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本文从历史背景、歌舞音乐、乐器、宗教音乐等方面对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交流进行论述。
关键词:隋唐 古丝绸之路 中外 音乐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空前的交流,繁荣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稳定局面将音樂文化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外域音乐文化的输入,此时对外来音乐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不但有利于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的蓬勃发展,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与信任。建立起多民族、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之间方法交流与合作,并在相互融通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音乐文化发展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与外来音乐文化的交流,彰显于外来音乐文化的大量输入,其中丝绸之路便是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是一条连接欧亚各国经济与文化的陆上要道,东起长安,西至罗马,作为一条重要的枢纽,将中国与外国联系起来,为多民族、多国家音乐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骞通西域以来不仅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还将西域音乐带入中原,造新声,用于鼓吹乐。从西汉末年,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向中原地区迁移,到西晋时期,迁移来的匈奴,鲜卑等人口近百万,居住关中地区的氏人、羌人五十万,占当时关中人口的一半,天宝初年京兆尹人达三十多万户,贞观的时候不到此数量,但当时长安一地的突厥流民却达到了万户,从上述人口数量的变化,反映出了当时丝路的往来中除管办宫廷间的交流活动外,民间的往来也日益频繁。隋唐时代丝绸之路上传来的外来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北朝以来外来音乐输入中原的现象增多,西域各国音乐在这时十分流行,如琵琶、筚篥等乐器均出自于西域地区。后魏、北周、北齐的皇室乐队也都来自外域,并且此时出现西域地区乐人在宫廷中任职,甚至干涉政治的现象。外来音乐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形成了外来音乐与中国原有音乐之间的融合。
隋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混战局面,统一了中国,但由于隋炀帝的腐败统治,使隋王朝在统治了短短37年后陷入混战,不久后,再一次出现了政权的统一,这就是唐王朝。隋代虽说统治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由于统治阶级对音乐十分重视,此时的音乐文化呈现了繁荣的局面,唐太宗在统治中采取了开明的政策,使唐代社会很快摆脱了唐初的贫困状况,富裕繁荣起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此时,唐朝统治者胸襟开阔、充满自信,允许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并存,使出生卑微的中下层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并允许各种学派的并存,即尊崇儒教,又信奉道教,同时也信奉佛教,形成了儒、道、释并存的状况。唐代疆域辽阔、富国民强,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当时”音乐运河”上歌如海、人如潮、歌舞升平、乐工云集。各地区、各民族的歌舞百花齐放,集英荟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和伟大作品。在当时形成了民间“家家学胡乐”,宫廷音乐以少数民族音乐为主的音乐现象,其中以燕乐为代表的宫廷歌舞大曲即呈现出当时中原与少数民族国家与地区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繁盛景象。在隋唐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歌舞音乐发展到辉煌时代,除本土音乐的自身发展外,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音乐文化经过世代的传播、交流,到隋唐时期成为了远播域外、席卷朝野的新乐。
隋朝虽短短的37年统治,东西南北中的乐舞却完成了第一次大融合,据《隋书·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 ,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1}自隋起文帝初年即制定七部乐,七部乐包括国伎(西凉)、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在七部乐中除清商伎外,其余乐部都是边疆和外国乐舞,隋初国伎即为西凉伎,隋代将其作为多部乐之首,本想把它当作时中原乐舞,可终究不能否认它是西凉系统,是中西乐舞结合的产物,隋初除了七部乐以外,还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音乐,均来自外域(西域音乐有三部),在此时中外音乐交流十分频繁,外来音乐渐渐开始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将七部乐发展为九部乐,增加了康国和疏勒两个乐部(西域音乐增至五部),并将国伎排在了第二位,将清乐放在首位,九部乐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文康伎)。九部乐除清商伎是中原汉族的乐舞以外,其他外来乐舞皆保持了原有的面貌,由于隋代统治时间短暂,人们还没来得及将这些乐舞进行融合改编,很快又陷入战火之中。不久后再次完成的统一的朝代即唐代。
唐代以来国力强盛,西域各国与内地政权为从属关系,边疆向朝廷进奉大量的贡品以维系稳定和融合。各国最具特色的胡乐歌舞表演也在进奉的途中传入中原,随着胡乐的大量传入,其在当时的宫廷歌舞音乐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不同于隋代的原搬照用,创新是唐代乐舞的主要特征,唐代宫廷乐舞呈现出乐有新律、歌有新声、舞有新姿,以包容的姿态接纳一切外来文化,并通过交流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乐舞。唐“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3},后来唐太宗平高昌,收其乐,在九部乐的基础上增至十部乐,十部乐为燕乐、清商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十部乐中除清商伎为中原传统乐舞外,燕乐和西凉伎为中西结合的产物,其余乐部均来自域外(西域音乐增至六部)。不仅仅这些歌舞,还有于阗乐、突厥乐、伊州乐、米国乐等等许多的西域音乐也陆续的传入中原,在唐代音乐中,西域音乐几乎占据了统治的地位。
唐太宗时期改十部乐为坐部伎和立部伎, 坐部伎一般3—12人,堂上表演,用丝竹乐伴奏。有燕乐(《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六部乐舞,以抒情,音乐细腻,并注重个人技巧。立部伎通常60—180人不等,用锣、鼓等乐器伴奏。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八部乐舞,以气势磅礴见长,场面宏伟。《旧唐乐·音乐志》载坐部伎“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3},立部伎“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声,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唯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4}从旧唐书记载来看,坐部伎与立部伎的乐舞音乐之中,坐部伎只有一部是中原音乐,其余的五部都是西域特色的乐舞。立部伎绝大多数的乐舞都是西域风格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唐人对西域乐舞的喜爱,龟兹乐是一种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鼓和舞相配合的乐舞,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魅力,从而能体现出唐代的盛世景象,故受到唐代人喜爱。
开元、天宝年间乐舞中来自西域或西域音乐家创作的乐舞有《六么》、《伊州》、《梁州》、《胡璇》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在进入中原以前首先将边境音乐与当地音乐相融合,再进入中原后与汉族音乐相融合形成新的音乐风格。沈括《梦溪笔谈》载唐天宝十五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燕)乐,这一时期音乐为三乐并存, 其中燕乐为中原与胡乐乐舞相融合的产物。在唐代的乐舞中,舒缓闲雅的中原汉族舞蹈风格很少,更多的是胡乐中雄壮铿锵的音乐风格。中西合璧的音乐现象不单单体现在乐舞中,也不是一種孤立的历史现象,这种融合与唐代幅员辽阔,各民族间的和平共处相关,也有当时多教派的共存,各阶级的共处有关。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除体现在乐舞方面以外,在乐器方面,伴随着西乐东渐的脚步西域乐器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箜篌(凤首箜篌、竖箜篌)、筚篥、阮咸、羯鼓、毛员鼓、腰鼓等相继传入中原,并成为了唐代的重要乐器,丰富了中原音乐文化。在宗教音乐方面,唐代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佛教音乐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形成自己的体系,成为了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儒、道、释等宗教并存的现象,无论何种教派音乐都常常被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隋唐时期的说唱音乐形式“说话”、“变文”即是在宗教传播推广过程中形成的音乐形式。在当时寺院的活动常常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一些特定的宗教节日中,寺院会组织各项活动,如看戏、祈福等,僧人为了传播教义利用民间音乐将晦涩难懂的教义进行加工变化,寺院中的节日表演成为了胡乐传播的重要途径。同时,印度地区的拼音字母经由沈约等人结合汉语声调和天竺字母的特点创立了汉语拼音体系,对唐代以后中国歌唱技术和作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唐代由于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当时佛教达到了全盛时期,唐代宫廷音乐中便采用了大量佛曲。唐歌曲大曲中的一部分,也是宫廷燕乐的一种形式——法曲,又名法乐,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传》中,因用于佛教法会而得名,唐玄宗李隆基作《霓裳羽衣曲》即是一首著名的法曲。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使当时音乐发展达到了鼎盛时代,同时对中国后世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丝绸之路上中外的音乐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注释:
{1}{2}{3}{4}刘蓝.二十五史音乐志(第二卷)[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