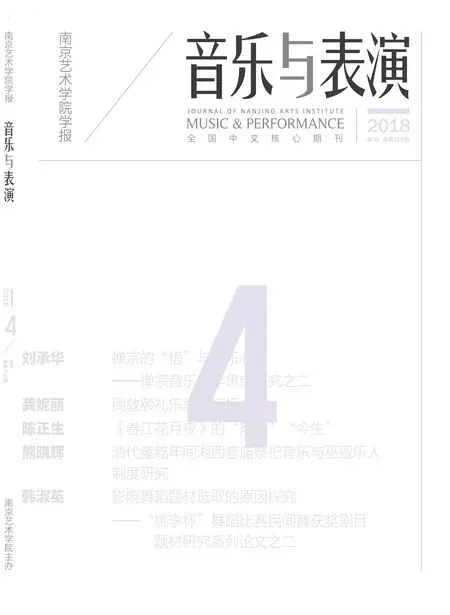当代中国流行乐坛“旧曲新唱”的“创腔”问题探讨①
姚毅萱(南京艺术学院 流行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引 言
纵观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流行音乐发展历史,“旧曲新唱”(或称翻唱)现象如影相随,逐渐成为一种独特且颇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各类音乐真人秀节目热播,越来越多的“旧曲(或称老歌)”被重新演绎。“旧曲新唱”中,就有一种令人颇感新意的创新性。一些较成功的旧曲新唱作品,从音乐(包括旋律、节奏、曲式结构、音乐风格、情感内涵等)方面或演唱表现技法(音色、速度、歌唱技术技巧、演唱风格、情感意境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由于其包含一定的能为受众广泛接受的再度创造,相关审美选择、思想观念、表情观念、表情技法乃至体现的音乐审美时代思潮具有相应的进步性,故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流行音乐现象。其中,关于音乐形态或云歌唱“唱腔”的创新——“创腔”,可谓是上述“翻唱”之再创造的基础部分,对于流行音乐演唱表演研究至关重要。
“创腔”概念源自宋元戏曲创作实践。在此后数百年的戏曲、曲艺创作中,凡针对曲调与字调规律、节奏与字调规律、音色变化规律以及“依字行腔”等方面的阐述,都可以归纳在“创腔”这个范畴当中。从我国古代第一部声乐论著《唱论》到《南词引正》《曲律》《中原音韵》《乐府传声》以及近现代音乐理论家的研究,充分表明“创腔”技法是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戏曲音乐创作及演唱的重要手段。
“传统戏曲音乐中,其一度创作(创腔编曲)和二度创作(演唱及演奏)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主要是由于演唱中即兴因素的大量存在,演唱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唱腔在变化过程中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传统戏曲音乐中,演唱与创腔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1]这与流行音乐自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发展,与流行音乐制作人和演唱者在对一些“旧曲”进行重新演绎的情况是一致的。在重新演绎过程中往往也运用了改变“旧曲”的旋律、结构、情绪、音色等各种方法。而在这些方法当中,本质上看就是大量运用了我国古已有之的戏曲创腔手法。有意思的是,“创腔时必须按戏曲固有的艺术规律办事,而不能抛开演员的特长而我行我素地设计。创腔应该与演员协作,完成创腔至演唱之间的转换任务,这样才能创造出活泼、动听、演员驾驭自如的新腔,才能广为流传。”[2]这与近年来音乐真人秀节目中的“旧曲新唱”呈现出的音乐创作规律是一致的。大家在实践过程中,也越来越注重音乐人和演唱者的共同讨论、商议,进行具体创腔操作。特别是“翻唱”更是建立在舞台演唱者个人语言特征和呼吸力度、习惯等基础上,演唱者完成的旋律、节奏、音色等要素,也需要与音乐作品意境等有效结合。正是这样的审美要求,才让越来越多的表演者下意识地从各方面挖掘建立自己的表演特点即唱腔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视为我国流行乐坛编曲、演唱中的“创腔”。
关注流行音乐“创腔”问题的学者尚不多见。郭鹏《蕴藏在“细节”中的流行机制—翻唱歌曲文化新解》[3]、雷美琴《掀开“翻唱”歌曲的面纱—流行歌坛“翻唱”歌曲的审美品评》[4]、龚浩与王飞《我国旧曲新唱的创新手法》[5]、潘勋《浅议“老歌新唱”唱经典歌曲》[6]、刘爽莹《浅谈流行音乐的翻唱现象》[7]、何世剑与陈伟琳《民谣“南山南”翻唱流行的文化诠释》[8]、霍敬《流行歌曲中的翻唱现象观察》[9]、张伟《打破翻唱 重归原创—从“中国好歌曲”看流行歌曲创作的多元》[10]、黄彦与刘璐《关于电视歌唱竞技类节目中“老歌新唱”现象的思考》[11]、王思琦《“新瓶装旧酒” 还是“杨柳结桂枝”—对歌坛翻唱现象的美学思考》[12]等论文,针对“旧曲新唱”中改编音乐形态、文化意义、市场机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针对流行歌曲演唱者在“旧曲新唱”时,如何形成自己的演唱个性、具体操作方法有哪些,以及针对翻唱歌曲如何运用“创腔”理论等问题,则是目前亟待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思考的大问题。
一、几种常见的“创腔”方法归纳
(一)根据旋律走向的“创腔”
根据旋律走向进行旧旋律的翻新,就是戏曲音乐创作中的“相顺”。于会泳说:“在同一曲子中,(腔词)双方均保持其自行规律的完美,而又相互适应,从而步调一致地共同完成对于统一艺术内容的表现任务。”[13]49从歌曲的旋律走向来说,“相顺”就是体现出歌词的字调、语调与旋律的升降曲直结合有助于美化唱腔的运动状态。在“旧曲新唱”的“创腔”过程中,有时旋律和四声并不能完全统一,但不能改变旋律高度时,用装饰型润腔手法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了。从声调上看,它的音响要素即音高、音势、音长主要集中于所读字的某一音上。字的声调节奏和音乐节奏相比,在总体上所占有的时值是极短暂的,而音乐上各种装饰音却具有相似的短暂节奏时值特点,这样就给运用各种装饰音来校正字调,平衡和调节腔词关系成为可能,它可以在保持总的旋律线的流畅中产生幅小时短的曲折以符合字的四声趋势。[14]以袁娅维翻唱的《阿楚姑娘》为例,相较于原唱,在许多地方加了装饰型润腔之后,整首歌曲的字调和旋律的贴合程度更高,也使歌曲更具婉转悠长的韵味。“阿楚姑娘,乡村里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其中“姑”是阴平字,原唱用的润腔是5-3两个音,而袁娅维翻唱则用了3-5-3三个音润腔,从字调效果来看,原唱5-3从高到低唱“姑”更有去声之嫌,而翻唱用了3作铺垫,使字调更具阴平字特征,也更显柔和,又不乏变化流畅。
(二)根据节奏强弱的“创腔”
节拍在音乐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旧曲新唱中节拍的变化可以带来显著的创新意味,因而受到大家的重视。有学者曾将节拍和律动结合起来进行诠释:“律动”是指“音乐心理上的时位感”,也即“一个时间单位中开始那一瞬与其之后持续部分之间在心理上的强弱差异感”;“它是心理上的一个‘力点’和‘搏动感’,而正是这种‘力点’和‘搏动感’所造成的时感反应,构成了我们可称之为‘律动’的心理感觉”;“律动这种时位感可以是匀整的,也可以是不匀整的”,这样,上述“节拍”就成了“律动”的一种“外化形式”—“功能性均分律动”,即“强弱有序”(功能性)、单位时值匀整的律动形式。[15]“唱腔节奏的强弱位置变化如果能在保持自行规律的同时与唱词轻重变化的步调相适应,便构成相顺关系,……如果不相适应,便成为相背关系。”[13]99借鉴以上律动概念,可以标识流行歌曲翻唱中由于节奏和强弱对位变化而产生不同效果的做法。例如,歌曲《野子》苏运莹和沙宝亮的创腔方式不同点在于:两个版本的节奏强弱安排有区别。“一直往大风的方向走过去”句中,“走过去”三个字,苏运莹版本采用的是弱起和正拍节奏,而沙宝亮作了三个正拍处理,由于节奏稍有不同,演唱上的侧重点也发生改变。苏版侧重强调“过”字,因此“走”字的韵母并未完全展开,采用了半闭口唱法,强调“走”的急促感;而沙版则强调了“走”,把ou母音的字头字腹字尾充分展开完成,强调“走”的从容感。如谱例1:
谱例1.

(三)根据音乐语态进行“创腔”
杜亚雄提出过“句子是表达完整思想的具有一定语法特征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句子或句中的某个片段在语音上的抑扬顿挫叫语调。语调包括句调、节拍群和逻辑重音等方面。句调和旋律线条关系密切,节拍群和逻辑重音则和乐句中乐逗的划分和节奏形态有关”。[16]以周晓鸥在《歌手》节目中翻唱的《爱不爱我》为例,在“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句中,“借口”处,停顿了片刻,之后的乐句又重新进拍子开始。这种处理方式让听众有强烈的期待感,特别是“口”字落在六级和弦上,具有下属和主和弦双重功能。因此,在乐句情绪衔接效果上也更贴切。周晓鸥的重新演绎,使节奏更加自由、拖拍和抢拍似乎更随心所欲,完全打破了原唱版本的工整规矩。也正是因为这种“打破”,让这首充满力量的摇滚作品多了些柔情和从容。
(四)根据方言特点进行“创腔”
歌曲演唱中会因为情绪和意义的需要,在声韵上特地做出与普通话的区别,例如把有些声母的卷舌音唱成平舌音,鼻韵母故意拉长归韵的时间或者将方言运用到个别乐句或字音当中等。歌曲《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儿,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主)”一段,其歌词中的“睛”“精”“举”声母是J,而“去”和“举”韵母是u,其中把“主”字变化为“举”,一是为了歌词声母一致和韵母一致的需要,其次是为了突出俏皮戏谑感,让形象更生动。
谱例2.

另外,在“旧曲新唱”中,许多歌者似乎故意“吐字不清”,以达到对歌曲重新演绎和“标记”的目的。一些流行歌手,特别是有海外生活学习经历的华语地区歌手,在语言吐字方面呈现出与内地成长起来的歌手有很大不同。从周杰伦、陶喆、王力宏、林俊杰等近年来几位流行歌坛代表人物来看,他们形成的吐字特征不是常规的普通话形态,他们在处理声母和韵母时会做特殊的摩擦或变形,这显然受到了欧美流行演唱发声方法及律动特点影响,也和地域方言特点有关。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不是“创腔”理论在当下流行音乐和演唱中的延伸体现呢?萧敬腾在翻唱《你是我最心爱的姑娘》时,将“而我的心就像那翻涌的浪花,永远陪着你哪怕是海角天涯”,其中“涯”Ya变形为Yai。“涯”在普通话发音中并没有这个读音,但许多台湾歌手在这个字的处理上几乎都是采取这种“变形”,形成了地域方言在音乐形态上的特殊表达。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不能绝对化,语言本来就是人类沟通的工具之一,只要语境符合,能让人听懂,就应该容纳华语流行歌曲中语言的多样化和变化性。
(五)根据音色情绪进行“创腔”
在音色变化上,润腔内在的音质变化是极为丰富的。如运用滑、擞、顺、假声等方法而产生的特殊音响效果是构成润腔内在音色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对这种音质的变化,又取决于在唱奏中由不同的发音条件与动作手法对它的支配。如在汉语歌唱中,由字的某一语音基础 (条件)而带来或影响到对发音器官或手法动作在音色上的某种区别。因此,在唱奏中,汉语字(音节)的语音变化过程同时也就是造成一个润腔在音色上的变化过程。林忆莲在《我最亲爱的》翻唱中,“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林发挥了个人气声演唱的特质,在“世界”采用先出气再出声的方式,使声音呈现出迷离的虚声音色,但紧接着“管”字立即变成了实声演唱,在情绪上有推进作用。在林的演唱中,虚实结合总能表现得恰到好处,在充分发挥个人音色特质的基础上,将歌曲情绪意境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几种常见的不当“创腔”方法
(一)旋律与字调“相背”
“相背”概念,于会泳说:“在统一内容范围内,腔词双方的自行规律互相妨害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必有一方的自行规律由于受另一方影响而不完美,因而可能造成腔害于词或词害于腔,对统一内容不利的结果。”[13]8同样,从流行歌曲的旋律走向来看,相背就是歌词的字调、语调与旋律的升降曲直结合破坏了唱腔的美感运动轨迹。以歌曲《爱的主打歌》为例,“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主打歌”三个字分别是上声、上声和阴平,当两个上声相遇第一个要变为阳平,而旋律安排则是前两个字音高和调值完全一样,加上逻辑重音自然放在“主”字上面,这样就造成了词意理解的偏差。当语调和旋律反向而行时,一般都是相背的。由于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决定了流行歌曲的创作量大,更新换代速度快的特点,在巨大的音乐市场当中不可能做到每首作品在字调和旋律的关系上精雕细琢,因此网络上也整理了许多关于歌词与旋律相背的滑稽实例。
谱例3.

(二)节奏与字调“相背”
在前面已经说到了“唱腔节奏的强弱位置变化如果能在保持自行规律的同时与唱词轻重变化的步调相适应,便构成相顺关系,…….如果不相适应,便成为相背关系。”[13]99歌曲《祝福》中“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如果歌唱者将“尽在”唱成前附点,效果则不如唱成八平均拍来得好。这正如沈洽在《腔词关系研究》读解(续二)中分析“拆跨”“拆破”是指由于乐逗(或乐型)与词逗的不适当配置而使相关词逗原来合理的逻辑结构遭到破坏、腔词关系上出现“相背”、听觉上出现“破句”、词义上令人“费解”或“误解”等情况。区别在于:“拆跨”只是从唱腔方面(也即乐逗或乐型方面)来说这件事,“拆跨”一词也只是用来指称“乐逗”和“乐型”;而“拆破”是从唱词方面(也即词逗方面)来说这件事,“拆破”一词也只是用来指称“词逗”。[17]这两个观点都是沈洽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期提出的,虽然相隔几十年,但从逻辑关系上来看是延伸和发展的关系。
谱例4.

(三)语态与乐句“相背”
在“旧曲新唱”实践中,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例如违背了乐句与语态的和谐关系、句调和旋律线条背道而驰,又或者是节拍群和逻辑重音与乐句中乐逗的划分和节奏形态步调不一。从听觉效果来说,这样的“相背”让听者无法准确获得歌者的情绪状态甚至产生南辕北辙的“误会”。用沈洽“拆跨”概念来看,“拆跨”是从唱腔方面(也即乐逗或乐型方面)来说这件事,“拆跨”一词也只是用来指称“乐逗”和“乐型”。某一场选秀中有歌手翻唱了经典曲目《梦醒时分》,将原曲2/4拍节奏改为3/8拍,将抒情风格改为摇滚风格,本来这种改编创意无可厚非,可由于改编之后节拍与歌词的排列方式破坏了句意的完整性,让听者产生“歧义”。“早知道伤心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在副歌乐段中,由于呼吸换字位置错位,导致将“早”字吃掉,引起意思变化;之后“一点点”的安排是第一个“点”放在弱拍,紧接着强拍安放第二个“点”字,违背了语音和语义的表达规律。“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歌手换气点安排并没考虑整个句意,而是在“人”“永”之后换了两口气,将“永”和“远”割裂开,从听觉效果和听觉心理来说,整个副歌乐段匆忙不堪,让听者产生一种慌乱的心理感受。
(四)语言与意境“相背”
前面说到在“旧曲新唱”中,许多歌者似乎故意“吐字不清”,以达到对歌曲重新演绎和“标记”的目的。但在实践中,许多歌手想把“吐字不清”当成是“个性”,而并没有把“吐字不清”处理得“恰当合理”,甚至成了“怪腔怪调”,产生的效果很容易造成尴尬。某一位知名歌手重新演绎《慢慢》时,针对很多字的韵母和声母都做了较大程度的改编处理,歌词如下:“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真爱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忍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忍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其中“疼”声母由T变为C的摩擦音;而“生”“成”这些eng母音归韵变化为跳过字腹直接到字尾的方式;“独”的u母音变化为ü;“慢”字an母音变为a母音;“点”字ian韵母直接省略成in;“泪”“飞”的ei母音唱成i母音;“爱”ai母音变形为“ei”。他的这种所谓“创新”就是将汉语普通话声韵特征做了颠覆性改编的实例,尽管实现了其“个性”,但破坏了字义。
(五)音色与风格“相背”
在音色变化上,润腔内在的音质变化是极为丰富的。如运用滑、擞、顺、假声等方法而产生的特殊音响效果是构成润腔内在音色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对这种音质的变化,又取决于在唱奏中由不同的发音条件与动作手法对它的支配。在某个歌唱真人秀节目中,一位知名歌手演唱了《爱情电影》,除了将歌曲改编为二声部和音之外,歌曲改编后情绪风格基调基本延续了原作的面貌。主歌部分歌手采用的气息位置和音色还能理解为本色真实的状态,进入到副歌后,随着音高逐渐爬升,歌手演唱的气息位置和音色空间感也越来越向上升,形成喉头越来越高,气息越来越憋,音色越来越紧的效果。“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入戏,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到落幕不会离去。”这一乐句在听觉上产生字音的挤压感,给听者心理上也造成一种压迫紧张和不安感。另外在许多选秀歌手的翻唱中也出现过许多音色与音乐风格情绪不吻合的现象,例如对《春天里》《吻别》《梦醒时分》《往事随风》等经典曲目翻唱。歌手初衷是希望把某一音色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从而达到让人耳目一新的目的。可现实是,如果是脱离音乐风格本体的“创新”,不仅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而且会让听者焦躁不安。
三、旧曲新唱时的“创腔”原则
(一)时代性
随着时代变化,对声音、语言以及非声音因素方面的审美认知也不断在变化。随着国际化趋势日益显现,对外来语言和唱腔的借鉴也不可避免,或者说只有吸取更多文化的养分,为己所用,才能让演唱更具技术性、艺术性和独特性。正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艺术观念的演变,音乐表演观念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表演观念、综合表演观念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相互借鉴、相互转化。”[18]例如福音歌的演唱技巧、约德尔演唱技巧、印度歌曲颤音技巧,以及随着时代变迁审美演进的过程中显现出的其他各类技巧。正如前面举例到关于邓丽君的声腔特点引起的巨大反响,专门提到时代背景因素,反观几十年后的歌手们演唱,这种邓氏情歌演唱方式只适合缅怀而无法再成为主流。20世纪80年代的歌唱中,对声韵母的吐字要求和对逻辑重音、结构重音的认知也和当下大不相同,它们无关好坏,只是时代变迁的必然产物。这段话用在当代华语流行歌曲创腔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二)地域性
汉语言丰富程度从主要分类到细小分支达到数十种之多,每一种语言的音色、声调、音高、时值感、力度感都与音乐的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影响着当地音乐旋律和歌唱风格特点。这些研究在民族音乐学当中已经取得丰厚的理论果实。其实在流行歌曲演唱中也能寻找到这些踪迹,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一些变异,或者说是隐藏在流行音乐的外在形态下,需要研究者把这层外衣解开才能看到其中的运行特征和规律。声韵因素明显涉及到演唱时的声音音色表现,它们与口腔发音的形状、如喉舌齿牙等部位直接相关。一般北方音乐旋律感较强、时值较长、响度较强,从歌唱方式看,发音部位靠上,音色嘹亮高亢。而南方音乐旋律一贯比较平稳柔和,时值较短,响度也弱,歌唱发音时舌根音运用较多,声音靠下。南北音乐地域性差异对旧曲新唱时的创作,包括节奏型、律动感、力度感以及整体结构等,也都具有很大影响。
(三)相对性
在近些年真人秀歌唱节目中,许多老歌新唱的新就是体现在音乐重新编排,包括速度、节奏型、配器方式等,演唱者的演唱也要依据这些方面的编排,重新安排气口、力度重音甚至行腔方式。因为作曲者除了一般地受到调式、音阶、节拍、节奏约束以及考虑到和声、配器等之外,其他一切音乐元素几乎都可以按照作曲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去改写;而唱腔设计则除了要考虑到音阶、调式、节拍、旋法等一般音乐逻辑的制约外,还都暗地受着某种“程式”规律的制约。正如有些戏曲创腔实践者针对“字正腔圆”的相对性问题这样说道:“唱……常常因为音律的关系,字音可能不会正确,这还是可以的,刻板讲究咬字必然要影响音律,结果变成字正腔不圆了。”[19]另外“唱腔不怕字倒,单怕味倒,能做到字倒味不倒比字虽正而味却倒了要好得多,因为唱腔毕竟是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的。”[20]在“旧曲新唱”中这样的相对性很常见,虽然不仅表现在“字正腔圆”方面,还要更多体现在音乐本体改变方面。歌曲《甜蜜蜜》原版风格甜美,唱腔柔和,节奏稳定;而改编成R&B风格之后,吐字行腔也要迎合R&B节奏特点,重音力度位置以及律动方式也随之改变;摇滚风格《甜蜜蜜》除了改变配器之外,连和声铺设都做了改变,大量采用非常规和非协和的功能和弦,并运用了摇滚乐惯用的节奏音型表现模式,颠覆了对传统和声的听觉审美。
(四)思想性
近些年来,“旧曲新唱”在中国流行乐坛可谓方兴未艾。但总结其中的良莠不齐的现象,即可发现,改编后歌曲节奏型、律动型,音色、语言都可能做到颠覆性的改变,但其中优秀作品屈指可数,改编效果不理想的作品倒是不少。本文第一和第二部分通过对“旧曲新唱”的正反例子比较,也是为了说明针对以上几部分改编创新一定要建立在艺术创作的思想性基础之上。有学者对21世纪翻唱特征作出以下概括:“将翻唱本身作为一项专业技艺,以对原作的拓展、超越甚至结构程度为准绳,旨在实现美学层面的大胆突破。翻唱歌曲不仅是一种特定的怀旧模式,也是精巧的装饰工艺和流行制造有意识的操作性策略。”[3]但关于当下翻唱盛行的现象,也有学者提出了以下分析及担忧:“以零碎细节的操弄赏玩与后现代式的引用拼贴僭越了系统化的艺术创造与构思,造成了原创生产力的衰竭、作品的匮乏以及音乐发展的阻塞。这正是为什么当今翻唱歌曲水平达到如此之高,而原创音乐作品从数量到质量再到势头,其成就却远不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因。它利用与歌曲主旨无关的各种前卫技巧进行外部包装,颠覆了原曲形式和内容的对应关系及稳定性,以所谓审美的名义,放逐了情感表达与心灵沟通,由此导致了传统象征体系和表征逻辑的坍塌与崩溃。这里,一种变态的听觉形态学昭然若揭:歪唱盛行;曲解、误读、解构、反讽泛滥;意义被磨平,以换取感官的惊喜与愉悦;音乐彰显其作为声音快感之科学的时代意义。”[3]作者尖锐批评的,无疑是针对旧曲新唱过程中由于缺乏思想性而造成的种种“歪唱”现象。
结 语
“旧曲新唱”中的“创腔”方法既采用了传统民族演唱精华部分,又与时代进程中的变化因素息息相关,作为当代歌者如果能牢牢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创腔”理念,就能在演唱实践中达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效果。这一研究首先有助于发掘独特个性的声腔形式。众所周知,忽视语言个性的音乐表演灾难并不是今天提出的,在九十年代针对民族唱法“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争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任何一种歌唱艺术在进入单一化、模式化的怪圈之后,艺术生命和感染力必将大打折扣。其次,如何做到利于教学双方更有效地交流。如果教学双方都理解了腔词关系的重要性,那在教学交流过程中自然更便捷明了。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语言特点以及存在的语音问题,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学生也可根据教师的审美操作,结合自身语言和运动特征建立独属自己的呼吸方式和肌肉运动形态,达到建立独特的力度感、律动感和色彩感,从根本上提升乐感。再者,要利于流行音乐演唱语言研究。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对腔的发展要求,因此才能为我们留下丰富的声腔品种。然而声腔的发展过程始终没有离开对字的辩证思考,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无论音乐风格如何发展,声腔艺术的基本规律也不会变,我们只有努力学习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结合当下时代审美思想,才能创造性地迸发出更多新鲜实用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