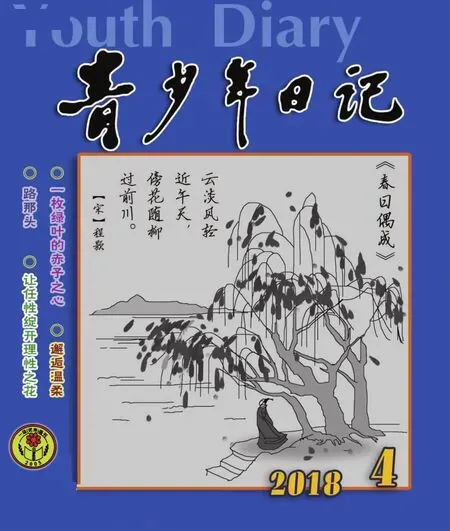阅读伴我成长
□陈昕如
3月4日 晴
婴儿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老人去世时亲友为他发出的最后哀鸣,都引我好奇,也让我迷惘。我参不透生是为何,死又为何。
让我对“死亡”有点懵懂意识的,是余华老师写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
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忍不住将自己代入,成为小小的孙光林。这般,在感受年少的冤屈,无效的反抗和短暂的温暖之后,我目睹了祖父孙有元拖拉多日后卑微而凄凉的离去,目睹了父亲孙广才喝醉酒后掉下粪坑的龌蹉死态,目睹了好朋友苏宇脑血管破裂后温柔而安静的离开……
我甚至还目睹了弟弟孙光明在大河里胡乱扑腾之后的渐渐沉下。瞧,我在观察:“活人是不能直视太阳的,但弟弟做到了。他的眼睛大大地瞪着太阳,眼中尽是灰暗混沌而无光彩,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瞪着太阳了。”听,我在品味:“人死了,并不是走出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孙光林,不,我品味完以上,竟直接想起了太爷爷。
记忆中的那个清晨,小小的我抬头望着睡着的太爷爷,不哭,也不闹,更没笑,只睁大眼睛,一动不动。我以为太爷爷只是累了,想睡得更久一点。睡在他自己的大床上,本就很好,我不知那些大人为何要手忙脚乱地把他挪到客厅。还睡进那么小的箱子里。还在上面加了个透明的玻璃盖子。我当然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头戴白布,还放声悲鸣。他们如果和我一样乖,只站在客厅里耐心等待,或许太爷爷马上就醒来了。
除此,我对太爷爷的唯一记忆,便是那日在山上理发的场景:太爷爷半躺在太师椅上,白白的泡沫围了他半脸,淡黄的阳光照得它们闪闪发亮。隔着师傅替他裹好的白围裙,我百无聊赖地挠他的手心。他动一下,我就笑一声。他又动了一下,我又笑了一声。后来的他似乎想握紧我的小手,阻止我的捣乱,但是又没能。
下晚,家里就传说太爷爷面色红润,却是不太能讲话的消息。此刻想来,那些闪亮的白泡沫,那只想握紧却又没能握紧的太爷爷的手,似乎都在昭示,当时,太爷爷正慢慢走出我的生命。因为没几天,太爷爷也永远地走出了他自己的时间。
“将死者埋葬以后,死者便永远躺在那里,而生者继续走动。他一旦脱离时间便固定下来,我们则在时间的推移下继续前行。”
读到此处,耳畔又响起太爷爷被火化的前一刻,亲人们发出的那声声抑扬顿挫的哀鸣。这些哀鸣声,渐渐和孙光林母亲悲痛欲绝的脸重叠在一起。我看到走出时间的弟弟,不,孙光林的弟弟,水淋淋地躺在家门口的泥地上……不觉泪湿眼眶。
死亡的意味,我好像终于懂得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