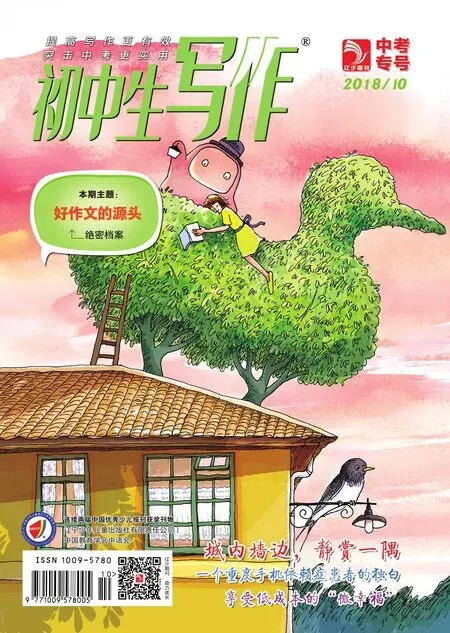坐火车
◎湖北 杨 健
一直喜欢铁路,当然还有火车。
小时候,喜欢和小朋友在铁道口玩,因为经常可以看到蒸汽机车。当道口的警示喇叭开始聒噪,路人的脚步变得匆匆,我们一群小孩儿就兴奋了,马上整齐地在铁道边自动列成一条直线,小脑袋齐齐地转向一侧。很快,听见了“呜——呜——”的汽笛声,然后便能看到白汽从高大的烟囱里升腾出来、斜着向后拖出长长的“彗尾”。黑黢黢的机车头像巨象一般临近,步伐沉稳,仪态端庄,正面的红色五角星也向我们昭示着不可阻挡的力量。它越来越近,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红亮的大车轮上挂着的白色连杆,有节奏地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合着铁轨的哐当哐当,驱动着这庞然大物从我们身边一轰而过。这画面,于儿时的我,就是最初的有关韵律的陶冶。后来,在许多老西部电影的经典桥段里,我又无数次地回味过这样的韵律。
我也曾不止一次地登上过它,让这个会演奏交响乐的大家伙,慢慢地带我去一些当时认为很远的地方。每一次上车后,我都会直接冲向车头的方向,直至在驾驶室的门外,停下来,怯生生地立着,看里面的人和事。我喜欢看司机开火车,羡慕他坐得笔直与专注、神力与威风,想象着自己也和他一样,时不时抬起手,潇洒地拉响汽笛。我喜欢看穿着帆布工作服、戴着蓝灰色军帽的司炉,用力地挥动大铁铲,不停地往炉门里送进泛着银光的大煤块。煤灰和着汗水,还有被呛出的眼泪,在他脸上慢慢成泥。我还执迷于欣赏车厢间绞合在一起的构件,被千钧的力量拉扯,还能严密地运转,也爱盯着脚下飞一般退后的枕木石块,还有清晰着模糊、又模糊着清晰的两条平行线出神。这看不出究竟是动着还是没动的平行线,似乎就是我哲学意识的最初启蒙。
我长大了,蒸汽机车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它停在废弃的铁路上,变成了文艺青年拍照的背景;有的还钻进地下,变成了地铁站里的巨型摆件。我不伤怀,也不惆怅,毕竟铁路还在,火车还在。虽然早就全部电气化,“火车”再也看不见明火和煤烟,但它和铁轨的合奏,还是一样动听;它在瞬间造成的时空变幻,还是让人着迷。
现在,我喜欢坐的火车,是被许多人瞧不上,甚至有些嫌弃的“绿皮车”。因为它的落伍、它的不合时宜,铁路干线上早就看不见它的身影了,只有在支线上的小站之间,还能看见它在恍如隔世的人间奔跑。小站人少、随意,候车的时候,可以看见远方的列车拉着漂亮的弧线,从山谷间缓缓向你靠近。车厢简陋、亲切,敞开的窗子,随时随地掠进清爽的空气和自然的光影。被都市人边缘的绿皮车,仍然是偏僻小镇的百姓们重要的交通工具。背竹篓穿草鞋去赶集的老汉、提着各色大塑料桶去采蘑菇蓝莓的大妈、眼里耀着兴奋光芒的淘金者、参加邻镇喜宴的老老小小、去自然保护区做志愿者的大学生……这些永远不会在都市的电梯间里邂逅的人,突然就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和你这样的近,又是这样的亲。这是一种怎样的穿越?头顶的电风扇呼呼转,吹拂着这些劳动者憨实的笑脸。轻轻晃动的车厢,仿佛在讲述着一个个平淡而又传奇的故事。他们的故事,真是说也说不完。
现在坐得最多的火车,当然还是动车和高铁,如果它们也算火车的话。高铁真快,小时候觉得很远的地方,现在一会儿就到了。只是曾经喜欢发呆地看铁轨,因为车窗密封,伸不出头而看不到,也看不清了,它似乎在推进器的加速再加速中,进入了另一个次元,消失在时间长河里。所以,虽然坐着舒适,总有很不过瘾的感觉,就像在坐飞机上,除了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对过程的记忆只有一片茫然。
中国的铁路越修越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我很庆幸自己经历了完整的火车换代过程,体验到不同年代火车独有的魅力。当然,儿时的崇拜之物,是会扎根在一个人心底的。直到现在,看到一处废弃的铁轨,我还是习惯沿着它散散步,想象它会通向哪里。有时也会俯下身子,碰一碰锈蚀的大螺钉,回忆着它往昔的繁忙与荣光,也重温一下儿时那些在铁道边无所事事的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