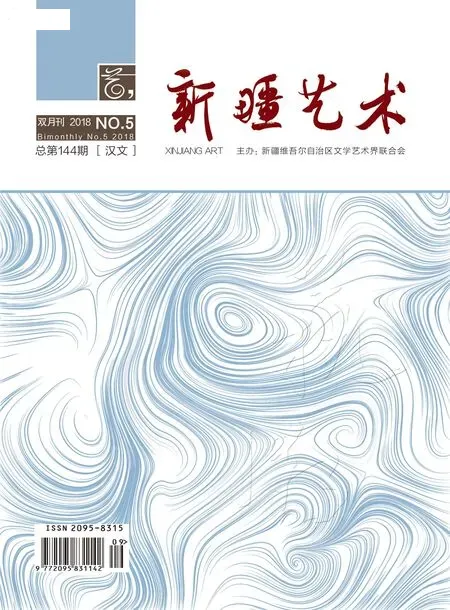中外合作纪录片话语策略研究
□ 张贻苒

中韩合作纪录片《大道中国》海报
自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以来,各纪录频道和传媒公司近几年来都在致力于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其中联合摄制是国际化道路的一种主要方式,我国陆续和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合作过不少自然、历史、科技类纪录片,但社会现实类题材纪录片较少。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大道中国》①分别为中、美、中韩合作的社会现实类题材纪录片,是该类题材在国内外反响较大的代表作品。
一、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与“同一论”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而以合作方式进入国际纪录片主流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一种重要方式。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通过纪录片以更好更深入地讲述中国故事是实现形象建构和国际认同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纪录片的话语策略尤为关键。笔者认为,“话语”是传播双方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话语策略的分析可以参照肯尼斯.伯克“动机修辞学”中的“同一论”。伯克认为,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你只有跟另外一个人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手势,具有同样的音调和语序,使用同样的意念、态度和观点,只有把你的方式与他的‘同一’起来,你才会使他接受劝说”②。因此,借用修辞“同一论”,有效解读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中采用的话语策略,可以映射出制作/传播主体对信息的表述、隐含的动机及价值观的呈现,从而为跨文化传播活动提供反思。
在“同一论”中,伯克提出了三种方式来获得认同,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与“误同”。“同情认同”强调的是产生感情上或心理上的共鸣,即传播者让受众通过相似的感受、情感、体验对自己产生认同,以达到劝说的目的;“对立认同”则是通过确立传受双方共同的对立面而产生认同,类似于“敌人的敌人可以做朋友”,是在分裂中求共识;“误同”,有的翻译为“虚假认同”,与前两者的有意认同不一样,这种认同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伯克以汽车为例,指出开车的人很容易错误地将机械的能力视作自己的能力。
下面以《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大道中国》为例,从修辞“同一论”的角度分析其话语策略的运用和问题。
二、“同情认同”
对于“同情认同”的修辞,伯克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政客亲小孩;二是他乡遇故知。如政客通过亲吻小孩得以获得小孩父母的欢心,从而有利于父母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其实这方式广泛存在于带有劝说或是形象建构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力图通过寻找带有共同情感寄托的符号而寻求彼此的联系,进而产生认同感。
(一)共同情感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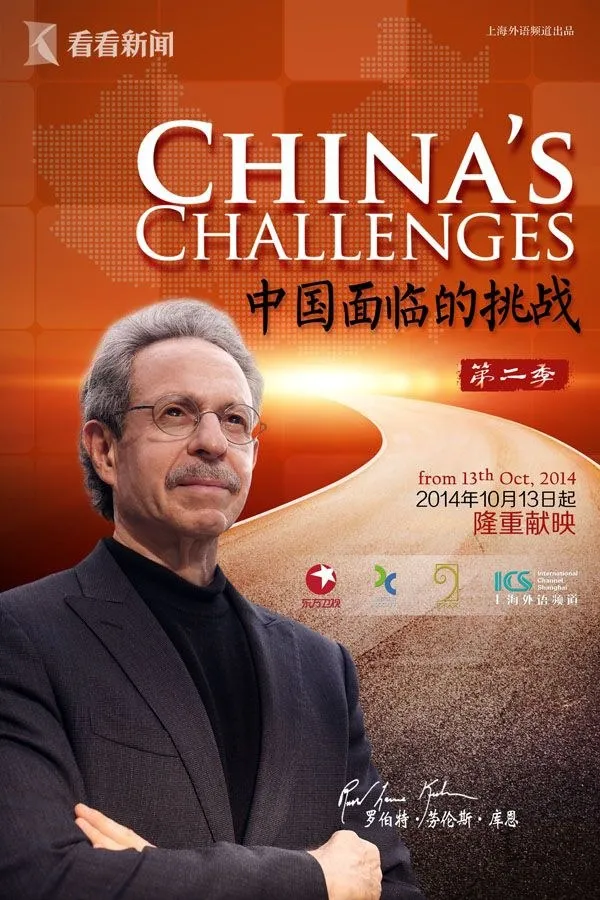
中美合作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
“同情认同”的基本修辞手法在于借助共同的符号让传受双方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大道中国》就多处使用“同情认同”的修辞。在《文化软实力》一集中运用了一些对于国内观众和国外观众同时熟悉的情感符号,如中外知名的郎朗、苏富比拍卖行的中国古董,以让异质文化的观众产生“同情认同”。在以往的跨文化交往研究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确立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属于含蓄、隐晦、间接的高语境文化,而欧美国家的低语境文化相对更加直接和坦率。诸多学者也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文化向西方输出时也提出要根据语境的不同,注意交流策略和互相尊重。“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亚非欧大陆,目前我国纪录片覆盖的主要地区包括西方国家和受西方文化、语言等影响的前殖民地区,在交往交流中必定存在语境的隔阂。这也是上世纪末我国带有外宣性质的纪录片由于不讲究话语技巧,在国外要么不被接受要么看不懂的原因之一。显然,坦率直白的符号编码信息,对于以西方为主的低语境国家解码者而言,更为直白和清晰。
(二)共同价值:小空间的微叙事
上述的共同情感符都是基于输出寻求与受众一致的符号,而笔者认为“同情认同”还可能存在于相似的生活经验、“可转移”的体验,和共同的普世价值。澳大利亚文化产业经济学家霍斯金斯曾提出的“文化折扣”的概念:“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它地方其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假如电视节目或电影是用另外的语言制作的话,因为需要配音和打字幕,其吸引力就会减少。即使是同一种语言,口音和方言也会引出问题。”③因此,为了减少“文化折扣”,在《中国面临的挑战》的话语策略中,“同一”的方式不仅仅停留在“共同情感”的层面,还将其扩大到了“共同价值”。但“价值”往往是无形而又容易陷入宏大而空洞的陷阱,因此小空间的微叙事恰好可以为相似体验和共同价值提供这种传递渠道。
“微叙事”,即“较短时间内达成的故事描述或意义表达”④,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由于“宏大叙事”表达有限,相较于“公共空间”,讲述小场景、小空间中的小人物及其故事更容易获得“同情认同”效应。
《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有小空间人物、事件的描述与表达,如在《会制造的中国人,你会创造吗》一集中主要探讨中国制造如何创新创造的话题,里面选择了若干个小人物的故事进行展开,有油画家、手机商、就读双语学校的学生、创业者等,每个人物的故事讲述时间都在3-4分钟左右,故事均只在他/她所在的小空间小环境内做一个大致的讲述,但会通过当事人出镜口述和解说词点出和主题相关的核心因素。如深圳大芬村的女油画家吴媚和这个村的大多数人一样是靠模仿西方名画制作流水线油画起家,但经过金融危机的历练和市场需求的转型,只有她和少数画家走上从模仿者到原创者的道路,存活下来并最终开拓了新的市场。故事简明扼要且具有代表性,全球制造业如何从模仿到创新,尽管所处的阶段不同所花的时间不同,但对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中的人民来说都是必须经历的阵痛,通过一个个的“微叙事”串联起来,“共同价值”的传递就有了落脚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用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一句话作为注解:“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同时配以主持人行走在油画村小巷中由全景升至远景的俯视镜头,古典音乐悠扬传来,调动了观众的想象与思考。因此,着眼于小空间的微叙事来进行形象传播和建构还包括了解说词文本、视听语言等方面的综合运用。
三、“对立认同”
“对立认同”,指两者由于具有某种对立面而形成联合,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敌人。这个共同的敌人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更可能是人的生存环境,还可能是制度、理念等等。在中国文化与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强势文化对话时,往往会有诸多关于政治、宗教、民族性格因素的障碍难以跨越,这些似乎成了都可以被视为“对立面”。但仔细分析这两部中外合作纪录片的话语策略不难发现,在貌似不一致的“对立面”之外,其实都有一个双方都反对或不认可的“敌人”,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达成共识或形成联合。
(一)去“他者化”
“他者”原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在后殖民的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这个术语后来被泛化到不同社群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交流,指的是相对于中心/主流文化方的弱势文化者⑤。在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去“他者化”是诸多传播者努力的方向,中国纪录片国际化的过程中,可以借用“对立认同”的修辞策略进行去“他者化”。

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剧照
《中国面临的挑战》中有一集《中国人,你信什么?》探讨的是中国人信仰和宗教心理、宗教政策的问题。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常常有批评认为中国宗教关系紧张,相关政策也较为严格,如只能在国家允许的宗教场所内传教。这在有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诸多西方受众看来,就是一个与他们有很大差异的“对立面”。面对这样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该集纪录片的话语策略大量采用了“对立认同”的修辞,即找到了西方人宗教信仰自由和中国特色宗教信仰自由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伪信仰自由”、“伪宗教自由”。首先在开篇有这样一句解说词说道:“(在中国)只要这个宗教是劝说人们做好事,对他人富有爱心和慈悲心,无论信仰哪种宗教都没有问题”,先奠定了中国人信仰传统的民族心理;然后通过采访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分析出了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的视角看待中国/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包容并存,即解释了中国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文化根源。而对于相应的传教规定,一个基督教的上海牧师给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一个一个敲开非信徒的门做访谈,会反感我们的,可能因为这个反感,使得我们无法传递福音”,即我们的宗教政策不是限制自由反而是因地制宜地契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因此,尽管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看似存在着“对立面”般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主要是国情、民族性格的差异,而不是有没有、能不能宗教信仰自由的本质差异。在此处的话语中,对于一些国家/地区披着信仰虔诚实则没有宗教信仰选择自由的“伪信仰自由”、“伪宗教自由”才是全球不同信仰者共同的“敌人”,从而实现了与异质文化观众的“对立认同”。
(二)民族性是真正的受众视角
受众在接触外来文化的早期是存在猎奇和观赏心理的,但随着新鲜感的逝去,在看多了“他者”习俗、歌舞之奇观“秀”之后,受众开始思考这些“秀”背后的民族历史缘由、与该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关联性、民族间差异的合理性等,从而实现“使用与满足”。
在以往国外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中,由于制作团队较少有中国人参与,在创作时可能或多或少会代入“自我”文化对“他者”文化的理解,甚至是对“他者”的误读、偏见等。《大道中国》源自韩国KBS电视台2015年特别推出的一档纪录片《超级中国》,中方引进后将其进行了改编,原片名《Super China》(超级中国)略带“超级大国论”的意味显得张扬浮躁,与中国崛起的未来取向并不相符,更改后的片名《大道中国》则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背景,蕴含了包容、平和的民族性格。因此,采取中外合作方式的纪录片在兼容国际视角的同时,可以避免陷入被外部文化浅层次读解甚至曲解的情况,更多地从本民族国家的文化、性格、历史中寻找现象背后的答案。“同一论”中“对立认同”的本质也是通过在分裂中形成凝聚,对于跨文化语境的受传者而言,对其他国家/民族/地区的认识并不是浅尝辄止于“走马观花”,感受表象行为包裹下的文化核心才是真正的受众视角,这也是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一种诠释。
四“误同”
“误同”是伯克“同一论”中最富有创新性的观念,它大多可使受者在无意识中与传者达到认同,从而被说服,因此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软性修辞。误同经常的表现形式在于人对自身处境的误同上,如女性在购买某女星代言的护肤品时,会假想自己用了该产品后也会如女星一样拥有白皙的肤质和优雅的外貌。从这两部中外合作纪录片看,“误同”的修辞主要体现在影片主持人和采访对象的选择上。

纪录片《大道中国》剧照
《大道中国》中《文化软实力》这一集中,谈到中外文化的交流及“中国热”的出现,讲述了非洲、欧洲几个国家孔子学院的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在其中的一个案例中,巴黎孔子学院的几位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学习和理解成语“塞翁失马”,体会到了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及文化内涵。如此对于外国观众而言,他们也容易将自己假象为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那些学生,从而无意识中也参与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种“误同”在影片中普遍存在,学习中国功夫、气功、太极、书法学书法的外国人身影和个案频频出现。
《中国面临的挑战》则将这种“误同”修辞贯穿了全片,典型的体现就是由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担任全片的出镜记者,他深入工厂、医院、民工子弟小学、养老院、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进行实地采访,与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士交谈。在片中,库恩的角色同时是讲述者、观察者、倾听者、发问者、体验者,如在《中国,文明依旧重要吗》一集中,库恩就与中国太极武术家切磋美国拳击和中国太极的差异及融合。由一个外国人串联主持的方式,体现出中西方的互动和对话性思考——库恩提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问题,中方则直面问题,呈现事实,并尝试剖析事件背后的一些关联因素。⑥
《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大道中国》是近几年中外合作纪录片中影响力较大的两部作品,从新修辞理论“同一论”出发切入话语策略融合了艺术学、传播学的范畴,也是包括外宣纪录片在内的影视作品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小视角。笔者希望能通过应然和实然的分析,映射出制作/传播主体对信息的表述、隐含的动机及价值观的呈现,找到跨文化传播中的冲突与平衡,从而为认知传播活动提供反思。
注释:
①《大道中国》是由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与韩国KBS电视台在2015年联合特别推出的纪录片,它的前身是韩国原版的《超级中国》。
②刘莉:《伯克新修辞学同一理论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③ 谭天:《两种文明观:中日版本纪录片〈新丝绸之路〉的对比分析》,视听》,2016年第3期。
④ 乔新玉:《微叙事:多屏互动时代的传播奇观》,《现代视听》,2013年第11期。
⑤张贻苒:《云南民族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分析:民族视角与文化间性的融合》《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⑥ 辛静单波:《建构具有对话性的中国形象》《当代传播》,2015年第4期。
(本文图片由张贻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