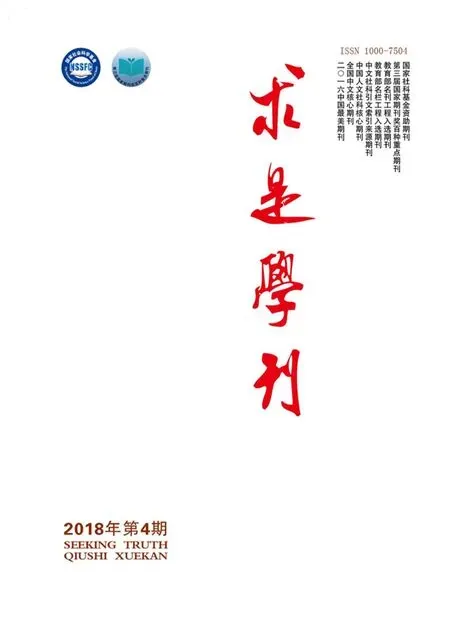解释学的同一性批判
——再论张一兵文本学
张 琳
“文本学”①为了行文上的方便,本文将张一兵教授所提出的文本学及其后来的两个演化版本“后文本学”和“思想构境论”统称为“文本学”,指称张一兵的解释学思想。是张一兵教授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提出的一种解释学方法论。它秉承了张一兵治学的批判性维度,该理论的提出、发展与深化正是通过对思想史研究背后的解释学立场的批判而得以完成的。张一兵指出,这种解释学追求以某一元素为中心对异质性元素的同一性统摄,或是同一于作为绝对主体的作者与读者,或是同一于作为绝对客体的文本。而他的文本学拒绝任何单边主义霸权对异质力量的占有性支配与遮蔽,它以文本解读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的历史复杂性和异质性对各种同一性强制予以逐一消解、各个击破,并最终展现出文本解读乃祛中心的异质性构境,意义是在作者—文本—读者三种异质性力量的当下互动中的情境突现。
初版于1993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张一兵将“驳论性”列为该书六大理论原则之首。“由于本书力图纠正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历史过程关系的误释,所以众多理论阐述的字里行间中总是在辨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规定‘不是什么’,这是一条理论主线。”②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自序(1993),第13页。熟悉张一兵教授的读者不难发现,批判性的驳论是其思想表述的一条主线。文本学自不例外。文本学的提出、展开与演化,正是力图纠正传统思想史研究对思想家的种种误释,并努力辨识出文本解释的过程“不是什么”:不是前苏东中心,不是文本中心,不是作者中心,也不是读者中心。在张一兵看来,这种“中心论”意味着阿多诺所批判的全部“史前”人类思想发展中轴线——同一性逻辑。③参见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引言,第57页。同一性逻辑的背后是主体或客体的绝对性,是对异质性的抹杀与强制,最终将是对真理的扭曲和遮蔽。而文本学所做的,恰恰是指认出那些溢出于同一性逻辑之外的异质性存在,并在异质性构境的基础上实现开放的、有限的真理。
一、以五大解读模式消解前苏东教科书的同一性强制
在张一兵提出文本学思想的20世纪80年代,国内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是被前苏东教科书体系所主导的。前苏东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式诠释和同质化处理在当时代表着唯一正确的权威解读,我们自己的研究者只能是非反思地相信与无条件地同一于这些教条,任何对教课书的违背都被判定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违背。
面对前苏东教科书的同一性强制,张一兵摆出了“五大模式”这一国内外马哲研究的实情。他概括指出,自20世纪30年以来,国内外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讨论中大体出现了包括前苏东模式在内的五大解读模式,它们分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教授的模式。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内外学术平台上,“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异质的”,这也就意味着前苏东模式仅仅是与大家平起平坐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国内学界长期赋予它的唯我独尊的解读霸权。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导言以“五大模式”开场,其用意①张一兵直言:“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就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这是我在导言中首先提出不同解读模式的深层寓意。”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27页。正是要以解读模式的异质性击破前苏东模式的同一性逻辑,赋予每个解读者以合法性与话语权。
与之相伴随,过去被“原理”和“体系”长期遮蔽的文本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载体和源头活水,又重新回到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公认的前提和起点。这也正是张一兵“回到”系列②“回到”系列指的是张一兵教授以“回到”命名的一系列思想史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包括《回到马克思》(1999年第一版)、《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2008年,以下简称《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2014年,以下简称《回到海德格尔》)和《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2016年,以下简称《回到福柯》)等。的初衷所系:跳出权威解读模式的同一性强制,直面第一手的文本,给出每个解读者自己的异质性解读,推动学术研究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以读者对意义的创造性生产消解文本意义的同一性强制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前苏东教科书的主导性地位的瓦解与衰落,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自由与繁荣的活泼景象。然而令人喜忧参半的是,“回到文本”之后的学术界在摆脱前苏东教条主义的同一性强制的同时,却无法在丰富多元、五花八门甚至大相径庭的各种解读结果中获得新的同一性。而最令学界困扰的是,每个解读者都以“回到文本”来宣称自己解读的绝对正确,但不同的解读者之间往往又无法相互承认,更难达成一致共识,其结果就是“为真理的霸主地位而争得面红耳赤”的尴尬境地。
在那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思想转型年代,几乎每个个性化的解读者都难逃“过度诠释”的质疑。张一兵教授曾提及对他触动最大的来自与他本人思想发展最为密切的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两种批评:“一是我的一些老师特别是孙伯教授曾当面批评我:我们做了一辈子的马克思,为何没有看到你所言说的马克思文本中的东西?二是在许多次课堂讨论中,同学们总是提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同一文本上看不到你所指出的东西?’”“‘你书里写的一些东西,到底是原作者的思想还是你的?’”①张一兵:《回到列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作者的话,第12页。简简单单一句“为什么你在文本中看到的东西我没有看到”背后其实是一种极为根本的否定:既然文本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你能看到,我就也应该能看到;如果我看不到,甚至我们很多人都看不到,就说明你看到的东西并不属于文本的客观意义,而只是出于你的主观臆造。由此一来,无法被学术共同体承认,无法达成学界共识的解读结果,直接就意味着它是缺乏客观真理性的主观臆造。
然而,对上述质疑细加推敲便可以发现,其立论是以文本意义的客观同一性为预设前提的。这种客观同一性意味着,文本意义在逻辑上必然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而且在不同时空下,所有人看到的永远都是同一个东西。这非常类似于自然科学实验真理观——真理的判断标准是科学实验的可重复验证性,也即实验结果在实验者本人以及其他实验者之间保持超时空的同一性。在笔者看来,以文本意义的同一性作为真理标准,其实是对自然科学实验真理观的不自觉挪用。因此,面对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上述质疑,在警惕和质疑文本解读中的主观臆造的同时,同样或者首先需要慎重考量的是:人文学科对自然科学实验真理观的这种挪用是否合法?
张一兵教授提示,文本意义的客观同一性预设恰恰是自然科学带给人文学科的最大陷阱。因为它无视文本解读过程中文本意义的非实体性存在以及读者意义对文本意义的重构与溢出。②张一兵:《回到列宁》,作者的话和导言。在张一兵看来,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不是深入文本之中的探囊取物,文本意义并非是实体性地存在于文本之中现成的定型之物,③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载《张异宾自选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03页,原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布展开来,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④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2001),载《张异宾自选集》,第44页,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文本解读本质上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激活与重构,是每个解读者基于自身的支援意识等个性化资源对文本意义的创造性再生产而非同一性复现。读者所获取的意义(意义B)和文本的意义(意义A)之间始终不可能完全重叠与同一,读者意义从其本性上就是超出文本意义的同一性强制之外而拥有保存异质的合法性。⑤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由此,张一兵指出了一个多少有点令人不安的实情:承认解读结果上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将意味着,每种解读结果的真理性不再是绝对的、排他的,而是敞开的、有限的。⑥张一兵:《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与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论——兼答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挟真理以令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三、以作者对文本的分层分时发布消解读者的同一性强制
如果说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处于历史和现实所赋予的至上地位,从而一定程度上对读者形成了某种同一性强制,那么在学术批评领域,情况却恰恰相反。作为批评家的专家性读者、权威性读者,在面对同行特别是新生代的个性化文本时,往往拥有学术共同体所赋予的正统地位和同一性权力,从而使得后现代主义所张扬的“作者死了”、读者至上⑦参见张一兵:《巴特论阅读——对阿尔都塞的一种理论“反打”》,载《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4页。成为学术批评中一种并非健康的倾向和风气。
作为“经常在捅哲学固有江山中的马蜂窝”①这是张一兵的自嘲:“我可能经常在捅哲学固有江山中的马蜂窝,让人家不能安居在惯常的学术治安的洞穴里,不过,真不是有意而为之的。”参见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第一卷),后记,第505页。的个性化学者,张一兵教授对于读者至上的同一性强制,可以说有着较为切身的体会。在其成名作《回到马克思》再版之际,张一兵提到这本著作问世十年以来的际遇令他颇感意外:在真诚的学术批评之外,仍然不乏一些学者的粗暴否定和暴力批判,“以一种想当然的理论构架将《回到马克思》座架到他自己假想的批判罗网中……这其实是一种低层次的理论法西斯主义!”“这些人思想中所内居的深层语法结构恰恰还是暴力性的,因为他们总想通过简单地贬斥他人、专横地自我标榜来非法照亮自己……”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二版序言(2008年),载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三版),第50、22页。也因此,张一兵在自己的第二本“回到”——《回到列宁》一书引言中如此表达了作为作者的无奈:“读者始终为上,真正存在的永远是读者以自己的理论逻辑去积极建构的某种特定的理解之境。”“读者的思想构境总是处于权力话语的地位,不在场的作者和沉默的文本总是弱者。这才是真相。”③张一兵:《回到列宁》,导言,第47页。
是否文本一经公开发表便取消了作者对文本的一切权力?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是否完全被动地同一于读者的解读和判断?张一兵用海德格尔的学术场境故事给出了明确的否定。海德格尔把自己不同性质的文本展示给不同的读者。被迫臣服式的表演性文本、争执式的表现性文本、隐匿性的神秘文本和直接在场的现身性文本是张一兵教授根据海德格尔的“写给谁看”而对其思想文本所做的区分。张一兵强调,前两类文本都是海德格尔迫于学术权力场而对自己真实思想的有意遮蔽和变形,后两类文本才是其真实思想的直接呈现。而且,这四类文本不仅区别发布的空间以面对不同层面的读者,而且还区别发布的时间以便把不同性质的文本展示给不同时代的读者。
四种类型的文本及其时机性发布,表面上是海德格尔对自己文本的分类,其背后也是这位古灵精怪、世事练达的大思想家针对读者的接受度和理解力所做的区分。因为正如张一兵文本学所提示的,文本的生命力有赖于读者去充盈与延续,④张一兵称:“没有任何读者的文本就是已经死亡的东西”,参见《回到列宁》,导言,第51页。作者的不在场与文本的沉默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总是由每个时代的每个读者来述说。读者自身的局限性愈大,对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遮蔽也愈深;反之亦然。因此,作者基于对读者接受度和理解力的考量而分层分时地发布自己的文本,也是消解和对抗读者的同一性强制而葆真文本的一种无奈现实之下的策略性安排。在笔者看来,这是在某种意义上追求孔夫子所讲的“不失言”亦“不失人”。⑤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篇》)
四、同一性批判的反身自指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学在消解文本解读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任何一方的同一性强制的同时,也对张一兵教授本人的学术研究形成了某种反身自指的同一性批判。这种批判来自学界同行,也来自张一兵自己的学生,甚至还来自张一兵本人。⑥张一兵称:“《回到马克思》一书只是一个‘在途中’的努力……为此,我当然愿意做今天中国第一个自觉组织‘批判’自己论著的人”,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二版序言,第25页。
较早指认张一兵治学中隐含的同一性强制的是北京大学的杨学功博士。“北京大学的杨学功博士也曾经当面向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读全集,那么是不是不读全集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我这里边有一个暴力性的强制,因为我读了原著,所以我讲的马克思是最原本的。”⑦张一兵、刘景钊:《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张异宾教授访谈录》,载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708页,原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10期。这类指认在事后得到了张一兵教授的正面承认,①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里面处处反映了这样的念头”,即“我的理解是客观绝对正确的”,我的理解“是最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实际上我的所有关于马克思的看法……都不过是我自己的一种看法。”参见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并由此从根基处修正和重塑了他后来的学术表述方式和文本学思想。
这种转变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体现在出版于2008年的《回到列宁》一书中。张一兵强调,《回到列宁》所运用的思想构境论“超越了”②张一兵:《回到列宁》,作者的话,第3页。《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学解读法。具体而言,《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尽管张一兵在思想意识上“已经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即我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不会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只是一家之言”,③张一兵、刘景钊:《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张异宾教授访谈录》,载《回到马克思》,第708页,原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10期。但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坚持把自己的个人理解说成是“马克思认为”,并试图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取真理霸主地位。但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张一兵则坦陈自己的研究不过是“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症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不再将自己的一家之言的解读结果直接等同于研究对象的思想本身。“我的就是我的,不硬说是他人的”。张一兵力主在思想史研究中对“是什么”与“我认为”之间做出界分,并自觉摒弃了作为权威解读者的同一性强制。
然而,张一兵教授还面临着另一项可能的“指控”:作为原创性作者的同一性强制。张一兵赞同④参见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第63页。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哲学内涵的暴力性”的指认:“谁拒绝跟着做,谁就会被怀疑为没有精神祖国、没有存在家园的家伙。谁就是‘卑鄙的’。”⑤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7页。在一次访谈中,张一兵对此亦有所反思:“我将来也可能被批判的是,我是海德格尔式的神秘主义的或者贵族式的东西”,“像阿伦特和雅斯贝斯骂海德格尔一样,说不懂诗意的生存的都是下等人。金福没骂我说,TMD不懂你的构境论的都是笨蛋呵,将来肯定有人骂我”。⑥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
如何在批判同一性的同时避免造成新的同一性强制,如何超越同一性逻辑的理论闭环和权力对抗?文本学以构境存在论为依托,从同一性批判走向异质性构境,或许可以视为张一兵教授破解同一性强制的一种理论努力。
五、从同一性批判到异质性构境
张一兵教授将自己的“回到系列”——《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和《回到海德格尔》分别标定为文本的客体视位、读者的主体视位和作者的主体视位。⑦参见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第7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视位”(Blickstand)的标定与各种强制性的同一性逻辑有着绝然的区别。视位不是设定中心,而只是一种角度的提示;视位不是强行同一,而只是推动一种视向(Blickrichtung)和视域(Blickweite)的展开。⑧张一兵:《“何所向”:历史性解释的基始性构境——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载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第299—304页,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进而言之,张一兵文本学所标示的三种视位,是对文本解读过程中三种基本的异质性力量即文本、读者和作者的标定,而且每种异质性力量在同一性逻辑面前并非是无条件地束手就擒,而是以构境的方式具体地、历史地参与到每一个当下的重新建构。
尽管以主体向度为理论特质⑨参见张琳:《胡塞尔现象学语境中的张一兵“文本学”》,《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的文本学常常被误解为对文本向度的抹杀或者忽视,但事实上张一兵在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坚持和强调以文本作为起点和基石。在他看来,“我们手上应该居有的文本语境的厚重性。……这种阅读训练具有像马林科夫斯基所说的‘田野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基始那般的前提性和不可跨越性”。①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丛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丛书总序,第5页。强调“回到文本”的《回到马克思》自不必说,即便是突出方法论上的主体向度的《回到列宁》与《回到海德格尔》,张一兵也始终坚守文本的“前提性”和“不可跨越性”。《回到列宁》中所运用的读者视位,并非“一种主体的随意论,它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准确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依据对列宁文本的更精细的分析,在特定条件下对列宁文本的分析”;②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而在《回到海德格尔》中,“从作者主体视位出发,基于写作和思考情境”所做的文本分类,也“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观产物。这种研究中的‘主体性’创造活动,只有在大量的‘对象性的’文献研读过程中,并在传统研究框架(既定学术治理场的内化)‘失范’的地方才能发生”。③张一兵、苏明:《“回到事物本身”:马克思、列宁和海德格尔》,载张一兵:《构境论: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张一兵访谈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为了进一步标定文本、读者、作者三种视位之间的共生关系,张一兵将文本研究的具体过程细化为三个阶段:一是符号文本层解释(文本视位),二是互动性的意义场的理解(作者视位),三是生产性文本阅读的思想构境(读者视位)。④张一兵:《回到列宁》,导言,第51页。通俗地讲,“我们要理解一本书,首先文字要看懂……知道文本说了什么”;然后是“在看懂文字的基础上还要弄懂作者提问的方式,提问的方法”,以便把握作者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最后是在弄懂了文字的意义、作者的观点和意图之后,我们产生出来新的意义,即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生产。⑤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的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2013年第4期。张一兵强调,文本研究的每一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和支撑,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深化与扩展。相应的,每个视位也都是不可替代的,相互之间是一种支持与扩展的关系。
张一兵将文本解读的实质理解为异质性构境的过程,它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以文本语义层为桥梁和依托而“重新建构起来的意义情境”,⑥张一兵:《回到列宁》,导言,第47页。是三种异质性力量在构境过程中实现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性异质视域融合”。⑦张一兵特意强调:“一些论者……以为那本书(《回到马克思》)是在原教旨主义地回到马克思的‘全集’和‘原文’。其实我的所谓文本学研究从来就是历史性的异质视域融合。”参见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序,第6页。与传统解释学中同一性逻辑的本体论预设不同,文本学的基础是构境存在论,它是“一种交互主体论。不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占有性的支配与被支配,而是一种互动生存论”。⑧张一兵:《学术小传》,载《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张异宾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结 语
本文以批判性的驳论来呈现张一兵文本学在理论立场与核心主张上的发展与演化。为了确立文本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基始性地位和不同解读者的平等话语权,文本学以文本解读结果的复数性和异质性消解了前苏东解读模式的绝对真理性;为了证成读者意义与文本意义之间不可避免的异质性,文本学以文本意义的激活与呈现离不开读者的创造性再生产消解了文本意义的客观同一性幻象;为了彰显作者作为文本第一权利人的应有地位,文本学以作者对文本发布的时机性把控消解了读者至上论的傲慢与偏见。在驳论的语境中可以发见,文本学的批判性在理论表述上的进攻与激进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防御和保守:同一性,为异质性留余地。在这个意义上,张一兵文本学既在理论主张上映射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内学界告别独断、封闭走向自由开放与多元共生的历史进程,又在解释学层面上为这一伟大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自觉。
批判一切同一性哲学的阿多诺,以和平的伙伴式“星丛”反对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强制。星丛是“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是“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与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①参见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引言,第56页。始终贯彻与践行同一性批判的张一兵文本学,在走向异质性构境的进程中,也在力图推动中国学术界和批评界走向群星熠熠、相映成辉的灿烂“星丛”。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言,真理即是星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