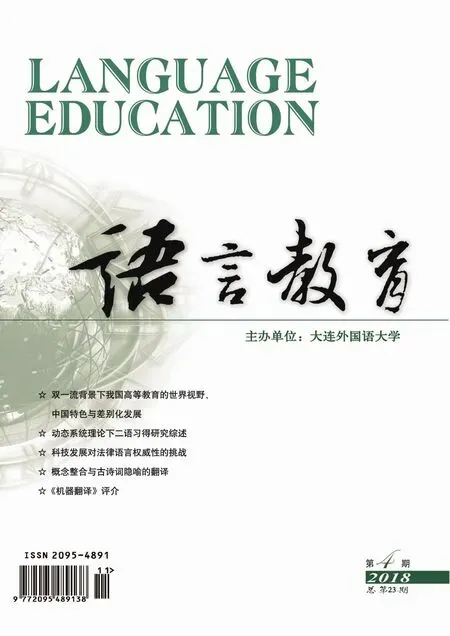理性决定种族归属?
——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慧骃国游记”
叶婉华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深圳)
1.同类“使用”的伦理禁忌
《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最后一卷“慧骃国游记”(AVoyage to the Country of the Houyhnhnms)在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学者们通过探讨其与科学、哲学、历史等关系,从文本溯源、精神分析、文类分析、女性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各种“解密”,然而,它的最终涵义似乎成为永久的谜题。
本卷人们争论的问题是:格列佛(Gulliver)对野胡(Yahoo)乃至整个人类的憎恶是否代表了斯威夫特对人类的态度?许多学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格列佛在慧骃国的遭遇能够证明见识过“完美生活方式”的人不能再适应空洞庸俗的人类社会,斯威夫特戳破了人类是理性动物的幻想①此类评论的代表者为GeorgeSherburn和Ronald S.Crane,见Sherburn,G.1958.Errors Concerning the Houyhnhnms[J].Modern philology(56): 92-97.和Crane,S.1961.The Rationale of the Fourth Voyage [A].In R.Greenberg (eds).Gulliver’s Travels:An Annotated Text with Critical Essays[C].New York:W.W.Norton&Company.。而另一部分评论家却强烈抨击这一论断,认为不能将格列佛和作者的态度混为一谈,斯威夫特的尖锐嘲讽针对的是文中出现的几乎所有人物②持此立场的学者有Kathleen William和Edward Stone,见Williams,K.1951.Gulliver’s Voyage to the Houyhnhnms[J].ELH (43):275-286.和Stone,E.1949.Swift and the Horses:Misanthropy or Comedy?[J].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3):367-376.。然而,学界争论的同时,对此问题的先设条件却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格列佛自诩理性,为什么会糊涂到将对毫无理性的野胡的厌恶直接转移到明显具有理性的人类上?如果只是单纯认为文本嘲讽野胡所体现的“人性本恶”,或断定格列佛“疯了”或者“太天真了”,只会陷入正反二元论的困境,非此即彼的论断只会使最后一个问题的解答愈加困难。其实,如果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格列佛对野胡并非只是憎恶那么简单。
在第十章中,格列佛用野胡皮和油制造各种用具,如“鞋帮穿烂了就再用晒干的‘野胡’皮做鞋帮”(Swift,2010:217)。在制造回乡的小船时,“我用自己搓的麻线将一张张‘野胡’皮仔细缝到一处起来把船包起来。我的帆也是用‘野胡’皮做成的……”(Swift,2010:221),“我在我主人家附近的一个大池塘试航了一下我的小船,把有毛病的地方改造了一番,再用‘野胡’的油脂将每一处缝隙堵死”(Swift,2010:221)。在不多的此类叙述中,作者还特地指出了一处细节,即,最小“野胡”皮比老一点“野胡”皮更加好用,因为“老一点的‘野胡’皮太粗太厚”(Swift,2010:221)。
这几处描写格列佛如何使用野胡制品的情节,如同昆西在“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中所述的一样,给读者“在感觉上产生了一种……永远也无法说明的效果”(昆西,1823:145)。这种效果是令人惊骇和畏惧的——文中此时,格列佛早已从内心接受了野胡是人类这一事实:“当我想起我的家人、朋友、同胞或者整个人类的时候,……他们还确实是‘野胡’”(Swift,2010:219)。然而同时,格列佛却如同使用畜类皮制品般使用同类皮制品,尤其在格列佛轻描淡写地谈及小“野胡”皮比老“野胡”皮更好用时,不就是谈论婴儿的皮比起成年人的皮更加有用吗?仔细思量,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文学伦理学认为,人通过理性而产生伦理意识,建立并遵守伦理秩序,使人类得以繁衍下去,其中,“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聂珍钊,2010:18)。食人和使用同类便是伦理禁忌中的一种,因为人类内心天然存有精神联系,这使人在对同类进行食用或肢解的时候产生感同身受似的痛苦。休谟(David Hume)将这种特殊的联系称为“同情”(sympathy),并认为是道德伦理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见休谟.1996.关文运译.人性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斯密(Adam Smith)将同情进一步拓深为“同感”(empathy)——人天生通过同情联想可以感知他人的痛苦或快乐。“借由想象,我们把自己摆在他的位置,我们设想自己正在忍受所有相同的酷刑折磨,我们可以说进入他的身体,在某一程度内与他合而为一,从而对他的感觉有所体会”(斯密,2008:20)。在同情原则下,不食人和使用同类是人类特有的伦理保护机制,虽然从物质性来说,人的肉体和动物并无大不同。
令人惊异的是,并无学者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对文中的伦理禁忌进行解读。实际上,评论家们对这部分的关注并不多,只有寥寥几人提起。代表性评论有罗森(C.J.Rawson)与凯莉(Ann Cline Kelly)。罗森(C.J.Rawson)在“格列佛与温和读者”(Rawson,1973:689-693)一文中,将格列佛与《一个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中提议父母售卖婴儿之肉以维持生活的“建议者”相提并论,认为:“尽管格列佛……不像(《一个小小的建议》中的)建议者那样宣扬同类相食(Cannibalism),但是他的确用野胡皮来做衣服和船及船帆”(Rawson,1973:689)。这里,罗森虽然注意到伦理禁忌的问题,却明显认为这只是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并未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进一步阐述其深层次原因。凯莉(AnnClineKelly)认为此举是格列佛为“确立他与野胡的不同,并建立起对野胡的统治”(Kelly,2009:218),但也只是一语带过,并未注意到格列佛使用同类的伦理问题。
本文将从文学伦理学出发,“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聂珍钊,2010:20),通过分析启蒙时代哲人们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论述,审视和厘清格列佛、慧骃与野胡之间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解答格列佛若无其事地使用动物皮制品般地使用同类皮制品的原因,以及作者设置这样的“残忍”的场景的用意,最终得出格列佛此举的意图——与人类进行伦理切割,使自己在绝对理性的基础上与慧骃种族伦理属性趋同。在他看来,理性是决定伦理归属和占据伦理秩序制高点的唯一标准。而作者是明显对此持反对意见的。
2.慧骃与野胡:人与动物
慧骃与野胡的伦理关系在三者中最为简单明了。从文学伦理学角度来说,“‘伦理’是指人或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自然形成的关系和秩序”(修树新,刘建军,2008:167)。那么他们两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否存在?从文中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慧骃与野胡的关系极为简单和直接——野胡是一种工具,经过强制性地驯服后,能为慧骃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它们替慧骃拉车,擦身子,梳鬃毛,喂草料等等。在第九章中,作者进一步明确了野胡的动物属性——“当地居民还突发奇想,想用‘野胡’来为自己服务,结果十分轻率地忽略了对驴这一种族的培养。驴这种动物文雅、温顺、规矩、容易养,也没有任何难闻的气味,虽然身体不如‘野胡’那么灵活,但干活的力气还是足足有余的”(Swift,2010:214)。这一特意将野胡和驴子进行对比的描写使作者的意图更加明了——慧骃与野胡的关系是人与动物关系的类比:慧骃如人类驯养其他野兽一般驯养野胡。因此,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论述入手,尤其是探讨本书写作的启蒙时代关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互相地位对比等思想和观点,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解读慧骃与野胡的关系。
人与动物的关系论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动物学意义上对“人”下过定义: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动物是“种”,有理性是“属差”,理性是人的本质,“只有人才能用概念进行思维,能认识事物的一般和必然的本质,产生抽象的理论知识”(王成光,2015:73)。在启蒙时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对动物的论述一直影响到当代。作为唯心主义论者,他认为人可以通过思维来描述这个世界。人的“思维”(mind)是个独立的物质,与上帝的“思维”联系在一起,而不具备“思维”的动物,只是“自动的机器”(笛卡尔,2000:44),没有思想,理性和灵魂。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虽然认为残酷对待动物于人的道德有害,但是认为人类拥有理性,而“这种能力正是人和畜类差异之点所在,而且在这方面,人是显然大大超过畜类的”(洛克,1983:666)。另一启蒙时代学者康德也认为人具有理性,所以才能成为被尊重的对象:“人类以及一般来说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是作为自身即是一目的而存在着,……那些其存在并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而是依赖于自然的存在者,如果他们不是理性的存在者,就只具有一种作为手段的相对价值,并因此被称作为‘物’;而理性的存在者则被叫做‘人身’”(康德,2006:83)。康德在这里很明确指出,动物并不具有理性,不能作为目的存在,而只是具有手段价值的“物”,不能成为限制我们道德行为的根据。
总而言之,从古希腊时期到高扬理性旗帜的启蒙时代,哲学家们以理性、思想、灵魂等抽象特质是否存在作为依据,确定人的“本质”,并在人与动物之间划出清晰界线,消除各种可能令人与动物不分的两可状态,确立人在世界上的中心位置。在这样的情境下,严格依照理性去对待或使用动物“在启蒙时代角度看来都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举止”(Panagopoulos,2009:153)。
3.慧骃与格列佛:理性决定种族伦理归属
那么格列佛是慧骃伦理社会中的一员吗?首先必须看到,格列佛与野胡有着显著不同,这不仅体现在格列佛外表干净,举止有礼,而且,他擅长思考,懂得感恩,拥有口才,具有在“理性和美德”上提高的潜质。书中,最令格列佛的主人感到惊奇的“还是我(格列佛)那说话和推理的能力”(Swift,2010:183),于是他悉心教导格列佛慧骃的语言,在与别的慧骃交谈时允许格列佛旁听,并发表意见,还每天指出他上千的错误,让其改正。平时格列佛外出时,还派家里的仆人去保护他。格列佛在慧骃主人家中有着多种角色:他不仅是解闷的宠物,而且还是被教导的学生和偶尔提供建议的有用野胡。那么,有理性,有自由意志,已经成为一个伦理社会的准成员个体的格列佛,能否被纳入慧骃的伦理体系中呢?
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慧骃主人认为格列佛不是同类。慧骃主人虽然对待格列佛格外和善,与其他野胡截然不同,但是认为格列佛归根结底还是个“畜生”。如,书中说到他曾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格列佛的建议,用比较温和的阉割野胡的方式“一代之后就可以将所有‘野胡’全都灭绝”(Swift,2010:214),并认为“向畜生(格列佛)学习智慧也不是什么没有脸皮的事”(斯威夫特,2010:214)。可见慧骃主人始终认定格列佛为动物。其二,慧骃的全国代表大会认定格列佛是野胡。大会举办过程中,与会的“代表们都对它(慧骃主人)家里养着一只‘野胡’(指我)很反感,而且养‘野胡’不像养‘野胡’,倒像对待‘慧骃’一样……,这样的做法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Swift,2010:219),因此要将格列佛驱逐出慧骃国。格列佛的慧骃主人虽然并不赞同,但是却没有阻止。格列佛与慧骃的关系最终还是归于慧骃版的“万物链”关系——处于最高地位的生物(慧骃)与可任意处置的动物(格列佛)之间的关系。
为何格列佛谦卑又好学,勤勉而坦率,同时时时表现出对慧骃的崇拜,渴望继续向慧骃学习和向好的决心,却始终不能被其接受为同类。慧骃认定确立伦理关系的标准和依据究竟是什么?
在文中,慧骃用以区分它们和格列佛所代表的人类的标准有两种:第一,外表。在第四卷的前两章,慧骃主人及其家人遇见格列佛时,马上判断他是野胡。甚至它奇怪于格列佛的“可教,有礼貌,干净”(Swift,2010:180)的同时,也坚信格列佛是一只野胡,这一切都源自格列佛与野胡外形的相似。到了格列佛衣服的秘密被发现后,它们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断。然而这种基于外貌的本质主义式下定论方式在文中却遭遇了自我解构:文中的驴子,如果去掉耳朵的些许不同,和慧骃(即马)几乎一模一样。而驴子在慧骃的眼中,不过是与野胡相似的受奴役的动物的一种,在第二章中,慧骃们还试图喂给格列佛驴肉(Swift,2010:177)。另外,通过格列佛对英国马匹的描述,慧骃们也确定英国的马与它们是属于不同的种类。这只能证明一点:外形相似即属于同一种族,不过是个伪定论。
第二,是否具有理性,是否满足“自然与理性就足以指示我们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Swift,2010:192)的条件。对于慧骃而言,“理性是一种本能”(Panagopoulos,2009:147),“它们的伟大准则就是培养理性,一切都受理性支配”(斯威夫特,2010:210),而且“它们的理性因为不受感情和利益的歪曲和蒙蔽,所以该怎样必然立即就让你信服”(Swift,2010:210)。因此,理性成为慧骃这一种族的绝对指标,一切不包含绝对理性的“生物”都是其他族类的他者,都会被视作慧骃版“万物链”中慧骃之下的生物。根据这一标准,格列佛及其他所诉说的人类现状并不满足这一条件。
在这里,慧骃对“种族”异乎寻常的执着值得注意。据富兰克林(Michael J.Franklin)统计,在《格列佛游记》中,“种族(species)”一词出现了至少27次,其中至少有22次出现在“慧骃国游记”中(Franklin,2009:76)。慧骃对“种族”纯洁性的执拗,与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的“教派成员的排他性‘种姓自负’”①见Steven M.Wish.2001.Animal Rights[OL].http://www.britannica.com/topic/animal-rights,accessed 6/8/2016.(韦伯,2013:213)不谋而合,只是慧骃的“种族自负”的排斥性更为明显,而且认定同类的准则是慧骃的“理性”而不是加入同一教派。
聂珍钊曾指出:“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社会里就必然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聂珍钊,2010:19)。然而,如果一个个体无法置入社会的伦理秩序内呢?如何能受到伦理规则的约束?在慧骃国这一稳固的伦理秩序社会中,具有一定理性,但是不能完全依照理性行事的人类代表格列佛,无法得到适当的定位,他的“流动型”使他成为慧骃世界的异数。毕竟,他是有理性的野胡?还是野蛮化的慧骃?这些问题无解。他落在慧骃与野胡二元对立的真空中,无法进退,无法安置。最终按照慧骃的“基于纯粹理性的种族伦理不可破坏性”原则,格列佛成为颠覆和潜在破坏者的代名词,结果只能被驱逐。
慧骃的纯粹理性被深深地烙上启蒙时期唯理主义的烙印。这一理论代表学者笛卡尔认为,所有知识体系都可以用理性推导出来,并能得到对世界真实性的认识;同时,作为天赋观念论者,他认为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和真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源于天赋。这种天赋的理性使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上帝的全能性和神圣性。
4.格列佛与野胡:理性定义人类?
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格列佛为何要使用他认为是同类的野胡呢?这需要先厘清格列佛与野胡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书中,作者在外貌、来源、本性三方面暗示和强调了野胡与人类的“种族同源性”。
首先,在外貌上,格列佛早在第二章已发现野胡这“可恶的畜生竟完完全全是个人的样子”。虽然“它(野胡)的脸真是又扁又宽,塌鼻子,厚嘴唇,大嘴巴。但这些差别在所有野蛮民族的人身上都是很平常的……(Swift,2010:176)”。两者惊人的相似性使格列佛“恐惧和惊讶简直无法形容”(Swift,2010:176)。
其次,在来源上,书中多次暗指野胡来源于人类。在第十二章中,格列佛几乎明示了这一观点:“……那两只据说是许多年前出现在‘慧骃’国一座山上的‘野胡’可能会引起争议;根据那种意见,‘野胡’种就是它俩的后裔,而据我所知,那两只‘野胡’可能就是英国人”(Swift,2010:233)。
最后,在本性上,格列佛多方列举人类恶劣品性的例子与慧骃主人观察到的野胡恶习极为重合。在第六和第七章中,格列佛和慧骃主人的对话集中展现了人类与野胡相同的贪婪、虚荣、势利、狡猾、阴险、淫荡、懒惰等恶习。而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现在第八章。格列佛在河中洗澡时,一只母野胡将之当成自己的同类,进而“对我(格列佛)产生了爱慕之情”(Swift,2010:210),格列佛在受到惊吓之余,“可再也不能否认我浑身上下无处不像一只真正的‘野胡’了”(Swift,2010:210)。
然而,格列佛与野胡的区别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格列佛坚持不肯脱掉衣服,证明了德里达“衣服只适用于人类,是人类的‘固有属性’之一”(Derrida,2002:373)这一论断。另外,格列佛的语言、思考、劳动能力也验证了多位哲学家把人与动物区分开的标志。人类不可能等同于只体现了人性之恶、没有任何理性和语言能力的野胡。
在这个问题上,格列佛却没能用慧骃所称的那“一丁点儿理性”来进行思考分辨——他执着地认定了人类就是野胡,甚至比野胡更低劣。
从第三章最后一句话中格列佛开始称呼自己的同类为“野胡”开始,格列佛“人类”这一物种愈发憎恶——他将人类的恶与野胡的恶等同,继而将人与野胡的本质等同:“当我想起我的家人、朋友、同胞或者整个人类的时候,我认为不论从形体还是从性情上看,他们还确实是‘野胡’”(Swift,2010:219)。这使他产生严重的自厌情绪:“有时我碰巧在湖中或者喷泉旁看到自己的影子,恐惧、讨厌得只能把脸别过一边去,觉得自己的样子丑不忍睹……”(Swift,2010:219)。
出于这种强烈的厌恶,格列佛只想离开他的族类,融入慧骃的社会,“我在这个国家虽然还不到一年,却已经对它的居民非常热爱和尊敬了,拿定主意永不再回到人类中,而要在这些可敬的‘慧骃’中间度过我的余生……”(Swift,2010:202)。于是,格列佛做出了他的“种族选择”(Ethical Selection):以绝对理性为基准将自己与慧骃种族属性趋同,与人类进行伦理切割。
那么如何与同类切割呢?格列佛的途径是:使用野胡。通过对野胡的剥皮,榨油,使用野胡皮和毛发等行为,格列佛从心理上和伦理上摈弃了自己的种族,试图成为慧骃版万物链中具有绝对理性的慧骃之下,拥有些许理性的有提高潜质的“类慧骃”生物。这样,根据理性的有无和多少决定权力大小的唯理论思维,从而使格列佛对于野胡(及人类)拥有绝对的道德和权力优势,并切断了他们之间拥有伦理关系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慧骃对其他族类生物的看法,是有理性的人类对无理性的动物的理念的投射。在这里,借助格列佛对待他认为是同类的“野胡”的方式,作者将这一看似合理,实则违反了人类伦理禁忌的举动呈现出来,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哲学问题:理性是否是定义人类伦理归属的唯一标准?
5.理性、伦理秩序与原罪
第十一和十二章描述了格列佛被驱逐,回到人类社会的过程。而彼得罗船长解救格列佛这部分的描写尤其耐人寻味。格列佛千方百计想要逃离人类,却总是被彼得罗船长所挽留。在这一叙事过程中,彼得罗船长展现了一个有礼、仁慈、慷慨的欧洲人形象,而相比之下,格列佛出于憎恶野胡的心理处处拒绝,不禁令人觉得其不合时宜,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如格列佛要求从他的小船上拿些东西来吃,船长立刻叫人拿来了一只鸡和美酒;当格列佛想要泅水逃走时,船长阻止了他的自杀行为,十分诚恳地问其原因,并慷慨提供各种方便和帮助;格列佛不想接触任何与野胡相关的东西,船长体贴地拿新衬衣,新用具给他,等等。无论格列佛如何无礼对待他,船长还是和善地对待格列佛,提供住所,给他建议,并最终将格列佛安全送回家。
船长展现的特质其实与格列佛所憎恶的野胡本性有天壤之别。实际上,船长展示的仁慈和友爱并不亚于慧骃。然而,这并不妨碍格列佛在肯定船长豪爽、有礼、诚恳等优点的同时,还始终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略有几分理性的动物”(Swift,2010:226),并且对人类的观感不仅没有改观,甚至更为厌恶,在第十一章近结尾处,当船长“诱使我来到门口,我发现(对人类的)恐惧已经逐渐减少了,可仇恨和鄙视似乎有了增长(Swift,2010:228)”。
为何在感受到了船长的仁慈之后,格列佛反而更加憎恨人类呢?答案很明显,格列佛认为通过慧骃的教导,自己已拥有了普通野胡所没有的理性和认知上的能力,如识别“骄傲(这)一恶”(Swift,2010:234)的能力,从而高人一等,因此他的态度是傲慢的、俯视的、如同主人般高高在上的。更重要的,这还折射了格列佛害怕沦落到万物链低层的恐惧——慧骃国中被自己宰割的野胡变成自己的妻子、子女、邻人,那是否代表自己也是野胡?因此,格列佛否认了这种伦理关系,并一再在提及人类时使用“动物”之类的词,如,他时刻“担心他(邻居)用牙齿或爪子来伤我”(Swift,2010:234),他还要“教导我自己家里的那几只‘野胡’直到它们都培养成顺良的动物”(Swift,2010:234)。格列佛反复在提醒读者,自己与人类这种生物在种族上有着根本不同的。他保持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只是出于恐惧自己会变成动物的可能性。因为,动物意味着在万物链中的伦理地位处于全然的被使用的“物”的状态,他看似不正常的行为是与人类在种族伦理上进行切割,根本上反映了自然界伦理身份高低所标识的等级和权力意识。
6.作者的最终意图
斯威夫特对各教派的纷争深恶痛绝,认为那玷污了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和一致性。但是作为一名保守的英国国教牧师,他对于上帝的存在是极为敬畏的,人类切不可因为自己的小聪明,就以为可以和上帝一样神圣,从而变得骄傲自负。他在“一封写给新入神职的年轻绅士的信”中,谈到“我们的救世主……并没有赋予我们除了现在拥有的其他能力”(Swift,1973:485),并“最真诚地建议(年轻人)在布道中千万不要想法去卖弄机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Swift,1973:479)。
在理性方面,作者显然认为,格列佛认定理性能决定伦理归属这一点是荒谬可笑的。如果理性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标准,那么刚出生的婴儿,和智力有障碍的人是人类还是动物?文中理性至上的格列佛回到人类社会后无法定义自己的伦理身份,陷入伦理关系混淆的漩涡中,最终无法融入任何社会。这将斯威夫特的意图十分明了地摆出来:他对启蒙时期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思想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唯理学者们“对人类本性潜力持不切实际的观念,期望人类可以以某种方式超越自己的局限性”(Monk,1973:635),这样注定失败的尝试只会使“尔等憎恨人类”(Swift,1973:586),并导致严重问题。
当然,斯威夫特并非否定理性,他只是认定人的理性只有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埃伦普赖斯(Irvin Ehrenpreis)曾说“斯威夫特希望人类尽可能地有理性,并相信宗教才能使人类变成这样,而理性会最终引向上帝的神启”,“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一个理性的人,理性会使人信仰基督教,这两种天赋是和谐一致,并必定会相互受益的”(Ehrenpreis,1957:894)。蒙克(Samuel Holt Monk)也曾指出的,斯威夫特认为“当一个人并不是作为上帝的自由的道德代理去思考,去行动,去感受,……他就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人性(Monk,1973:634)”从这方面来看,格列佛妄想只从慧骃身上学习理性,使自己自我完善,是不可能的,因为慧骃作为“自然神论者想要在上帝天启之外建立一个理性的系统是邪恶和荒谬的”(Ehrenpreis,1957:892)。
7.结语
从格列佛对纯粹理性的向往,却最终触犯了“使用”同类的伦理禁忌可以看出——绝对理性只会导致人性的堕落。格列佛最后自以为获得更多知识和理性而骄傲,妄图挑战上帝,否定“建立在禁忌基础上的伦理秩序”(聂珍钊,2010:18),坚持用理性来定义种族归属,造成了他最终的伦理悲剧。从这个意义来看,第四卷对人类理性的尖锐嘲讽和对人类伦理身份的颠覆性反问,瓦解了人类/动物,理性/非理性,甚至对/错等二元化对立概念,有着现代主义式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