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
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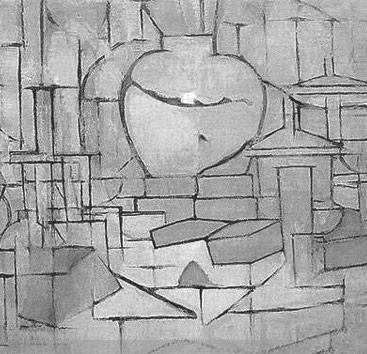
深夜食堂
从安倍夜郎漫画里出来的食堂,
在霓虹的暗处,背街小巷,
烹饪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的真相。
猫饭、茶泡饭、红色香肠、酱油炒面,
松 冈锭司,山下敦弘,及川拓郎,登坂琢磨,小林圣太郎,
这些眼花缭乱的名字,
就是人间烟火。
我有点居心不良,一直追,
企图甄别食堂里的成份与阶级。
结果是所有的装模作样,
在朴素面前不堪一击。
终于明白了那些面膜和画皮,
走不进深夜的食堂,
夜的手伸过来,近乎于残忍,
一一剥离。
卸 下
卸下面具,
卸下身上多余的标签,赤裸裸。
南河苑东窗无事从不生非,
灯红与酒绿,限高三米,
爬不上我的阁楼。
南窗的玻璃捅不破,不是纸,
窗外四季郁葱,总有新叶翠绿,
滴落温婉的言情。
真正的与世无争就是突围,
突出四面八方的围剿,
清心,寡欲。
阅人无数不是浪得虚名,
名利场上的格斗,最终不过是,
伤痕累累,体无完肤。
把所有看重的都放下,就是轻,
轻松谈笑,轻松说爱,
轻轻松松面对所有。
任何时候都不要咬牙切齿,
清淡一杯茶,可以润肺明目,
看天天蓝,看云云白。
半糖牛奶
早晚一杯牛奶,加半糖,
半糖有一种弹性入侵,
依赖、纠结、适可,想入非非,
这是很重要的尺度。
我用一个花甲的味觉,
调试了这个口感,
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比如人生这个大词其实很小,
与品格、性情毫无关系,
仅仅是深一脚、浅一脚,
最后走成自己的路。
鸿鹄之志和高屋建瓴都很可疑,
有點像牛奶满满加糖,
失去弹性的自信就是糊涂,
还自以为是。别人看一眼就腻,
反胃,甚至痉挛。
我一直拒绝满糖和不加糖,
对半糖情有独钟。
半是状态,半是把握,
半是清晰与含混之间的自留地,
深浅自己拿捏,游刃有余。
流 浪 猫
它的身世可疑。
它的形迹可疑。
它流浪,在暗处与鼠类勾肩,
行走阴湿的下水道。
我对它的怜悯最初是一条鱼,
鱼刺被它当成剑,起舞于月黑风高。
我继续在它出没的角落布施,
牛奶、猫粮、无刺的虾米,
希望它立地成佛。
我不能与它对话,可以宽恕,
我看见石头流出眼泪。
没有家的滋味我也曾有过,
背井离乡,或者,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
但流浪不是成为流氓的理由。
街边、野外、灌木丛物种复杂,
从生到死留下好名声,
无计其数。比如那只流浪狗,
轻脚轻爪,从不伤人。
夜有所梦
夜有所梦。
据说春梦里的对象很陌生,
对此我将信将疑,但是很多人认同。
我的梦不在春天,没有斑斓,
夏、秋、冬里也没有春。
我梦里都是神出鬼没,
那天神对我说,
赐你万能的权力,诅咒你敌人。
我在手机上翻检所有的名录,
都笑容可掬,没有。
鬼又过来,拿一贴索命符,
去把你身边的小人带来。
我省略了学生时代,从职场过滤,
也找不到可以送贴的人。
世界很大分不清子丑寅卯,
习惯忽冷忽热的面具,
看淡渐行渐远的背影。
与人过招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轻易指认敌人和小人,
自己就小了。
如果我不幸光荣受伤,也要宽恕,
让我的血淡化成他的泪,
以泪洗面,换回以前的模样。
无 比
我经常使用这个程度副词,
省略前戏和后缀,节制过度的热烈,
它不孤独,语义能够抵达无限。
我的无限程度都是限量版,
唯一。在唯一里无限放大,
像夜里偷袭而来的梦,重复、极端,
与现实相距两颗星辰。
这几乎是无法丈量的距离,
比我知道的天涯和咫尺,更残忍。
始终不贰。认定无比就是无比,
一条路走到黑,白也是黑,
黑得根深蒂固,一目了然。
我对厌倦情有独钟
厌倦时刻分明一日三餐。
厌倦早出晚归两点一线。
厌倦书桌前半真半假的抒情。
厌倦阳台上一丝不苟的色彩。
厌倦甜言蜜语。
厌倦风花雪月。
厌倦瓜熟蒂落。
厌倦水到渠成。
厌倦阴影虚设的清凉。
厌倦落叶铺满的哀叹。
厌倦口蜜腹剑钩心斗角。
厌倦虚情假意心照不宣。
我对厌倦情有独钟,
循规蹈矩顺理成章按部就班,
让我迟钝、萎靡、不堪,
形同行尸走肉。
厌倦,厌倦,厌倦流连忘返,
把过去的每一寸光阴,
清空。留一块旧年的伤疤,
独自刀耕火种。
如果要我充当凶手
从海里打捞的大牌不分主次。
鲍鱼、生蚝、刀鱼、海胆,悉数登场,
虾蟹不在演员表上。
此刻我正襟危坐,心生惊悸,
只好躲在杯盏的后面,
灌醉自己。我的表演比专业更专业,
始终举不起一双竹筷。
好想把筷子扔进海里长出海藻,
海里多一尺屏障,
桌上少几个演员。
我知道那些大牌都是狠角色,
身后的海不会视而不见,
总有一天兴风作浪。
记起释道海师父对我说,
忘其耳目。这对于我实在太难,
我正在参与一次集体杀戮,
听见了海的哭,由远而近。
如果生物链上必须要我充当凶手,
我也不会选择海,宁愿
投身于海成为长出刀刺的礁石,
网来网破,船不能肆无忌惮。
海洋里的生命自由、鲜活,
风平浪静,蔚蓝,一直蔚蓝。
不着一字
我珍惜所有的倒影,
一如珍惜它站立的真实。
倒影倒下的误读是委屈自己,
我错了。倒影没有错,
倒影身不由己。
背影渐行渐远,我在看,
一尺和一千尺之外可以确定,
我不言语不着一字。
隔 空
很南的南方,
与西南构成一个死角。
我不喜欢北方,所以北方的雨雪与雾霾,
胡同与四合庭院,冰糖葫芦,
与我没有关系,没有惦记。
而珠江的三角,每个角都是死角,
都有悄然出生入死的感动。
就 像蛰伏的海龟,在礁石的缝隙里与世隔绝,
深居简出。
我居然能够隔空看见这个死角,
与我的起承转合如此匹配,
水系饱满,草木欣荣。
我的老爷子
老爷子最早在水上行走,
从重庆到汉口,两点一线,
巫山云雨和两岸猿声,都抛在身后。
我无法想象那些水运的枪支,
如何安全抵达。
万恶的旧社会的那些枪口,
最后对准了谁?老爷子的水性,
就是把弟妹带大,养家糊口。
很早失去了父亲的我的老爺子,
身边七个兄弟姊妹,后来,
还有了我哥我姐和我,
以及孙子、曾孙,连绵不绝。
这是一个兵工厂的家族,
老爷子名副其实做了老大,
稳坐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
我的老爷子从来不问天上的风云,
只管地上的烟火,拖儿带女,
踉踉跄跄走进新的社会和时代,
他人生的信条就是过日子,
平安是福。
以前是他说经常梦见我,
我无动于衷。现在是我梦见他,
不敢给他说我的梦。
害怕说出来,他心满意足,
就走了。必须要他牵挂,
我是他的幺儿,不顶嘴,不流泪,
与他相约,百年好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