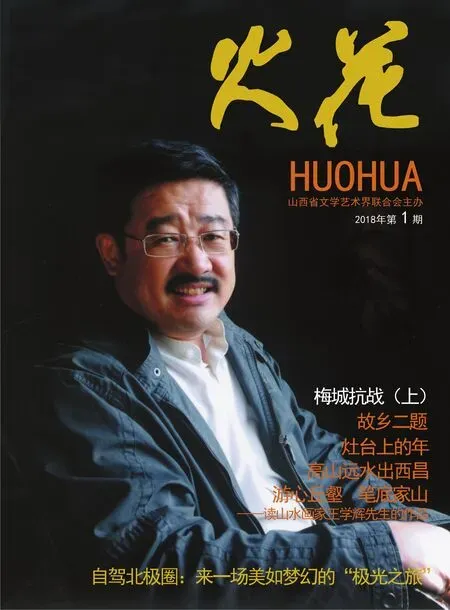村庄的记忆
张呈明
村庄是漂浮在大地上的一叶浮萍,人们终将会失去它。
我无数次游走于村庄的大街小巷,或走出村子从远方回望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故土,却怎么也还原不了村庄最初的模样。
我寄希望于梦中,反复出现在梦境里的依然还是村西北角的那片蒹葭苍苍的苇坑,里面常常会飞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鸟儿,抑或传出这样或者那样奇怪的声音,总会让人感觉到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秘密,只有四季不断的风儿知晓。
村子总共有三条东西大街,两条南北大街,坑洼不平的土路每逢雨天总会泥泞不堪。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是这个村庄的血管,连接着五、六百户人家。炊烟在村庄的上空袅袅升起,起初每家的烟囱冒出的炊烟或粗或细、或浓或淡、泾渭分明。升到一定的高度便缠缠绕绕、不分彼此,最终成了村庄的魂魄,慢慢飘向遥远的天际,去寻找远古时期的影子。炊烟总是朝发夕至,夜静之时方可安静下来。村庄唯一不变的恰恰就是这缥缈的炊烟,炊烟可以自由散去,但是它的根却散不去。它的根深深地植入了大地宽厚的胸怀里,植入了乡村的每一座小院里,每一座灶台里,每一道砖缝里。村庄因了这缠缠绕绕的炊烟才会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
村庄不断有熟悉的面孔离去,而又不断有新的面孔加入进来。犹如村头那棵参天的白杨树的叶子,总会有一些老的叶子落下,紧接着一些新绿的嫩叶萌生出来。根在哪里?在乡村。乡村是人们的根,而大地则是每一个人永远的归宿。
村庄的历史在哪里?在老人们那漏风的嘴巴里和珍藏了不知多少代的那本发黄了的家谱里,在荒野中残缺的碑文里。
多少年过去了,你再回首看看村庄,会发现,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但似乎又早已面目全非。
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白天想破脑袋的问题,一到了寂静的深夜,进入沉寂的梦乡之后,过去的一切就会清晰地再现出来。我诚恐诚惶地在时间的隧道里独行,曾一度怀疑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我早已不属于这个世界,眼前的这一切都是幻象或者梦境?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白天一个世界,而夜晚却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半睡半醒之间我不敢确定,即使已经感觉到就要醒来时仍不敢睁开双眼。我曾经试着睁开了眼睛,后果是一切都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任凭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村庄的人们朴实而善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只有冬季是人们休整的假期。其它的季节里,总是在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劳作着。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了地,任凭露水打湿裤腿和鞋子。三夏或三秋大忙季节几乎就整天不回家,中午就着咸菜啃点带来的煎饼或者馒头,或种或收或锄草,反正不闲着。待到落日的余晖映红白马河水,依然还会有不少的庄稼汉劳作在田野深处。他们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像侍弄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打理着庄稼,让汗水湿透最后一片衣角。此刻,庄稼地深处传来“咯咯”的声音,那是老野鸡在召唤贪玩的儿女们。确有这样的庄稼人,他们可以听得到高粱、玉米、小麦拔节的声音,却听不到家人催促他们回家的呼唤。
地里的活干完了,离村庄就近了。待到暮色四合,一缕缕炊烟升到半空中,而后在傍晚的微风中弥漫开来的时候,村庄便浸润在一片温馨的氛围之中。劳累了一天的庄稼汉扛着农具,牵着牛,或撵着一群羊,吸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听着鸡鸣、狗叫,伴着谁家母亲呼唤贪玩迟归孩童的声音,人便醉了。
他们春天播下希望,然后用汗水浇灌着嗷嗷待哺的土地。待到金秋时节,硕果累累,一年的辛苦顿时化作了甜蜜的回味。庄稼总会因主人的付出不同生出三六九等来,于是便有了那句农谚:“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俗话说:“孩子自己的好,庄稼人家的好。”这个时候会有极少数不争气的人,趁黑夜悄悄把手伸进邻家的田里。但是真正的庄稼汉会悄悄咽下遗憾,暗暗攥紧拳头,把希望寄托于来年。
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身上总会带着永远也磨灭不去的印记,那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是给了他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村庄。尽管有不少人用尽了浑身的解数,甚至不惜重金想洗去曾是农村人的印记,但是一切终归于徒劳。
哪个人没有自己的故乡?是故乡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即使无数次走出去,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依然会固执地认为故乡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而他的一切都是由这片故土衍生出来的。
村里总会有几棵古老的树木,也许是老槐树,也许是皂角树,也许是杨柳松柏之类的,虽然没有楠木那么金贵,但是生长到这个年岁了,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棵树的概念。苍劲的枝干布满了疤痕,一如老人粗糙的手掌。枝干上不知源于何时被系上了红布条,虽然风吹日晒早就褪了色,但这却是村庄召唤游子的经幡。无论你走多远,无论官做得多大,老了总会被召回村庄来。村庄记得,老树也记得。不管是在天南的,地北的,当官的,还是经商的,混得光鲜的会衣锦还乡,混不转的也会感叹幸好还有个家,无论贫贱富贵,故乡总会像母亲那样宽厚慈爱地接纳他。每逢清明寒食节,总会有人赶回来祭扫一下祖坟,看望一下老宅,认一下族亲。离开村庄时还是青涩的少年或者血气方刚的青年,回到村庄时一如这迟暮的老树垂垂已老矣。即使是化作一抔灰,也要装到四四方方的木盒子里,被儿孙们抱回故土,抱回村庄。睡在故乡的泥土里,就等于睡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踏实、惬意。
我喜欢一个人穿行在村庄与村庄之间,尤其是喜欢去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庄。每看到一处老宅子,都会激动不已。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骑行来到位于邹城市西南方向三十公里的上九山村。那个时候的上九山村还没有开发建设,一切都是原生态。幽深幽深的巷子,层层叠叠的石墙,摇摇欲坠的石屋,躺在荒草之中的石磨、石碾。望着眼前的一切,我把自己想象成这个村子里的一员。我在蜿蜒曲折的街巷里寻找逝去的岁月,在长满野草的石缝里倾听古村的倾诉。
每一次从别的村庄回来,便对自己的村庄增添几分的眷恋。这种感觉抑或叫做情愫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我把这一切归于恋家的情结。每一次走出这个村庄的时候,分明有一种力量在牵扯着我。
走遍千里万里,最令我牵肠挂肚的还是生我养我的村庄。不管这片土地肥沃还是贫瘠,无论村庄富裕还是贫穷,它早已与我血脉相连。
不敢想象,若干年后,当这座古老的村庄化为一片废墟抑或烟波浩渺的泽国之时,我们的根将扎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