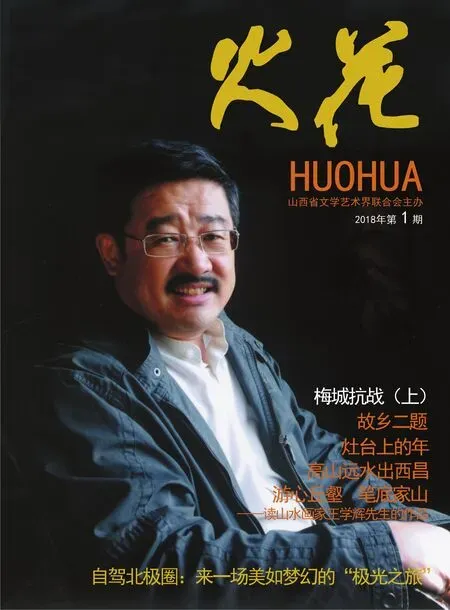梦母三章
何尤之
冷梦
您的脚步完成了人生的丈量,我归乡的路便在这里戛然而止。如同一座湍急之上的桥,突然塌陷。您纵身一跃,乘鹤而去。我站在悬崖边,如同走失,脚下的汹涌让我驻足迷茫。从此我守着悬崖,任由思绪追着您,日夜兼程。
就在某个夜。果然,我追上了您。
那个日子,酷热,风低。您要来看我。我是否答应了,答案已飘落。母子间何需问答,一切皆于无声处。从我嗷嗷待哺,答案便在。我的眼,在突然间,在梦里有了灵魂,飞越城市,穿越乡野,跨越水界,思越天际。我分明看见,您从某个飘摇的地方,向我而来。瘦弱的身影,年迈的双腿,只有信念,没有蹒跚,径直地向着有我的方向走来。
梦无章法,不可思议。有章法的不是梦,是被思维驾驭了的现实。
这个杂乱的梦,让我伤口添盐,负债累累,笔直地从山崖坠落。
莫名地,在您向我而来时,我却走了。我被一个莫名的人叫走,去了一个莫名的地方。
至今我都想不起来,那个莫名的地方是哪,更不知所去何为。有所为的是梦,梦导演了一幕悲剧,安排我去了那个地方,乃至未能守着您的到来。无法追责于梦,我空留长恨对天仰哭。
那个莫名的人消失后,我才莫名地回到了家。梦用最残酷的情节摧残我,鞭笞我,蹂躏我。您倒在床前的地上,空调疯狂地吹着。您被冻得满脸风霜,失去了知觉。我一个男儿,以无法想象的巨大悲哀,嚎哭着。撕心裂肺!柔肠寸断!我惊呼着将您抱到床上。对不起,对不起——鞭炮连珠的歉疚未能换来您的片言只语。
我哭着说,您不必守在这里,您可以去隔壁人家小憩。您缄默无语。但我知道您的答案。隔壁是别人的家,儿子的家是您永远的家。
我匍伏在地上,泪溅衣襟,哭到泪干。
您一直默然。然后在我的梦醒时分悄然消逝。
醒来时,我的脸上挂满了泪。空调仍在吹着,我的双脚很冷。仰目望顶,梦的皮鞭顽固地拷打着我的心魂,激起翩翩思绪。
犹记读书时,您的笑脸温馨了一个少年的整个孩提;
犹记大学时,您的笑脸温暖了一个青年的每次归程;
犹记工作时,您的笑脸温毅了一个中年的坚强步伐。
而如今,骤然之间,温已不在,留下一个个冷梦。如同一场寒冬,固执地覆盖着我的心野。偶尔落雪,或冬雨,在原野上蕴育,蕴育着一个又一个如春的暖忆。
冷梦千回,寻觅暖暖的您,不言悔,愿追随。
梦雨
在您的身后,梦雨纷纷。丝丝缕缕,不是春天。冷冷的雨点,呼啸而来,预示着一场严寒不期而至。
心若在,梦便在。烟尘滚滚,薄暮冥冥。您的背影,慢慢回过身来。我又触到了温暖,听到了叮咛,见到了光辉。
有梦的时光,一切依然如故。一样的风,一样的雨,席卷了我的梦境。养老院的温情,白发间的疲惫,少许时的忿恚,寂寥间的忧伤,踏着一个个夜色,搅动我的情思。我们挽手而坐,诉说往事。忆起青瘦的年月,酸楚乘风去,多少烟雨笑谈中。劳累一生的重负,凝结成一声迷茫的感叹。而今轮椅上承载的,不只是您的晚年,还有儿女效颦学步的青涩时光。
未来无法感知,任谁如此。养老院不该是您最后的归宿,却是您没有选择的选择。凄凄然,裹一身病痛,拖半身瘫痪,倚着别人的伺候,流落他乡,深深浅浅地伴着残烛。
我的愧痛,此生不赎。
我在漂泊的缝隙与您相见,不露一丝挣扎的痕迹。您是,我亦是。
您对我说,儿,我想回吴杨,看看我那老房子。
我对您说,老房子拆了,您的家被拆了。
这样的对话,被重复了若干次。谎言,如一根银针,扎麻了我的穴位,而我又能奈何?残缺的家园,残缺的您,难以重现旧时的和谐,您亦能奈何?我很沉重,有汗如雨。失了家园的悲壮,我能揣度。回家的情思,如小小的球儿,在您的心里弹起而又落下。家在三十里外,那个叫吴杨的村庄,并不遥远,竟是千山万水。熟稔于心的家园,清香芬芳的绿野,还有阳光的味道,小河的潺动,从此收藏进了您的历史。想家的忧伤,如一把工刀,一撇一捺,书写着您的痛,镌刻千疮百孔。
最后的心愿,没有心愿的心愿。直到您生命垂谢,故园接纳了您,永远。
梦雨缤纷,乘隙而来。雨浇灌着心田,一些心事在生须发芽。
梦回
村庄在斜阳中倾斜,斜阳在梦中倾斜。
树在倾斜,路在倾斜,老宅在倾斜。整个村庄在倾斜。纤手一般瘦弱的风,轻轻地将整个村庄撬起,村庄便失去了根。
我走在无根的村庄里,立足不稳。踉跄着,我来到您的门前。
以为,一如以往,您会敞着门,抱着拐杖,独坐床沿边,默默地数着日子。
以为,一如以往,我再偎着您,欲说还休,只道西风瘦,轻轻地叫一声妈。
老宅老矣,已荡然无存。您去了何方,我仰望西天。太阳变得炽热,云朵苍白如雪。门前的泡桐突然间拔节,树冠昂然向上。屋后的河流几时干涸,滴水不剩。圈里的肥猪撞墙而逃,撒开腿狂奔。母鸡骤然展翅高飞,掠过我的头顶。不远处的几个人,远远地指着我,在说些什么,却完全不问我是谁。光秃秃的老宅基上,我是一棵移栽过来的枯树,不合时宜地茫然四顾。
我的身体开始倾斜,脚下的土在松动,像有蚯蚓在铲我的跟。我挪步,却找不到平地可以息脚。四处张望,分明是旧时的面孔,陌生而惨淡。村庄褪了秀色,河水浑浊不堪,小路被谁蹂躏得坎坷崎岖。
我的村庄,我的童年,跟着您去了未知的何方。捧一把泥土,重重地嗅。拂拂手,泥土扬落。没有您的味道,泥土便没了特质。
一切因您而变。是谁说过,娘在,家就在!如今您在何方,我漂浮在没有航灯的夜晚。没有娘的故乡,我瑟瑟发抖,在倾斜中难以定稳。
身体在倾斜,一直倾斜,倾斜到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忽然倾出了梦境。半个身子悬在床沿,一身的汗湿透衣被。
沿着梦往回走,村庄、河路,以及那些面孔,都找了回来。
而您,我却再找不回来。
连同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