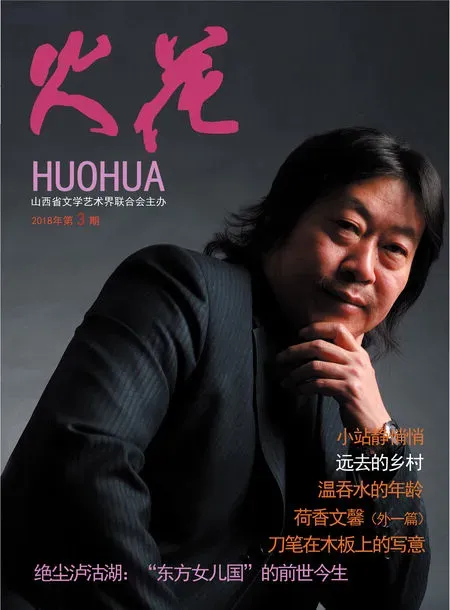在路上
——大时代小人物
王春旭
大日子
我太爷(曾祖父)那个年代,我们这里被称为“伪满洲国”。日本对我们这个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方式之一就是种植罂粟(俗称大烟,日译名阿片)。
人们发现可以将面粉掺进罂粟里多卖些钱,于是面粉的价格随之水涨船高。那一年,我太爷除了种植罂粟,还种了小麦,恰巧赶上风调雨顺,我太爷赚大了。富起来的太爷买了几十亩地,拴了三挂车。
从此家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左邻右舍纷纷靠拢来,有帮忙种地的,有帮忙赶车的,还有帮忙做饭的。那时候还不涉及工钱,帮忙干活就是混个饱饭吃。主人不懂耀武扬威,佣人也无需低三下四,当然也许就连“主人”“佣人”这样的词汇都不曾在彼此的脑海里出现过。我就亲耳听我太奶(曾祖母)说过,她看到车老板儿(帮忙赶车的人)家的儿子七八岁了,还光着屁股,就用自己的包袱皮儿给那孩子做了条短裤。
我小的时候,我太奶经常给我讲她们过大日子时候的事情。她说那时候偶尔改善伙食,煮很多鸡蛋,每人分到几个,她从孩子们手中匀出几个,回娘家带上。小脚太奶步行十多里路回娘家,不得不走走歇歇。大桥头有算卦的,一次她歇脚的时候,拿出两个鸡蛋,让瞎子给她孙子,也就是我父亲算了一卦。我父亲鼻梁上有一个大大的痣,算卦的说我父亲命不太好,多舛吧。我太奶讲这些的时候,慢声慢语,娓娓道来,眼神是悠悠的,神态是安详的,想必这就是大日子女主人的仪容吧。
我爷爷
我奶奶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她嫁给了我爷爷。我爷爷是一个有担当的丈夫,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这一点,从他学医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出来。起因是我父亲的弟弟,两三岁的年龄上病死了,为此我奶奶终日郁郁寡欢,终于有天晚上病倒了,我爷爷大晚上的没能请动医生。
“你爷爷三十七岁开始学医”,这句话,我父亲多次说起。说这话时,父亲的语调是铿锵有力的。我三十二岁那年,就读全日制研究生,当时我儿子三岁。对此,很多人都问过我,“你怎么那么有毅力?”我想,冥冥之中我爷爷已经做给我看了。
家里有很多本药书,爷爷看药书的时候,带着老花镜,镜子的两条腿用细绳连接着。爷爷还经常在煤油灯下抄写药书,也许那药书是借来的吧,或者是为了更好地记住。家里还有个大药橱,里面有杆很小很小的秤,配药用的。爷爷配药的时候,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小秤,一边看着药书一边不厌其烦地一会儿添秤一会儿减秤。
爷爷的医术如何呢?听父亲说,爷爷的一个朋友,也是患者,坐在我家炕上聊天,“你真有两下子,我这病吃了多少药都没见好,到你这儿就全好了。”爷爷在炕沿儿上磕了磕烟袋,“该着你出灾儿了。”
我有一个干大姑,关于她,还有一个笑料。那时爷爷已经不在了,干大姑仍旧年年都来给奶奶过生日。六七岁的我正在院子里玩,一抬头看到干大姑已经走到大门口,冲着屋子里喊“我干大姑来了——我干大姑来了——”,奶奶迈着小脚一边往外走一边笑着骂我“小骚妮子”,我无比委屈,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干大姑则哈哈笑着,“本来就是干的嘛。”
说说我这个干大姑的由来,那年干大姑得了一种病,找了很多大夫,都没有看好,遭了数不清的罪。谁料到了我爷爷这儿,药到病除。于是她执意要认我爷爷做干爹,以示报恩。她是蒙古族人,比较认亲。她跟我母亲的性格相似,都很外向。两家人往来比较密切。
那时候,我们村浇地,水要流经上村,上村是蒙古族人聚集地,我干大姑就住在那个村。我们村是汉族人聚集地,两村多多少少有些小矛盾,致使我们村每年浇地都不太顺利。不知从哪年起,队长开始安排我爷爷看水渠,从此浇地彻底顺畅。那时候集体劳动挣工分,看水渠是个比较轻巧的劳动,村里人羡慕地说“啥人啥命”。直到今天,我们村一些老年人还会说起这件事,为我爷爷那传遍十里八村的声望而赞叹。
印象中,爷爷穿件白衬衣,骑着自行车,早上走了,晚上回来。经常地,爷爷变魔术一般从兜里掏出一个烧饼,给他的孙子——我的大弟弟,那时候小弟弟还没有出生。大弟弟从爷爷手中接烧饼时,羊从大门外“咩咩”叫着进院了,“圈羊去”,爷爷催我,我只好乖乖地干活去。“爷爷为什么不买两个烧饼呢?”若干年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这件事。也许是爷爷重男轻女吧,也许是手头并不宽裕吧,我倾向于后者。
早出晚归的爷爷,中午饭通常都在患者朋友家里吃,那时候瞧病基本上就是吃顿饭了事,偶尔给个块八角钱。有的等到病好了,专程来我家,送来几斤大米或者稍微罕见的东西。
爷爷在家的日子,家里经常人来人往的。有来瞧病的,有来致谢的,也有来专程聊天的。爷爷去世后,门前冷落鞍马稀。母亲曾就此事问过父亲,父亲答:“朋友是一个人的,亲戚是一家人的。”
文革时期,爷爷被划为富农成分。“成分不济”这四个字,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我二姑、三姑、四姑说过,我大爷(我父亲的大哥)、我父亲说过,我奶奶也说过,跟很多故事开头那句“很久很久以前”异曲同工。我二姑说时,她很知足眼前的光景,有股子扬眉吐气的味道。我三姑跟二姑不同,她从来不怨具体的个人,她觉得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我四姑愤愤不平地,曾经她的同学喊她“富农羔子”,她赶上了恢复高考,考两次没考上。我大爷和我父亲说时,更多的是对自己命运的无限感叹,“成分不济”等同于“时运不济”了。我奶奶说这个词时,说的都是她的儿女们如何受成分连累,而她自己早已忽略不计,她更多的是接受,近似坦然地接受。事实上,因为遭遇被“抄家”,我奶奶得了心脏病。
我爷爷因为成分不济挨批斗,我奶奶让我父亲去给爷爷送饭。我父亲亲眼看到我爷爷在村部的小屋里挨批斗的场景。其实,看到这个场景的,不只我父亲,也有我大爷和我的几个姑姑。毕竟批斗不是一天两天就结束的,而我奶奶让谁送饭是随机决定的。对于我爷爷挨批斗的细节,他们说的少,我也不敢多问。值得一提的是,批斗我爷爷的人,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车老板儿、七八岁还光屁股的小孩子的父亲。
文革后的日子里,我爷爷跟那几个曾经批斗他的人朝夕相处在一个村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里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情,曾经批斗过我爷爷的一个人出殡,我爷爷也加入了抬棺材队伍的行列。在我爷爷那里,过去就永远过去了。
很多人包括我父亲在内都说我爷爷那人“心大”。几多风雨,几多坎坷,心不大也被撑大了啊。
我父亲
那时候交农业税,我们习惯说“交公粮”。我父亲赶着牛车,车上装了几袋子的高粱。到了村部,看到很多户人家都在交公粮。很快,我父亲就交完了。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那么快,父亲说因为我们家的粮食干净、不掺假。这一点,后来我读书住校就理解了,住校生每人都从家里拿小米换饭票,那小米饭类似“八宝饭”,里面什么都有。
我上大学的学费,是我父母亲跟亲戚们借来的。尽管这样,我父亲还是告诉我说,兜里放两三角钱,火车上有人要就给点儿。我很听话,真的就放了两角钱。某个站点,上来一个拄双拐的女人,穿着打扮比我好,尽管我身上穿的、包里带的都是我们家里最上乘的。她上来就唱了一首歌,然后说她家住在小山村,弟弟和妹妹都在上学,父母多病,说得她自己近乎声泪俱下,忽然她大声地说:“给五角的,我祝你旅途愉快!给一元的,我祝你发大财!”我本能的反应是祝福和价钱成正比。但我兜里只有两角钱,还不到她最低额度的祝福。我身边的阿姨看出了我的尴尬,跟我说学生就不用给了。但当时我内心对父亲表示歉疚。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老姑(排行最小的姑姑)考上了大学,那是我们村甚至我们乡镇的第一个大学生。其它村镇的人都议论这件事:“王台子(我们小队的名字)考上大学的,肯定是王国顺(我父亲的名字)的妹妹。”
我父亲跟新中国同龄。他会吹笛子,“东方红”的调子。他喜欢读书,四大名著开篇基本上背下来了。他借书看,也自己买书看,那是吃饭都成问题的年月,他竟然买书,可见他对书的热爱。我老姑考上大学那年,我父亲将他珍藏的书都给我老姑了,我记得有《三国演义》。
漫长的夜晚,我们姐弟三人躺在被窝里,我母亲借着煤油灯的光做针线,我父亲看书。看着看着就笑了,笑出声来,不识字的母亲不理解,“有啥好笑的”,每当这时候,我父亲就将他认为搞笑的部分念给我母亲听。我父亲还将一些简单的字用毛笔写在硬纸板上,放在灯窝(连接着外面灶台的小窗户)里,我母亲做针线时,偶尔抬头看看字。我父亲毛笔字写得尤其好。流行电脑刻印春联之前,左邻右舍都纷纷来找我父亲写春联,毫无疑问这是我父亲的一件荣耀差事。
碰上母亲因辛苦劳累而心情不好时,父亲也免不了挨唠叨,“大过年的,谁家没点儿活啊,搭着功夫儿(时间),费笔费墨,白忙活,没人说你好”,父亲讪讪地“一年不就写一次春联嘛”。有时候父亲正坐在炕上看书,厨房里忙碌的母亲突然歇斯底里地:“看那些书有什么用,能来钱吗,都给你添灶火堂里!”有次我母亲还真拿本书,极力地要添进灶火堂,两人撕撕吧吧地抢一本书。有时候,父亲既没写毛笔字,也没看书,他也难免被埋怨,母亲怒气冲冲地“这个家的日子,到了你这儿,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呢”,父亲坦然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嘛”。
我上大学后,第一个学期寒假回来,千里迢迢背回几本小说,是我从学校图书馆特意为父亲借的,当我兴冲冲地拿给父亲时,他一副疲惫样子,“看那书有啥用啊,我不看书了”。当时父亲正供我们姐弟三人上学,肩上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父亲不是一个标准式的农民。他干农活不地道,经常挨我母亲数落。秋忙季节,我父亲赶着一车庄稼来到场院(用来打谷、晒粮食的场地),问我母亲,“放在哪里”,如此免去一场责怪。
因为亲眼看到我爷爷挨批斗受刺激,我父亲精神一直不是特别好,他经常边走路边嘴里嘟囔着什么,致使他的小孙女都对他怕怕的。他经常晚上睡觉说梦话,梦话千篇一律地说唱式“哎呦我的妈呦——”,后面就听不清唱的什么了,致使别人都睡不好觉。
听我母亲说,我父亲说他种出了三颗最好的庄稼。这里,他指的是我们姐弟三人,都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以前我母亲曾跟我抱怨说,我父亲连一双袜子都没给她买过。其实一直以来,家里的钱都在母亲手里。父亲外出打工那些年,回家也是一分不差地把钱交给母亲。这两年,母亲说父亲变了,开始自己拿钱了,每次取出国家按月给打在卡上的钱,父亲都要揣在自己兜里。看来,父亲真的老了,老得没安全感了。电话里,“你爸赶集经常给我买猪蹄”,母亲兴奋地说。母亲爱吃猪蹄,而父亲吃素多年。年轻时的父亲不爱热闹,也不爱赶集,现在老了,脾气秉性倒变了。
我奶奶以前经常把别人给她过生日送来的糕点,分出一些,让我母亲拿回娘家给我姥姥、姥爷吃;为了增加营养,我母亲每天早上给我奶奶沏鸡蛋水喝,为此有时候我母亲还去别人家赊鸡蛋。这事,父亲说过太多遍了。父亲每次说,母亲都不好意思,嗔怒他“都过去的事了,说它干啥”。父亲的心变得柔软了。
我曾经问父亲“你知足吗”,他响亮地回答“知足”,如同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般。接下来是他如数家珍般地解释:你们仨都挺好,都争气,都有稳定的工作,都住上了楼房,我一点儿都不用惦记;现在种地都是机器了,也不累,种地不用交农业税了,还有补贴;你妈和我自从六十岁开始,按月领补助;“村村通”后,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将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