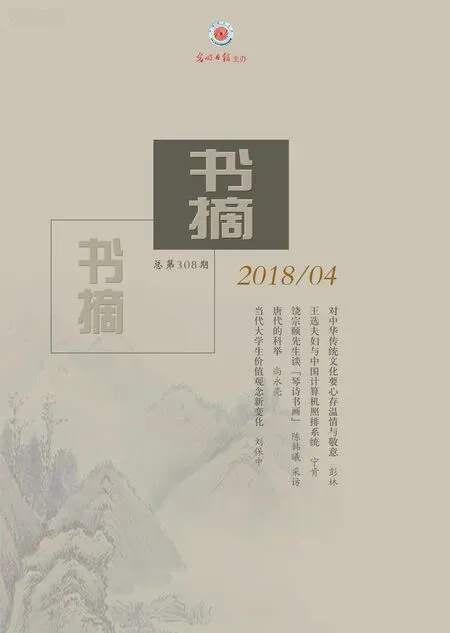记任铭善
☉王元化
任铭善先生,字心叔,江苏如皋双甸人。1913年生,1935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曾师从锺泰、徐昂、夏承焘诸位国学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专攻经学。七七事变后,我们一家从北平逃难到上海,母亲怕我荒废学业,通过老朋友之江教务长胡鲁声教授请任先生来教我中文,以准备报考大学。我每周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时课。那时任先生住在忆定盘路的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是战后匆忙建起来的一排排两层的简易楼房。当时租界因不断有逃难来的人涌入,人口骤增,房商新建了不少这种所谓新式里弄的简便楼房,任先生就住在一座楼房的底层。
我第一次去拜访任先生,看见他穿着一件长袍,个子不高,但两眼有光,神情肃然。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很直率,决不为了敷衍别人而随声附和。他是很讲原则的,上课时,从不跟我讲闲话。尽管任先生肃若秋霜,对人对己都有严格的要求,但他从未让人望而生畏,感到凛然不可亲近。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但他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三门课程。《说文解字》依序按照部首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他讲授了《内篇》和《外篇》,《杂篇》则没有时间教了;《世说新语》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我除了每周三次到忆定盘路他家里去上课外,有时他还要我到慈淑大楼去旁听他在之江大学的讲课。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我在他家上课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
任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居室只有几件木制家具和一把作为休息用的扶手藤椅,此外别无长物。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见他端坐在书桌前,孜孜不倦地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
就记忆所及,任先生曾对我有过几次批评,却从来没有对我表扬过。这不能怪他严厉,那时我正忙于抗日救亡工作,对知识学问的价值和意义还不理解。以致去任先生那里上课常常迟到,有时甚至缺席。任先生极为生气,责我自由散漫。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去上课,他从忆定盘路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久候不至”,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请假,并将此事向我母亲诉说。我回到家中,看到便条,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心中有些惶然,却并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倒是多年以后,每一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发音洪亮的嗓音,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使我愧疚,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社会阅历浅,却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也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出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了,只是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看你的文章气势这样急促,这样是不好的。”我听了不禁感到浇了一盆冷水,心想任先生对我的要求未免太高了。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这些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但他们写得确实好,使人从中感到一股清新不迫的韵味。我还记得一份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加上了圈点以示褒奖。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当时我还把自己正在阅读的金圣叹批杜诗请教他。他叫我不要读,说:“金批割裂了原文的气势,这是不好的。”“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有范畴。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撰文谈到,在西方很难找到和“气”相对应的字,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气”这个概念却存在于各个领域。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之前就已存在了。王充《率性篇》所举“齐舒缓、秦慢易、楚急促、燕戆投”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一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二是因龙泉哥窑遗址遭到破坏,他曾提出过呼吁和批评。从此以后,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不准教书,不准发表文章,每月只发生活费三十余元,令他到资料室劳动。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和历代碑帖卖掉。任先生曾是夏先生的高足,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感情笃深。反右后,任先生身处逆境,又患重病,却仍勤奋治学。他写出的学术论文除了1961年暂短的宽松时期得以本名刊出(如为《中华文史论丛》创刊号撰写《经纂小辨三题》),其他大多不能发表,夏承焘先生慨然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报刊上去刊载,稿费交给任先生去补贴家用。“文革”爆发,夏承焘先生为此多次被批斗,两人所遭到的凌辱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文革”次年秋,任先生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任先生临终前,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死了,夏先生可以少一条罪名了。”我是直到90年代去杭州时,才认识任平贤伉俪的。一次专程请任平兄带我去他家拜见师母,并和师母合影留念,作为我对任先生的教泽师恩的一点表示。那时我已年逾古稀,任平兄叫我和师母并排坐下拍照。相互推让了半天,我还是站在师母的身后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收入了我的画传《跨过的岁月》中。
论曰: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此所以忠言常遭忌于当道,直行多为社会所不容也。呜呼!任先生两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惨之境?他的敬业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有时想,他在为人处世上是不是太执着一些?对于这种品格,我不知道究竟应当加以赞美,还是为之痛惜?前些年听人说,上世纪50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学任教务长时,一心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律己严,而且也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曾在别人上课时去旁听,发现讲解有误,就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直言说出,以至使对方感到难堪。我能够理解任先生的性格。我相信,任先生这样做,丝毫没有扬才露己、贬损别人的成分,他比那些貌似谦逊的伪善者心地要善良得多。但是,他在做法上太激切了,太缺乏考虑了。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若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无邪堂答问》一书多重修身哲学,其中有许多精辟意见,令人折服,上面所引这些话也是不错的。但无邪堂是理学家,不大重视甚或轻视人的性情方面。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语云“人无完人”,亦明此理。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那种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恐怕这也就是人生产生许多困扰和悲剧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难逃此数。
——写给我们亲爱的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