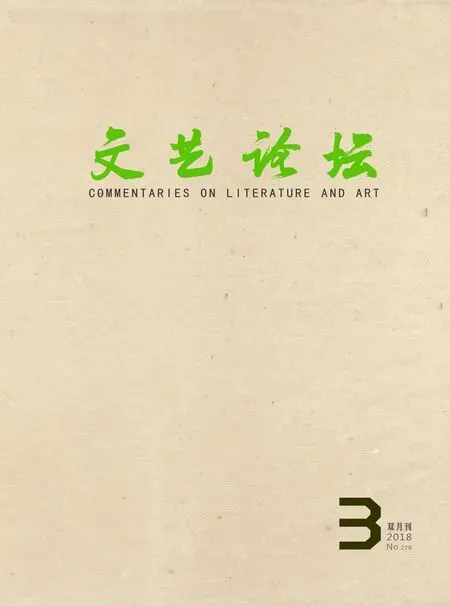流动的幻象:当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贾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当代艺术的流动性
当代艺术种类繁多、样式丰富,思潮一波接着一波,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与多变,当代艺术思潮在总体上呈现出了较强的流动性特征,有的往往只是昙花一现。20世纪50年代前后至60年代,是二战结束之后的沉寂期。1945年,萨尔瓦多·达利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迷咒》设计“梦”系列场景。1946年,“抽象表现主义”这个名称首次由罗伯特·科茨采用在当代纽约绘画上。1949年,西蒙·波伏娃出版《第二性》。1951年,由罗伯特·马瑟韦尔主编的深具影响力的刊物《达达画家与诗人》发行。1953年,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在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演。1956年,理查·汉密尔顿的拼贴作品《是什么让今日的家庭显得如此不同,如此诱人?》被视为首件波普艺术作品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展出。1957年,“零”(Zero)在杜塞尔多夫成立,以促进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对话。1960年,“后现代”名词出现于丹尼尔·贝尔的《社会学的终结》。在以上历史背景下,其间出现了抽象表现主义、拼合艺术、无形式艺术、废物雕塑、芝加哥意象派、新达达等艺术思潮。
1960年代至1980年代,是西方消费时代的迅速发展期,当代艺术思潮出现了关注个体、性别、身体、政治、科技的艺术主张。例如,1962年,波普艺术展“新写实主义”在纽约希尼·詹尼斯画廊展出。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出版《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5年,“极少主义”的名称开始被普遍运用。1966年,罗伯特·文杜里出版极具影响力的“后现代”论述《建筑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1967年,“贫穷艺术”由杰玛诺·塞朗提出,“概念艺术”的名字普遍化。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性政治》等,为此时当代艺术的发展推波助澜。1971年,“艺术与科技”在洛杉矶州立美术馆举行的展览中达到巅峰。1975年,首次“涂鸦艺术”在纽约艺术家空间展出;身体艺术作品在芝加哥当代艺术学院展出。1977年,苏珊·桑塔格出版《论摄影》;电影《周末夜狂热》造成迪斯科狂潮。这一时期的当代艺术思潮有波普艺术、行动主义、极少主义、贫穷艺术、概念艺术、身体艺术、女性主义艺术、公共艺术、装置艺术等。
1980年前后,世界政治格局相对稳定,艺术思潮的发展趋于平缓。政治关系、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大众传媒、流行文化、文学作品、建筑环境、资金流通以及其他各种力量在推动着艺术家进步的同时,还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艺术伴随着对以往既定模式的反思也开始发展起来。“伤痕文学”“伤痕美术”的兴起,正是这种思潮在艺术中的一个反应。“伤痕”一词得名于伤痕文学家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该文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的上海《文汇报》。这篇具有强烈悲情色彩的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普遍心声,因而引起了巨大反响。知青画家刘宇廉、陈宜明、李斌1978至1979年合作的连环画《伤痕》《枫》《张志新》,表现的也是后一时期人们在思想领域的反思和批判。这些创作开始体现出对个体内在生命的深切关注,原先的集体意识逐渐衰落。至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青年艺术家们掀起了一场激进的当代艺术运动,亦即“85新潮”美术运动。对于此次运动的意义,专家们见解不一。钱海源在其专论中总结了两个在后来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其一、“85新潮”美术运动以“观念更新”和“反传统”为名,推崇“艺术的非意识形态化”;其二、“85新潮”美术运动“全盘西化”,传播现代主义。①作者在文中例举了“新潮”作者的不少文章,指出他们都非常坦诚地将“全盘西化”的主张说得很清楚。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实际上首先复制了西方20世纪艺术发展的轨迹,总体上同样呈现出了较强的流动性以及驳杂性的特征。2015年初,雅昌艺术网连推七篇文章回首30年前的“85新潮”。文章包括《“85新潮”30年回首:曾经的“先锋与达达”今何在》 《“厦门达达”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85美术新潮”之“行为艺术篇”》《将“反艺术”进行到底——“85美术新潮”留下了什么?》等,末篇文章的标题直接将“85新潮”定性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反艺术”运动。评论家高名潞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图像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文化身份的角度、哲学观念的角度去看待1985年出现的作品,从各个角度出发对它进行定位,你会发现它是一次非常反艺术的运动”②。河清教授认为,“85新潮”只是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操练,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实为中国制造的西方“当代艺术”。而对于西方当代艺术,他的批判非常激进,“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认定:所谓的‘当代艺术’根本上不是艺术,因为它是建立在小便池(杜尚:《泉》)是艺术品的逻辑之上。‘当代艺术’的主要形式,把日常俗物直接拿来‘装置’,不是艺术。……‘当代艺术’不追求美,只是崇拜‘新’,追求奇奇怪怪。所以‘当代艺术’追求怪异、怪诞、荒诞、血腥等,司空见惯。”③河清在这里表达的是对当代艺术的反艺术与反审美倾向的强烈不满。毫无新意、平庸不堪、一无是处这些词仿佛是当代艺术挥之不去的恶评。法国哲学家让·波德里亚曾在《解放报》上直截了当地宣布:当代艺术一文不值。此文一出,令当时法国有关当代艺术危机的辩论硝烟再起,变本加厉。
二、反审美的美学风格
伊夫·米肖在自己的专著《当代艺术的危机》中列出了激烈反对当代艺术的理论家们的意见清单,大致如下:“当代艺术枯燥乏味;它不能引发审美感受;它在思维层面上弄虚作假,为的是掩饰空洞、毫无意义的本质;它毫无内容;确切地讲,它四不像;没有审美标准可以适用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无需任何艺术才华;它是在历史中枯竭的艺术;它是过度历史化的产物;它不再是具有批判性的艺术;它纯粹是市场的产物”④。这些理论家对于当代艺术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论断,也就是当代艺术已经成功地将审美从艺术的殿堂中驱逐了。
欧洲启蒙运动带来了现代艺术体系的诞生,康德将艺术的存在属性归之于审美,同时又在先天禀赋的维度上规定了审美独立于人类其它生存活动的类本质特征,从而为艺术立法,确立了“艺术自律”的概念。在康德看来,艺术家需要具备想象力、知性、精神和鉴赏力,同时这些能力需要与艺术创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通力合作,才能维持艺术的自律。康德之后,艺术的自律性趋势日渐强化,“艺术”与“美”被彻底地绑定在一起。谢林的《艺术哲学》提出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黑格尔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观点,他在《美学》一书的伊始就宣称:“这些演讲是讨论美学的;它的对象就是广大的美的领域,说得更精确一点,它的范围就是艺术,或则毋宁说,就是美的艺术。”美学“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⑤并且,美的艺术无论多么自由自律,还需要面向人类提升生命的需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真正的艺术不是要阻止生命,而是要激发生命、释放生命、美化生命;要将存在置入澄明之中,并把这种澄明作为提高生命本身来贯彻到底。”⑥比如,西方古典舞蹈的典范是芭蕾。芭蕾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为“跳跃”。舞者竭力把身体向上升举,通过足尖起舞和高翔空中,张扬自身的超越理想。它的动作的指向性是永远朝上的,“开”“绷”“立”“直”的美学规范使得人体时时保持一种优美的空中形态,从中不难看出对“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希腊雕塑效果的追求。如此对照当代艺术来看,当代艺术的反审美倾向遭人诟病也就不难理解了。
加之当代传媒技术的日益普及,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视觉化的信息与图像,形象取代语言,成为表达诉求的主要方式。人们热衷于从视觉图像中获得即时的满足,热衷于虚幻的、超现实的表象对感官的刺激。用鲍德里亚的术语,越来越多媒介化的图像和经验都变成了刻意的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拟像”。饱含本雅明意义上的“灵韵”的原型和复制品再难被区分开来,人们丧失了现实感,所剩的仅有超现实、反讽、挪用、媚俗和转瞬即逝。从这个角度来概括,所谓当代艺术,无非是一系列反审美的流动的幻象的集合。然而,当代艺术真的就完全没有价值可言吗?
1980年以后的众多艺术家和批评家一直大力投身于当代艺术的理论和批判性分析。最具影响力的几个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段时期的理论批判审视了众多艺术领域,包括艺术史的结构和趋势,博物馆、艺术节的政治策略和实践规范;艺术市场经济学的本质和运作;大众传媒通过何种视觉手段来影响观念和趣味,等等。特里·伊格尔顿著有《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文化风格,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幻象”。“我们碰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它的‘自由’由一种对事实的摹拟组成,这一主体根本没有任何基础,因此他有权在一个本身也是任意的、偶然的、随机的世界中或是焦虑地或是狂喜地自由流动。这个世界,这么说吧,以它自己的无基础作为上述主体的基础,以它自己无需理由的特征为这一主体的自由漂移颁发了许可证。……完全难以看出在这里人可以真正地谈论自由,正如在阳光里舞蹈的灰尘粒子不是自由的一样。”⑦不过,伊格尔顿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它的意义,在后来的访谈中,伊格尔顿承认,“后现代主义当然有较为激进的方面,我确实没有论及”⑧。对于当代艺术的这种较为激进的方面,朗西埃倒是颇为欣赏。朗西埃指出,正统的纯粹艺术及其审美规范一直都享有特权,甚至霸占了所有的美学空间,这种“艺术霸权”与“审美霸权”,势必会引起美学的“不满”。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在面对各种以怪诞取胜或者以拼贴见长的向日常生活敞开的大众艺术时,这种正统的“美学制度”便遭遇了严峻的挑战,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境。在朗西埃的“政治美学”理论的考量中,当代艺术最具价值之处恰恰在于其“反审美”的美学风格。
艺术创造在原始社会与生活是同一的,不存在优越感的问题,优越感的产生则是后来的事情,因为艺术、审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奢侈的、贵族化的或者说高不可攀的东西。随着当代社会开始大范围地推进政治民主化、教育民主化、文化民主化的进程,这种“高高在上”自然会被拒绝。当代艺术的“反审美”倾向带来的巨大变革就是审美的大众化意识的迸发,在一个审美泛化的世界里,人们的审美和艺术体验趋向于极端多样化以及不可控。为此,哲学家维茨提出,“艺术是一个潜在开放的概念,使人可以预见艺术‘极度扩张、冒险的性质’,可以吸收‘不停歇的变化和全新的创作’。”⑨韦尔施提醒艺术家必须高度明确自己的如下使命,我们的真正任务“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发展不同的感知角度和方式,以及变化多端的感知和理解图式,并且加以示范”⑩。当代艺术发展至此,让人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人们摆脱权威思想和趣味规范,向所有敢于尝试的人开放,从而带来了创造力和思想的更大的自由。
三、新历史阶段审美标准的重建
当代艺术使十八、十九世纪通行的审美标准不再有效,这已然是一件毫不令人奇怪的事情,现当代艺术本身就肩负着消解传统审美范畴的使命。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审美标准还存不存在?应该如何存在?当代艺术经常运用干扰、中断、抗拒等手法去创造一些酷炫、激愤和拙朴的作品,观众则在反传统审美产生的“震惊”效应中使那业已被审美化所麻痹或操控的感性得到复苏和拯救,但没有任何东西比震惊更快地丧失效果了。失却“审美标准”而引发的弊端在当下已经暴露得越发明显:艺术家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心理,一心只想其作品在市场上谋得高价;批评家畏首畏尾,从原先对特定作品的臧否转向对文化产品的无差别推广;艺术创作背离了专业性,媒体则随时伺机制造轰动效应;人们深陷上述幻象的泥潭无法脱身。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在当下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重新发掘一套可供操作的稳定的审美标准,它可以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突破感性经验制造的幻象。
策展人尼古拉斯·伯瑞奥德提出“关系美学”的理论,所谓“关系美学”指的是“依据作品所再现、制造或诱发的人际关系,来判断艺术作品”⑪。他认为中世纪的艺术关注人与神的关系,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着重表现人与物理世界的关系,浪漫主义美学更看重艺术与自我的关系,而当今的艺术关心的则是谈判、连接和共存这样的人际关系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艺术活动已经体现了这一转向。因此,现在的艺术的作用在于创建社区情景,建立“共识艺术”,以此创造和发展社会连接的新形式,这种新的连接形式可以缝合我们当下社会的碎片化。“关系美学”侧重于艺术的缝合作用,建造和谐的“共识艺术”。这导致朗西埃对该理论颇有微词,他怀疑“关系美学”将道德置于形式之上,消弭了政治维度,以至于会造成掩盖现存的社会冲突的后果。
朗西埃师从阿尔都塞,擅长于思考差异性、思考历史的断裂,而不是共识以及社会的可缝合性,更无法容忍关系美学将社会性乌托邦和革命希望让位于日常生活的微观乌托邦和摹仿策略。朗西埃认为艺术实践不能替代现实的政治行动,艺术的政治功能不在于介入现实,而是通过保持与现实世界的审美距离而发挥“歧感”效用,去扰乱所谓“正确”的观看、言说与行动的方式,改变各个政治主体对自身的“位置”和可能性的认知,使不可见者可见,不可闻者可闻,才有可能推动人类改变世界、引领自由解放的实践。比如比利时导演阿克曼的纪录片《另一边》、葡萄牙导演科斯塔的《旺妲的房间》。在国内,也能找到与朗西埃的理论有共鸣的艺术家,像张晓刚、毛旭辉。毛旭辉说:“艺术的功能即那种感性的力量异于概念之类的东西。惟有这富于感性的、微妙而深层的,又是自然的原型的变化是一般人所不知的。他们即使有所察觉和体验,但平庸的教育,流行的观念的干扰,阻碍了他们对事物本质的领悟。艺术在翻译、在暗示,像个发光体,但它不是解释。它启示,富于象征和寓言……艺术不是一种教育,它是一种唤醒。”⑫不过,与其说朗西埃讨论的是艺术,倒不如说他讨论的是艺术体制。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所谓的当代艺术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阐释的共同体的生活结构也越来越宽广。朗西埃据此倡导一种“歧感”美学,“歧感(dissensus)不是关于个人利益或观点的争吵。它是一种政治进程,通过使既定的感知、思想和行动的框架面对‘不被承认者’,也即一种政治主体,来抵制合法裁断,在可感性秩序中制造裂缝。”⑬在朗西埃看来,“歧感”永远无法被消解,它可以动摇既定的现实框架和既有的“常识”,从而开拓一片可见、可言和可行的新风景。在这里,“歧感”绝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理论,更像是朗西埃的政治理论在美学中的展现。
在最近汪民安教授与朗西埃所做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朗西埃在谨慎地防范自己的理论中以政治消弭伦理的倾向。他说他思考歧感概念之初,遵循的是“理性交流”的逻辑,这一逻辑认为基于一种能够使人们最终相互理解的对话,我们可以思考政治团体、思考社会生活的可能性⑭。伊格尔顿曾指出,“伦理处理的是诸如人的价值、目标、关系、操行素质、行为动机之类的问题,而政治提出的问题是,为了确保养成特定的价值观和素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权力关系和社会机构。”⑮因此,伦理与政治不能被混为一谈,同时也不能被截然分开。综上可见,当下审美标准的重建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无论“关系美学”,还是“歧感”美学,其实都是从艺术本体论的视角出发而做出的对新的历史阶段的审美标准的思考。高建平教授在其《艺术作品的“本体”在哪里?》一文中提到,艺术本体论从其字面的意义上讲,即关于艺术存在的理论。首先可以研究“艺术与哲学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即将艺术放在一个总体的本体论体系之中,看艺术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关系。世界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艺术可能是世界这个大厦中的一个房间,也可能是世界之外的一个独特存在”⑯。显然,“关系美学”对应了前者,“歧感”美学对应的是后者。行文至此,可以肯定的是,能令人一劳永逸的普世的审美标准是不存在的。
鉴于当代艺术的开放性,新的审美标准可能更倾向于以“复调”或“博弈”的方式系统性地呈现,从而帮助发挥批评的功能,判断艺术的价值。新的审美标准当然不会止步于“关系美学”和“歧感”美学。总的来看,新的审美标准的重建还是当代批评家和艺术家们待完成的一项课题。
注释:
①钱海源:《“85美术新潮”的若干论点》,《美术》1991年第2期。
②高名潞:《我为什么提出“85美术新潮”》,《艺术世界》2005年第1期。
③河清:《“当代艺术”:世纪骗术》,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0页。
④伊夫·米肖著,王名南译:《当代艺术的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
⑥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8页。
⑦特里·伊格尔顿著,华明译.:《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页。
⑧⑮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著,王杰、贾洁译.:《批评家的任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第227页。
⑨马克·吉梅内斯著,王名南译:《当代艺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⑩韦尔施著,陆扬、张岩冰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⑪尼古拉斯·伯瑞奥德著,黄建宏译:《关系美学》,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⑫费大为编:《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⑬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M]. London: Continuum,2004,P85.
⑭朗西埃、汪民安著,邓冰艳译:《歧见、民主和艺术——雅克·朗西埃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2期。
⑯高建平:《艺术作品的“本体”在哪里?》,《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