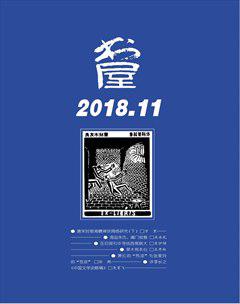威尔与克里斯托弗·马洛
傅光明
1. 威尔“挑战”“大学才子派”
威尔在伦敦看的第一部戏,是“海军大臣剧团”在菲利普·亨斯洛刚于泰晤士河南岸建成不久的“玫瑰剧场”上演的无韵诗悲剧《帖木儿大帝》(Tambur laine),作者是威尔的同龄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
虽说《帖木儿大帝》是马洛写的第一部戏,但这对于刚到伦敦不久,才在某剧团打杂并开始协助编戏的威尔来说,无疑是个刺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两人同为二十三岁:威尔是没上过大学,是刚进城的乡巴佬;马洛是剑桥大学艺术硕士。
更大的刺激在于,当时雄踞剧场的专业剧作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且多为名校出身的大学才子,罗伯特·格林、约翰·李利、托马斯·基德和马洛,乃名冠伦敦的“四大才子”,其中尤以马洛才情最高、成就最大。《帖木儿大帝》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马洛又先后推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史》(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和《马尔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两部大戏。
这么说吧,三年之后的1590年,当威尔摇着鹅毛笔正式开始写戏且崭露头角之时,马洛已是那个时代的头牌剧作家,被誉为“诗剧的晨星”。
但对威尔来说,比刺激更大的麻烦在于,这些才子从骨子里瞧不起他,罗伯特·格林甚至在其《小智慧》一书中,毫不客气地指桑骂槐:“我们的羽毛美化了一只自命不凡的乌鸦,他以‘一个戏子的心包起一颗老虎的心,自以为能像你们中的佼佼者一样,浮夸出一行无韵诗;一个剧场里什么活儿都干的杂役,居然狂妄地把自己当成国内唯一‘摇撼舞台之人。”
这话骂得够狠!套用尼克·格鲁姆的话说,“格林暗指莎士比亚是一个恶毒的剽窃者和乡巴佬”,因为他写戏常从才子们的剧作中“借”灵感一用,比如“一个女人皮囊里裹着一颗老虎心”见于莎剧《亨利六世》(下篇)第一幕第四场第一百三十八行。显然,“摇撼舞台之人”更是格林对威尔这个“挥舞长矛之人”(Shake-speare)的直接羞辱,因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英文名恰好由“挥舞”(shake)、“长矛”(speare)组成。“shake”有“挥舞”、“摇动”、“震撼”、“撼动”等多重意涵。
不过,对威尔之于马洛,尼克·格鲁姆说得十分精到:“莎士比亚深受马洛影响(他甚至在《皆大欢喜》中引用过马洛的诗作《希罗和利安德》),这种焦虑渗透进莎士比亚的多部作品,它们与马洛的剧作对话:模仿、戏仿、改写,并最终超越马洛——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莎士比亚写作生涯结束。但跟马洛相比,莎士比亚有两大优势。他是个演员,因此对角色的感觉更丰富。马洛没有这样的经历。这一优势能使莎士比亚摆脱马洛的影响,创造出像浮士德那样性格丰富的人物。另一个优势:那时候,马洛已不在人世。”
1593年5月30日,马洛在德特福德的一间“小屋”中死去,有的说起因于酒馆账单纠纷引发的争吵,被人刺伤而亡;有的干脆说死于谋杀。
1594年,莎士比亚开始“撼动”(shake)舞台,他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轰动一时,按格鲁姆所说:“1594年,玫瑰剧场,六天内上演三场——这真是壮举,因为一部戏的平均寿命,几个月内上演十几场便结束了。”
1602年,与威尔在“内务大臣剧团”同过事、曾红极一时的丑角演员威廉·坎普,对此时已写出《哈姆雷特》的威尔这样评价:“念过大学的人很少能把戏写好,我们的伙计莎士比亚比他们谁写得都好。”
2. 威尔“挑战”马洛
1586年,一位名叫鲁伊·洛佩兹的葡萄牙裔犹太人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私人医生,多年之后,这位御医卷入一场政治阴谋,并被怀疑伺机毒死女王。
1594年6月7日,在众多嘲讽挖苦的民众围观下,洛佩兹被绞死、剖腹、肢解。为迎合、利用当时伦敦人对洛佩兹及所有犹太人的仇视,“海军大臣剧团”此时重新上演了马洛在审理“洛佩兹案件”期间创作并上演过的《马耳他的犹太人》,共演了十五场,场场爆满。
因洛佩兹的名字Lopez与拉丁语“狼”(loup)谐音双关,它便具有了“犹太狼”的字义。在莎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法庭”戏中,葛莱西安诺讥讽夏洛克:“你这狗一样的心灵,定是前生从一颗狼心投胎转世,那狼吃了人,被人捉住绞死。”这个“被人捉住绞死”的“狼”(loup),或许就是指“洛佩兹”(Lopez)。
甭管洛佩茲是否入过威尔的眼,马洛笔下“马耳他的犹太人”巴拉巴斯这个人物形象,在威尔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同时,《威尼斯商人》用放债者的女儿强化喜剧(更是戏剧)效果,应直接源于马洛。莎士比亚甚至为了“挑战”马洛,更为吸引观众眼球多卖票房,他一开始写下的题目是《威尼斯的犹太人》,而且,这一剧名在剧团剧目上一直沿用到十八世纪中叶。
先来看看来自“马耳他”和“威尼斯”的两个“犹太人”。《马耳他的犹太人》一开场,是庆祝巴拉巴斯得到金银、丝绸和香料等大量财富;《威尼斯商人》虽也在一开场便强力引出安东尼奥的货船满载着丝绸、香料,但安东尼奥“情绪低落”,因为所有这些身外之物的财富跟他同巴萨尼奥的感情比起来显得无足轻重。正因为此,始终有后世学者,如奥地利诗人奥登试图以同性恋来诠释他俩的友谊。
与安东尼奥不同,巴拉巴斯的唯一目的就是挣钱。财富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中成为卓有成效的物质驱动力,这在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和巴拉巴斯的女儿阿比盖尔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夜色中的杰西卡将父亲的财宝装满匣子,扔给等候的情人,与他私奔;忠贞的阿比盖尔却在夜幕下从父亲家取出被罚没的财宝,扔给父亲。
由此,再来对比一下两个父亲对女儿的态度:夏洛克声嘶力竭地嚎叫,“我的女儿!啊,我的金钱!啊,我的女儿!”巴拉巴斯得意洋洋、不无反讽地慨叹:“姑娘啊,金子啊,美丽啊,我的祝福啊!”
两种滋味各有千秋,但在挖掘人性上,威尔更胜一筹。
3. 夏洛克“挑战”巴拉巴斯
马洛笔下的巴拉巴斯是个单线条的纯“恶棍”,他家财万贯,贪婪成性,阴险奸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撺掇女儿谎称自己皈依基督教,是为进入被没收并已改建成修道院的私宅轉移埋藏的财产;用一封信挑起追求女儿的两个青年决斗,使其双双毙命;为惩罚女儿,把修道院的修女全毒死;怕罪行暴露,又接连害死四名知情人;在土耳其人与基督徒的战争中,他诡计多端,阴谋叛逆,先将马耳他岛出卖给土耳其人,再策划将土耳其人投入沸水锅中,结果自己掉入锅中死于非命。他体现出一种全无人性的魔鬼般的邪恶,在他身上除了无尽的贪婪,找不出丝毫亲情、道德、法律、正义的痕迹。这样一来,马洛刚好用“他”这个犹太人,为当时对犹太人充满仇视的社会,以娱乐消遣的戏剧方式提供狂欢的温床。
巴拉巴斯虽也受到基督徒的鄙视、压迫,但他一味拜金,面目可憎,令人心生厌恶。两相对比,夏洛克的命运更令人心生酸楚,从喜剧发出的笑含着泪。威尔艺术地为夏洛克与基督徒的对立提供了真实、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作为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犹太人,并因此成为受基督徒鄙视的人。他要通过割下安东尼奥这个活生生的基督徒身上的一磅肉,把对所有基督徒的仇恨、报复淋漓尽致发泄出来。焉能说此中没有其犹太民族的自尊?简言之,夏洛克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其多元、复杂的深刻、精彩是巴拉巴斯不可比的。
实话说,在一些细节上,威尔对马洛有借鉴。比如,巴拉巴斯面对基督徒的蔑视从容自若:“当他们叫我犹太狗时,我只耸耸肩膀而已。”夏洛克也不例外,当安东尼奥骂他“异教徒,凶残的恶狗”时,“我对此总是宽容地耸一下肩,不予计较”。
另外,夏洛克在“雅各侍奉上帝的冒险买卖”中得到满足,和巴拉巴斯在“上帝对犹太人的祝福”里陶醉如出一辙。还有,巴拉巴斯相信,若没有天赐神授的物质财富,人便失去了活的意义,他向那些想拿走他财物的人吼道:“为什么,你们要断了一个不幸之人的命根子,比起那些遭受不幸的人,我的自尊就活该受伤害;你们侵吞了我的财富,占有了我的劳动果实,夺走了我晚年的依靠,也断送了我孩子们的希望;因此,从来就没有是非的明辨。”夏洛克听到威尼斯公爵的判决时,无力抗辩道:“不,把我的命和我所有的一切统统拿走吧。我不稀罕你们的宽恕。你们拿走我支撑房子的梁柱,就等于毁了我的家;而当你们拿走我赖以为生的依靠,就等于活活要了我的命。”事实上,这又何尝不是此时已无助无靠的失败者夏洛克残存的最后一点儿可怜的尊严。
以剧中人物的活色生香来说,夏洛克完胜巴拉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