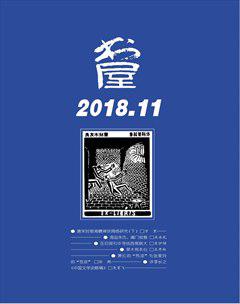《厨房》里的爱与生
杜怡
吉本芭娜娜的小说集《厨房》,收录了《厨房》、《满月》、《月影》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在内容上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即“死亡”与“重生”。书名取为《厨房》,意味着厨房这个特定的家庭场所充满了私密性,空间小且存储的物件多,赋予了主人公无穷的想象力,也见证了主人公情感的起伏动荡。厨房不仅包容了情感世界,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使人得以维持生命。厨房象征着生命与生活,也象征着重生。
半自传体的小说娓娓道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很容易带领读者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这个充满黑暗、阴郁、死亡的世界,似乎暗无天日。亲人接连不断地死去,主人公从茫然未知的少年到日渐成熟的青年,死亡从未停止它的脚步,它深深地“眷恋”着樱井美影。她刚从沼泽地里出来便又踏进另一片泥泞,生存的欲望不断被打击,但依旧步履艰难地活着。安慰人心的是一次次的厨房经历,以及由厨房诞生的食物;同时,最能够维持生存欲望的是身边的人,尽管身边的人也是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前行着,但一次次相依相偎的取暖,给予了彼此重生的勇气和能力。治愈性的风格,便让我想到了同样是日本的作品——《深夜食堂》,只是它是电视剧,更加直观地展现了朴实饱满的食物与都市生活中的人情冷暖。这间食堂从深夜十二点开始经营,它躲避了车水马龙的街道、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和高耸密集的楼群,错过了刺眼的阳光,但并不缺少人间的温暖,这温暖是由淡淡月光以及那个不苟言笑却体贴入微的厨师所带来,况且还有热气氤氲的食物。白天躲避在楼群里的人们,内心寒冷。夜深人静时,当繁华归于平淡,一碗碗暖人心肺的饭菜温暖了都市零散落寞的心,美味与饱腹填充了孤独感。由此看来,《深夜食堂》和《厨房》暗暗契合。《厨房》整部书分为三章,每一章都有一个题目:《厨房》、《满月——厨房II》、《月影》——都是在黑暗下酝酿情绪,发生故事。
第一章《厨房》,主人公樱井美影痛苦地回忆了身边的死亡,并不断地寻找赖以生存下去的支撑之物。她突然意识到她无比热爱厨房,喜欢在里面烹饪,甚至连睡眠都愿意身处其中。“我怎么会这么酷爱厨房的工作?就像热爱烙印在灵魂深处记忆中的遥远的憧憬一样,爱着它。站在这里,一切都恢复到了原点,某种东西又回到了我身上。”她对自己如此迷恋厨房做出了解答,她憧憬母亲在厨房里“乒乒乓乓”的“战斗声”,然后端出一盘盘用心做出的美食,一家人和和气气地吃饭、聊天,抱怨忙碌一天的不顺或是吹噓一下一天的成就,充满烟火气的世俗之乐。即使是如此平淡的快乐和适意,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获得的,我不禁想到高中的一个同学,她来到我家,唯独对厨房情有独钟。她说她的梦想就是结婚之后拥有一个这样的厨房,无须太宽敞,只需要亮堂,也要设计成推拉的玻璃门,这样丈夫和孩子可以看到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她也可以看到厨房外丈夫和孩子等待饭菜上桌的焦急与欣喜。当时的我大为惊愕,怎么会有这么“不求上进”的梦想?后来才得知,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虽有父亲,但形同虚设,从来没有为家里的一针一线贡献过一份力,他经常酗酒、赌博,即使在家,也和母亲不停地吵架;母亲为了维持家庭日常所需,经常在外奔波忙碌,几乎不回家,几乎不做饭。况且,住的地点经常随着欠债人的追赶而变动,新的住处往往来不及有一个“厨房”。再回忆起那日的场景,她那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的眼睛以及满心的期待,便觉得一切可解了,作为旁观者的我,更多是心疼。同学如同《厨房》里的主人公,渴望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
“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厨房。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样子,只要那里是厨房,只要是做饭的地方,我就不会厌恶。厨房即使脏乱之极,我也爱不自禁。”樱井美影不断地强调她对厨房的迷恋,这其实是对生活的热爱。每一个爱做饭的人都是爱生活的人,从本质来说,由最初的生理需求上升到了心理需求。精致、美味的饭菜出自于“溅满油渍的灶台、生锈的菜刀”,宛若呈现在外人面前光鲜体面的生活,其中掩盖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慌张、忙碌。但女人依旧热爱这样的厨房,饱餐一顿后,让厨房的脏、乱重新回归到整洁如初的状态,女人有办法让一切重新步入正轨。樱井美影多次在厨房中倚着冰箱睡着,她爱冰箱,大概是冰箱散热时发出的“嗡嗡”声,在孤独者心理便是“人气”,便是安慰。
第二章《满月——厨房II》与第一章《厨房》贯通,而这个贯通的主要人物是惠理子。惠理子是雄一的母亲,而更准确的定位是父亲与母亲的结合体。惠理子在经历了妻子的死亡之后需要继续活着,绝望之后的重生,他选择了变性。与其说是要面对真实自我,更是出于纪念妻子,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剧烈的疼痛之后,他用极致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妻子。在儿子那里,这不仅仅是一种性别的转换,也是一种情感的转换,父亲变成了母亲,弥补儿子缺失的母爱。母爱相较于父爱,可以更细腻,也可以更具体。变性的背后也是一颗残缺的心,人有时会选择用放浪形骸的行为来遮蔽内心深切的痛楚。逃离失去亲人的痛苦的方式有许多,但总会有一些人选择保留,不愿释怀。似乎选择了最正常方式的人是樱井美影,她选择了看似最洒脱的方式:用做饭来拯救自己。“为什么人竟是这样地无法选择?即便像蝼蚁一样落魄潦倒,还是要做饭、要吃、要睡。挚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自己却还是必须活下去”。人死如云散,往事不可留。死是容易的,只是活着的人还要想方设法地活下去,而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便是吃喝,似乎,我们人类这一生无论多么伟大,或是多么渺小,需要吃喝的生理要求消弭了彼此的区别,我们的动物性身体让我们注定不能让灵魂轻盈,自由自在地飞。
如果无牵无挂地飞,最好的选择便是成为风筝。但人有了牵挂,就如同风筝有牵线人,风筝有了限制,而人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却很踏实、安稳。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没有人可以从生到死一直陪伴着另一个人,但人独自前行总会寒冷、寂寞,需要同伴给予一些温暖,尤其是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加缪说人在困境中,容易产生相依为命的情感。用在樱井美影与雄一的身上,十分贴切。同样遭受重创,能够忍受彼此身上的缺陷,两个人带着死亡的阴影与缺憾的人生走入彼此生命并产生交集。
《厨房》前两章都属于《厨房》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月影》同样是死亡与重生的话题,与前面的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不期而遇的死亡袭击生命时,樱井美影以顾影自怜的方式悲叹命运的不公,雄一以旅行的方式远离习惯已久的生活,避免睹物思人以及承担责任,惠理子以转换性别的方式变更人生定位。《月影》主人公早月的男友阿等在一次意外中死亡,她以跑步的方式转移注意力,渴望在寒气凛冽的冬日用冰冷封存记忆;在这次意外中丧生的还有阿柊的女友,面对哥哥(阿等)和女友一同逝去的双重打击,阿柊一本正经地穿着女友的水手服,旁若无人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就如《棉被》里的男老师,面对深爱着的女学生的棉被,他沉潜在个人的意淫里,躺在棉被里,尽情地吮吸残余的味道,难以自拔。大凡恋物,实质是恋人,男老师因为不敢爱对方的人,于是就会去爱对方的物,对物加以崇拜。而阿柊敢爱对方的人,更敢爱对方的物,甚至痴迷。这或许与日本人追求极致的心理有关,凡事总要做到极端,甚至有时达到形神枯灭的地步。而《月影》中最为动人的地方在于将潜意识与心中模棱两可的情感完美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在恍惚之间,主人公见到了逝去的男友阿等,阿等在月影朦胧与江边雾气中浮现,随后又在其中消失。人影徘徊中多了和女友郑重其事的分别,但这简单行为却能让她解开心结,重新走上真实的生活。这些“灵异”、“共鸣”、“心灵感应”的现象更能够衬托出“孤独”。但毕竟一边沉浸在记忆里的雾霭中,一边只能痛苦地触摸生活。在巨大的哀痛之中,梦境与现实几乎难以分辨。
故事中有许多看似悖谬的叙事手法,人作为社会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在生活的路上不依靠人而依靠物,不依靠活人却依靠死人,实实在在的“真实”不敌虚无缥缈的“虚构”。这种无处沟通、无处倾诉、无处救赎的苦恼,大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享受的快捷的交通工具、沟通工具,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时间距离。伴随而来的却是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的隔阂。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可以嬉笑怒骂,但在现实的宽广环境里却难以交流,以致产生“现实世界不如虚拟世界安心”的感觉。
爱诗乐·沛克在《忧伤的时候,到厨房去》中写道:“地球的中心并不是一个巨大的铁球,而是一个个家庭里的一个个厨房。厨房是母亲的乳房,是爱人的双手,是宇宙的中心。”厨房当然是治愈的,当你特别开心或是特别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躲进厨房。厨房有母亲的影子,有我们还未出生时在母体里的那种混沌感与安慰感,或是在嗷嗷待哺时隐匿在母亲胸脯里的舒适感。《末代皇帝》中幼小的溥仪被轰轰烈烈的车马带进了紫禁城,陪伴他的只有儿时的乳母,乳母的乳房是他最亲切的生理之家,也是最亲切的心理之家。少年之时,溥仪看着形如枯木的先帝嫔妃心生厌恶,他投入了乳母的怀抱,他吮吸着乳母早已干瘪的乳房,却得到了心灵的安慰。
“我从没想到,我的障碍在于性格上的毛病,而它竟然会对菜肴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樱井美影会因油温未热而将菜慌乱下锅,最后总会毫不含糊地反映到菜肴的色与味上。饭菜的状态似乎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心情。就像故事讲的,母亲做饭拥有秘籍,所以才会将每顿饭菜做得可口爽朗,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发现了母亲的秘籍:“做饭的时候请加入一些爱。”这样的故事未免太过“理想化”与“鸡汤”,但是这并不阻碍饭菜成为爱与被爱的表现,让厨房成为爱的聚集地。
《厨房》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哲理,它只是揭露了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在和平年代创作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天然地会削减“崇高性”。吉本巴娜娜笔下的死亡,没有悲天悯人的沉重感,有的只是一種积极的思考,她渴望在现代社会里构建一种新的心理价值,而这种价值甚至也无法最终解决“疾病”,它只能“疗伤”。这种“治愈系”的写作方式和内容似乎有“鸡汤”之嫌,却比“鸡汤”更猛。“鸡汤”是逃,是阿Q式的自欺自瞒,以为构筑了自己的“乌托邦”便能一劳永逸地享受其中。但“疗伤”在于正视、面对,只有这些,才有可能走出困境,尽管困境在目前没有得到有效地处理,尽管在前行的过程中总会背负缺憾。在《厨房》中,惠理子是“疗伤”的导师,他通过变性,告别丧妻之痛,逃离过去的世界,也意味着今后无法再娶;他将变性作为感情的祭奠,既是解脱,也是背负;他利用变性获得女性的特权,获得内心的自由,可以像“柔弱”的女性那样自由自在地放纵感情,放浪形骸地大哭。哭过之后继续生活,这也是人的一种自我修复能力,不足够坚强却柔韧。普通人生活难以有“诗意地栖居”的轻盈,也难以有“向死而生”的深刻,有的恰好是二者之间的生存状态,这个“过渡区”弹性很大,范围很广,远比我们想象的宽容,也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如何过得更好,我也想给一个我的答案:好好吃饭,好好爱,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