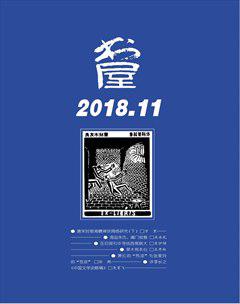评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
尧育飞
十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北师大辅修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有一天,为我们授课的刘宁老师在讲授唐诗“少年精神”时,建议我们读读李长之先生的著作。那时图书馆所藏李长之的单行本著作并不多,却有十卷本的《李长之文集》,其中就收录了《中国文学史略稿》。不读则已,一读便惊叹于李先生的才气,想不到枯燥的文学史教材竟也能意气飞扬,从此我便将此书备置案头,时常翻阅。后来研究生考试,我以此书为应试秘本,居然顺利过关。现在,《中国文学史略稿》的单行本面世了。从前言看来,编者于天池先生1978年考北师大研究生时曾以此书为秘本,一位曾有意出版此书的杨睿先生也藉此书考取北大研究生。这部书倒颇类科举时代的备考秘笈了。
然而放诸六十年前,《中国文学史略稿》不过是普通的高等院校文学史教材,虽则是1949年以后个人独著的第一部。冯其庸先生回忆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人民大学的教书生活时曾说:“那时建国才几年,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史教材实在还不可能有,当时唯一的一部是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然而现在这部书,不唯一般读者不熟知,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知晓的恐怕也不多。文学史教材汗牛充栋,不知一二实属情理之中,但《中国文学史略稿》作为新中国最早风行的文学史教材,有其独特的学术品质与可慨的身世,读者似不可不稍加留意。
一、新时代里最先风行的文学史教材
李长之(1910—1978),为现代著名学者、批评家,二十五岁即写出成名作《鲁迅批判》,此后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书也成为经典之作。李长之的一生,与数字“三”特别结缘。他有“三个向往的时代”:古代的希腊、中国的周秦、德国的古典时代;他有“三个不能妥协的思想”:唯物主义、宿命主义、虚无主义;他一生有三段愉快的时光:日本投降、全国解放、“四人帮”覆灭。在1978右派摘帽后的生涯末年,他仍有三部书希望完成:《中国文学史略稿》、《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生命的最后时光,李长之仍在修订《中国文学史略稿》,预备再版。他很看重这部《中国文学史略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还在清华读书的李长之不满于当时的文学史教材,预备自己写一部,然而那时友人老舍警告他说:“恐怕写完才觉得伤心呢。”1945年,在《我的写作生活》中,李长之重又发愿:“过去的是过去了,半生的希望是:假若再给我三四十年的时间和健康,我将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不希望长,却希望精;不希望广博,却希望深入。在这部文学史之前,须许我对过去的巨人和巨著,有自己的消化和评价,对过去的时代之文化史上的意义,有自己的发掘。”1946年,李长之到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至1953年,李长之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如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韩愈、李商隐、李清照等人,都有论著进行充分的研究。“才、学、识”他都具备了,这就为独立撰写《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坚实基础。恰巧彼时高校中文系百废俱兴,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文学史教材,早经积累的李长之在新时代的感召下,日就千言,很快写出了这部《中国文学史略稿》。称为“略稿”,则是李长之自谦此书“草率得可笑”,“就像一个习画的学徒先做一点儿素描吧”。
《中国文学史略稿》第一卷各章为:导论、古代的神话传说、最早的诗歌和诗歌总集、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第二卷诸章为:汉代的散文和辞赋、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文学批评、唐代的诗歌;第三卷数章为:唐代的传奇文学、宋词的发展。宋以后时段的文学史,李长之曾有意续写,在其沉默的二十年(1958—1978)间也曾系统着手资料搜集工作并撰写部分章节,部分残稿便是收入单行本中的第十一章《元代的文学》和第十二章《明清戏曲的继续发展》。1977年下半年至1978年年初,李长之还曾对《中国文学史略稿》进行过系统校勘,并拟增添若干图片以“增加读者兴趣”,这项工作得到他的朋友启功、常任侠和杨宪益的帮助。《冰庐锦笺:常任侠珍藏友朋书信选》仍存有李长之求助的一封信:
任侠兄如晤:
前闻安治言兄壮健如昔,可慰可羡可贺也。现有一事相烦,某出版社拟再版拙著《中国文学史略稿》,弟发奇想附插图若干,可增读者兴趣,如神话中之女娲、后羿部,与屈原有关之楚器楚简,陶、谢像之佳者,李、杜像之佳者,义山书,皆常见记载,迄未见其真迹,宋元有关歌舞演剧者,诸如此类。尊处倘有照片副本,望助我一二。又弟有太史公墓照片、太白故里照片,苦不美观,不足与史公、太白精神相称,亦思有所更换。历史博物馆有辛稼轩象,肥头大耳,不知何据。久不见,拉杂书之,以代畅叙。弟因足疾,不能出门,不一一。敬请近安!
弟李长之 一月廿九
1978年12月李长之不幸逝世,生命之神没有眷顾李长之的遗愿。然而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仍惦记是书的再版,可见他对是书的钟爱。是书最早由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并入时代出版社,1958年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6月印行第一卷、第二卷,至该年10月已经五次印刷至一万八千册,故1955年印行第三卷时,初印便是一万六千册。尽管同期还另有一些文学史教材问世,但就影响力而言,李著无疑可推当日第一(李著早于“北大本”和“中科院本”文学史教材)。遗憾的是,因李长之于1978年冬遽尔去世,《中国文学史略稿》的再版遭遇夭折,而他花费不少心力酝酿的插图本也难窥全貌了。好在单行本《中国文学史略稿》以李长之晚年的修订本为底本。
二、学者之大与自具面目的书写
李长之是一位对时代与学术风气有着敏锐自觉和担当的学者。还在抗战时期,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已专辟《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应》一章,讨论学者如何因应时代巨变。他引老师冯友兰《新理学》一书自序所言“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生发出“大时代里的学者也应该大,不要安于小”的呼吁:
凡是一个民族的武功可以称道的时代,一个民族在学术上的氣魄也应该有些可观。和亚历山大的征服世界的雄心相伴,有亚里士多德在学术上囊括一切的大企图;和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相伴,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浩瀚巨作。这都是同一精神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国军已经抗拒顽敌有五年了,而且最近在国外已经善尽职守了,他们总算给国家争了许多面子。难道知识分子不也可以立点大志么?琐屑的考据应该唾弃了,吟风弄月的闲情应该杜绝了。只是纂辑而不是著述的工作应该不须沾沾自喜了。气魄需要再大些,深邃的哲学应该钻研,各种文化的核心应该把握,较大的学术系统应该建立,抱残守缺的冬烘头脑固然要不得,务趋时髦的小摆设也不必留恋了!
抗战胜利后,李长之一度感觉时代大有可为,这便是研究与汉武帝霸业相匹配之司马迁的文章,于是有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9年的全国解放,是李长之生命中第二段愉快的时光,他为国家新气象所鼓舞,到了1956年,他在《欣闻百花齐放》一文中自觉表示“欢欣鼓舞、喜而不寐”。于《中国文学史略稿》而言,为那时代背景所鼓动,这书因而别具气象。
这种气象首先表现的是格局之“大”。诚如于天池、李书两位先生在《前言》中所言,李著《中国文学史略稿》首先在眼光之大,不止着眼于中国,还观照到世界文学的面貌,尽管较为粗率,但确实初具“世界眼光”。这一点与毛泽东致柳亚子诗“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可谓声气相感。而这种放诸四海的气魄,其他文学史教材的著者很少流露的。这便是书中在书写司马迁与汉武帝关系时,注意类比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写屈原和孔子时,暗暗比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关系;也是写唐传奇时,关注于“小说”一词在拉丁语系的词源,叙写《南柯太守传》时提及“这颇类歌德童话《新的梅露心的故事》”所能见出的。这种格局之大,又不止于横向对比的眼光,在纵向的时段划分上也自成一格。如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划分为四期:第一期是上古到西汉(古代);第二期是东汉到盛唐(中世纪);第三期是中唐到鸦片战争(近古);第四期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近代)。现在看来,这种划分仍颇显机械,但在当时颇称简明。因为观照者大,所以叙诸子散文时略过了《左传》。毕竟,与孔子、孟子、墨子、庄子等诸家相比,左氏思想牢笼于儒家之内,难以成家。而这,今天的文学史是万不敢这样书写了。
李著能够在格局上自称其“大”的面目,与其为个人独著不无关系。在李长之以前,独立撰述中国文学史是主流;在李长之之后,集体撰述似乎是唯一的主潮。集体编写的文学史面面俱到,然而面目呆滯,往往缺乏阅读快感。个人著述虽难免挂一漏万,但若著者确实对中国文学各个阶段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其书往往气韵生动,个性十足。体现在章节安排上,宋词的篇幅超越了唐诗。体现在词句上,对研究对象流露了情感。譬如写杜甫的人间精神时,李长之引朱放“学他少年插茱萸”、王维“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醉把茱萸仔细看”,然后说:“这同是九月九日的感想,也同是谈到茱萸,但杜甫的诗里是多么表现对人世的留恋深情呢!在杜甫的诗里最没有山林气,隐逸气——只有热爱人间的人才能获得人们的热爱!”这种句子和修辞,是合编文学史中很难出现的。
虽是独著,李著却并不抱残守缺,而是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陈寅恪、郭沫若、余冠英等时人的成果都为他所参考。李长之曾出版过《〈诗经〉试译》,但《诗经》部分引用的注释是出自林义光的《〈诗经〉通解》及闻一多的《风诗类钞》,并不执着于己著。参考之外,李长之也有自己独特见解,如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李白的生卒年、陶渊明的身世、柳永的词,这在当时都有创见,今天看来也仍具相当的学术史价值。
三、未竟之书的余响与遗憾
《中国文学史略稿》在五十年代甫一出版即产生广泛影响,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金申熊(金开诚)、刘世德和沈玉成便在《文学遗产》撰文评介这部书。尽管他们尖锐批评是书“有庸俗社会学倾向”,然而却也指出:“从《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的作者李长之先生到《中国文学史略稿》的作者李长之先生,其间显然有着很大进步的”。这优点是在融合诸家学说,注重探讨文学变迁的社会原因,关注到民间文学的作用,以及在语言上“表现了十分流畅的运用能力,这在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里还是缺乏的”。这书也很快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1954年第4号就刊登了清水茂等人评介中国大陆的两部文学史著述的文章,一部是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另一部便是《中国文学史略稿》。因读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而改名的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终于获得三册《中国文学史略稿》后感慨道:“在我读过的中国文学史当中,这一部最有启发性,最引人入胜。”
自然,《中国文学史略稿》的不足之处也并不少。譬如其叙述框架仍牢笼于“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框架内,写唐诗和唐传奇时,对唐代的古文观照就明显不足。写宋词,似乎也并不及多谈宋诗。对书中的不足,李长之有清晰的自觉。早在1955年,他便在第三卷的《印前题记》中诚恳表示:“至于大家对第一、第二卷所提的宝贵意见,容经我消化考虑后,吸取在未来的修订本中。”这并非客套语。此后李长之尽管失去写作权利,但来自朋友和陌生读者的意见,他都认真吸取。在《新版题记》中,他表示:“对这些我所珍惜的宝贵意见,我在尽可能消化为己有后,就动笔修改。暂时不能理解的,我也不轻率从事。有的我并不以为然的,就不能不放弃了”。每一条珍贵的意见,他都详加叙述。如“友人何其芳同志曾经在一次共同参加的大会上,特地跑来找到我,跟我说:我告诉你,你的文学史里把革命导师的话和一般人并列是不对的。他那时穿黄皮加克,还是很年轻的样子。我这次照他的意见修改了,不想他已经作了古人,我十分悼念他”。
李长之自己恐怕视《中国文学史略稿》为传世之作,晚年的修订可见出他这方面的用心。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版本相比,新版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改订之处并不多,有限的数十处,也多限于词句的雕琢。可见那二十年间,古典文学的研究并无太大的进展。然而学界新的动向李长之并不曾放过。在写屈原《天问》时,李长之引申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天问》是由于庙堂的壁画触动了情绪而写起的”,这句话之后便加以注释,五十年代的版本云:“题壁是不可靠的,因为那时的书写工具没有可能写下《天问》这样长的题词,但因壁画而动笔却是可能的。”新修订本则改为:“或者有人认为题壁不可靠,因为那时的书写工具没有可能写下《天问》这样长的题词。但根据现代发现的楚国的毛笔和楚简看,因壁画而题词是可能的。”修改的根据便是1954年6月长沙左公山十五号战国楚墓出土了毛笔。这新近的考古资料与文学关系似并不大,然而李长之显然注意到了,并且因此不惜推翻了自己早年的观点。
1978年的春天,李长之在《新版题记》中坦言,对过去视为畏途的元以来的文学史的复杂性有了深入的认识,他预备知难而进,写完整的文学史,然而天不假年,他不幸遽尔辞世。《中国文学史略稿》于是乎无法完璧。书残半部,虽则有缺憾之美,但终究如一道伤疤,于作者、读者而言,似乎都不能甘心。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重印的这部《中国文学史略稿》似未能于此稍补缺憾,如并未增添插图,也未收录1955年版的《印前题记》、1978年的《新版题记》以及与李著文学史密切相关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和编写体例》、《中国文学教学大纲》、《中国文学(明清段,史的部分)温课大纲》、《近代及现代文学大事记》等文章——而这些可以窥见李长之这部未竟书稿的用心的。相比而言,李长之友人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则幸运许多,林著虽成书稍晚,且初版仅叙及唐代,但得葛晓音等先生协助,于1994年终成全璧。
(李长之著:《中国文学史略稿》,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