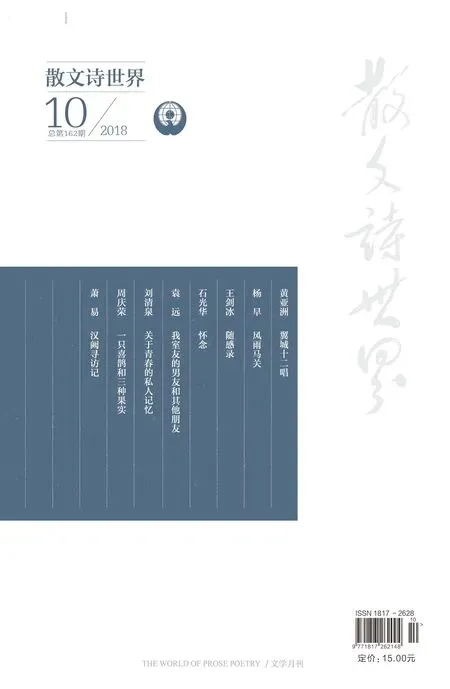刻骨,冷热抒情 三章
袁伟(扬州大学)
37℃
这是体温的一条红线,我的身体遍布警觉装置,小数点之后,不允许出现任何数字。
否则,扁桃体会燃起烽烟,免疫的三条防线全面告急。
否则,血液在深夜被煮沸,面红耳赤时,呼吸,变成没有颜色的炊烟。
否则,各种不同的梦,在半睡半醒中完成嫁接,结出未曾品尝过的野果。
否则……出于对这个温度的敬畏,我的记忆不愿再一一赘述。
“一个人在外,注意饮食,注意感知冷暖,增减衣物。”为了监控和预防,我把这句叮嘱,刻在感冒因子来袭的每一条必经之路上。
听妈妈的话,和我的体温有着同一刻度的词语和句子。在他乡,这是我唯一随身携带的行囊,在偶感风寒的时候,我就用它生火取暖,驱赶牙关之下瑟瑟的颤抖。
那时,眼泪的滚烫超过体温,它顺着脸颊滑落的斑斑痕迹,记录着我自以为是的错误。
85℃
大学北路拐角处的一间面包店。八十五度C,与爱情相关。
半年多,我无意于计算消费记录,面包的名称,是我们未曾公开的恋爱语录,记在时光手册上。
给你讲过做面包的面粉,讲过强筋、中筋、弱筋的蛋白结构和功用。
讲过一颗麦子的一生,怎样破胸、露白、出苗;怎样拔节、灌浆,低头沉默……
深秋的风,是一把锋利的刀,透过面包店的落地窗,我看到白露为霜,地表的温度被收割殆尽。
你左手握着一杯85℃的豆浆,右手紧紧地握着我的左手,说要把85℃的温热传给我,让我不再畏惧任何程度的收割。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百六十五个夜,我独坐在店里的木椅上,注视着窗外和店里的人群,直到打烊,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似你,却又都不是你。
85℃的爱情,注定不圆满,离理想的温度,还差几把柴薪。
99℃
剩下的一度,留给纬度,留给海拔,留给不同地方的锅碗瓢盆,去解释沸点的差异。
一块冰,在生活的容器里融化、沸腾。从固态到液态,是涅槃,是诸法空相,度一切苦厄。
99℃,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为了表达自己对人间草木的爱,我降低了血液的沸点。 一米阳光,就足以使它沸腾。
九九归一后,是我不愿面对的清零和重启。行走在生命的数轴上,我不迷信,但渴望并留恋这个宁静的落脚点。
99℃的人生,介于温热和滚烫之间。
我的热情,也只有99℃,可以泡茶,可以煎药,可以浓缩一些病痛和苦涩。
也许正是这一度之差,使我的体内燃起一堆不熄的火,或加热,或保温,它让我的胸膛始终保持温热。
剩下的一度,也留给自己,它会告诉身后的时光,为何我的性格会不温不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