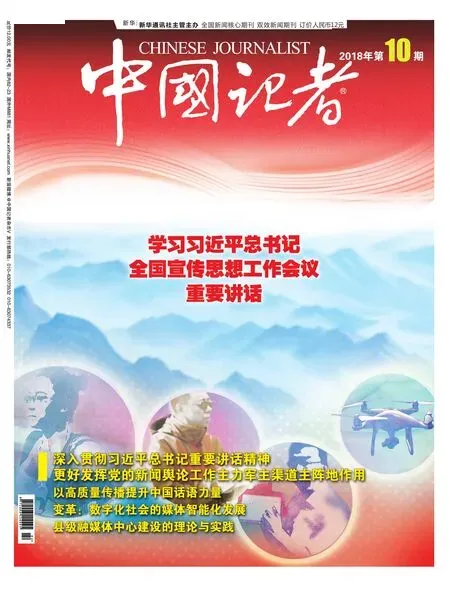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新闻报道的操作与限制
——以徐某某涉枪案引发的系列媒体名誉侵权案为例
□ 文/谭 明
内容提要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此前以刑事案件侦破为关键节点的刑事案件报道势必会受到影响。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报道中,新闻媒体究竟该如何处理刑事案件新闻报道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呢?本文以发生在H省C市的系列名誉侵权案为例,思考传统刑事案件新闻报道和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新闻报道的限制,探索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报道的操作。
传统刑事案件报道模式大部分以侦查机关侦破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关键节点,通过犯罪嫌疑人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描写,进行报道展开。但侦查阶段毕竟只是犯罪的查证阶段,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处于未知状态。
以H省C市2014年发生的一起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案(以下简称“徐某某涉枪案”)为例,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因涉嫌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3家新闻媒体从各种渠道获知此新闻线索后,进行报道。但是,该案后因证据不足,当地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并予以国家赔偿。徐某某认为,13家新闻媒体的报道行为,侵犯了其名誉权。从2015年到2018年三年间,他先后将13家媒体告上法庭。最终,有3家媒体一审败诉,被判赔偿损失、公开赔礼道歉,有10家媒体与徐某某达成调解协议:通过后续公开报道,澄清“不起诉”事实并赔偿一定损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这势必也会对新闻媒体的刑事案件报道产生影响。在此,本文以徐某某诉13媒体系列名誉侵权案(以下简称“徐某某案”)为例,思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报道的限制,探索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新闻报道的操作等问题。
一、刑事案件诉讼报道应遵循全面报道原则,适当将报道重心后移
笔者认为,刑事案件从发生到侦查、起诉、审判,每个阶段都属于“新近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发生阶段回答“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事”的问题;侦查、起诉阶段是回答“谁可能在某时某地做了某事”,审判阶段回答“某时某地的某事是谁做的。”
以徐某某涉枪案为例,13家新闻媒体所做的实际上是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新闻报道。其以2014年4月侦查机关作出的刑事拘留结论为报道切入点展开报道,通过建立犯罪嫌疑人与案件事实的直接联系,回答“某人在某时某地做了某事”。
但侦查阶段不过是查证案件的探索求证阶段。其所查证的结果,还需要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法院审判等后续阶段的进一步论证,犯罪嫌疑人是否是真正的“作案人”“罪犯”充满了变数。放到徐某某涉枪案中,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失,2014年11月,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2015年1月,检察机关对其又作出国家赔偿的决定。也就是说,新闻媒体之前基于侦查机关的素材,在新闻报道中建立的犯罪嫌疑人与发生案件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实质否定。
笔者认为,刑事案件新闻报道应首先对案件发展阶段进行区分,应该遵守刑事诉讼程序,面对持续发生变化的诉讼状态,建立“全面报道”思维,对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全过程,进行动态关注。案件发生阶段的报道应控制在“某地某时发生了某事”的范畴以内,限制“人与事实”之间的直接联系。报道重心也应当适度后移。审判之前的报道,应当侧重于“事”的呈现,减少“人”,回答重心是“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事”,客观报道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采取的各种强制措施即可。报道的重心,笔者倾向于是审判阶段。通过审判现场控、辩唇枪舌剑,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客观、全面、公平的还原案件真相,再在此基础上报道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判决,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融合。这既降低了新闻媒体的侵权风险,也真正通过新闻报道实现“看得见”的公平与正义。
反观徐某某案,实际上就是片面报道的结果。徐某某涉枪案,除了在侦查阶段,徐某某被刑事拘留后,诸媒体进行了报道外,之后的报道戛然而止,即便是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不起诉”予以国家赔偿决定后,在名誉侵权案结案前,也未有一家新闻媒体对其进行过后续报道。试想,如果诸涉案媒体,在案情报道时力求全面客观,对刑事诉讼过程持续关注,事后徐某某被不起诉后,主动公开澄清,而不是被动澄清,是否有名誉侵权之诉还难得一说;即便有,诸媒体在庭审时,是否又多了一条抗辩理由。
二、恪守“无罪推定”底线,慎用情绪化语言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条便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徐某某涉枪案,诸新闻媒体报道中,虽然对徐某某一直以“犯罪嫌疑人”相称,但却又以肯定的句式描述“高中毕业的保安会武术,还会造枪”“男子退伍后网上学造枪,家中制手枪弹被抓”“保卫科员工家中堪称地下兵工厂”“经过审讯,徐某……对非法制造贩卖枪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等。部分媒体甚至详细地报道了其家庭详细住址,部分媒体还公布了其肖像。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此种报道方式足以引起普通民众的“评价错觉”,潜意识形成“他是作案人,是罪犯”结论,这种在案件的查证探索阶段,就引入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评价、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压力的做法,实质上让犯罪嫌疑人过早贴上“罪犯”的标签,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
故徐某某案一审法院认定,在未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前,新闻媒体就以前述用语进行报道,其内容足以让普通民众产生对徐某某行为构成犯罪行为的认识,足以影响徐某某获得的社会评价,新闻媒体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
以此为戒,新闻媒体在刑事案件的报道中,尤其是审判结束前的刑事案件新闻报道,应当恪守“无罪推定”的底线,在未经法院最终确认前,禁止实质的定罪式和定性式的建立被报道人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直接联系。除了对公共性人物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外,应尽可能的采用实质性的匿名报道,除非案件侦破的需要,不公开姓名、不公开家庭住址、不公开具体工作单位等。
在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新闻报道中,尽量不掺带主观意识,不做“定性”式的讨论。尽可能的以中立者的视角去关注,客观准确地反映事实发生发展的过程,不偏不倚的报道新闻,避免“媒体审判”“舆论审判”。尽量不要刻意塑造侦查人员“高大全”、犯罪分子“假丑恶”的脸谱化形象,给读者容留更多的独立思考空间。语言表达上,慎用“百般抵赖”“丧心病狂”“狗急跳墙”“窜入某地作案”等情绪化、倾向性、感情色彩浓厚的语言;也不要为了使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进行不当的渲染等。像徐某某涉枪案中的“‘枪王’落网现场直击”、“会功夫的犯罪嫌疑人险些脱逃”等。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法言法语。刑事案件新闻报道总的来说是法律领域专业报道,法言法语作为法律领域的专业用语,拥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形成是法律领域历史发展和经验积累的结果,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法律职业者执行法律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文字。法言法语在刑事案件报道中的应用,更能实现案件还原的表述准确。
此外,部分新闻媒体在刑事案件新闻报道中,为增添新闻的生动性、故事性,会在新闻报道中透露些许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犯罪史、疾病史、个人癖好、家庭关系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甚至以此“补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笔者认为,虽然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新闻媒体应该从新闻伦理的角度进行考量,结合案情、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必要性决定是否报 道。
三、“有罪”供述应当慎用,不得使用自行采访获得的“有罪”素材
在徐某某案中,被诉新闻媒体都提到,报道的内容均来源于侦查机关提供的徐某某的供述。
但是,从刑事证据规则上来说,侦查机关所取得的证据,并不能即刻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些证据都必须经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合法性、关联性检验,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否则要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徐某某之所以被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就是证据瑕疵。根据H省人民检察院2018年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15978件次;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不批捕25880人、不起诉10873人。”在全国,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18年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捕62.5万人、不起诉12.1万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2864人、不起诉975人。”由此可见,在侦查阶段的新闻报道中,任意使用侦查机关提供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风险是存在的。
而且,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谁能保证在彰显政绩、自我宣传、自我保护等利益驱使下,侦查机关在向新闻媒体公开时,对这些供述没有进行“利益筛选”,只公开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甚至还未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证据资料,故意隐瞒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资料。由于调查权的限制,对于前述可能,新闻媒体根本无从甄别,直接使用并以此建立犯罪嫌疑人与案件事实的直接联系,无疑会增加侵权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也明确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事实的公开的职权行为进行报道……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经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可见,公安机关提供的素材,并不是新闻媒体的“保护伞”。
至于新闻媒体通过外围采访,获得的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其取得途径、取得方法、取得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能成为证据提供都难得一说,更别提是否经过质证。绝对不能以此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素材,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事实的直接联系。
总之,笔者认为,刑事案件新闻报道的实践操作中,在有罪素材的使用上,任何新闻媒体都必须要恪守底线,即:如无法律特别规定,任何在庭审期间以外的陈述(即传闻证据),都不得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采用。
四、对刑事案件新闻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
随着新媒体发展,新闻媒体作为信息唯一发布平台的地位确实受到了动摇。回归刑事案件本身,侦查机关也独立于新闻媒体,通过自身信息平台,建立了信息发布平台。在诸多社会关注较强、舆论热点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介入的同时,其自身信息发布平台即已将案件发生的“事”向社会公众通报。
于媒体而言,刑事案件事实报道和刑事案件诉讼报道,更多的具有“事”的描述性的特质,或多或少带有“新闻猎奇”的色彩。在当下媒体竞争环境下,专业新闻媒体对案件“事”的报道的必要性,就值得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新闻媒体是否可以考虑角色转换,从传统的片面“宣传”“通报”“猎奇”向“普法”“预防”角色转变。报道的侧重点更倾向于诉讼终了后的思考性报道。此类报道,介入时间在定性、定罪结束后,各种证据都已得到甄别,呈现给新闻媒体的素材更合法、更全面。于被报道人的权利而言,报道错误的几率要降低很多。留给新闻媒体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机会更多,更有利于法律知识的普及、犯罪的警示与预防、公民的自我保护等。
而这种基于刑事案件的思考性报道,必然对案件的选择突出重点和特点。笔者认为,这也符合刑事案件全面报道的要求。毕竟全面报道会牵扯到记者更多的精力,如果不进行必要筛选,对刑事案件的全过程跟踪,也势必影响到媒体资源的合理运用。相比而言,“过频”“过碎”的一般性犯罪新闻报道,不仅营造了不好的社会治安氛围,而且还起不到良好的社会引导效果。
所以,笔者倾向于在刑事案件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应当在舆论监督的前提下,适当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摒弃“有案就报”的思想,对选取报道的刑事案件,进行必要的甄别,“轻罪案件”“常见案件”等适当的舍弃,舆论关注度高、代表性强、教育意义与警示意义突出的案件应当成为首选,更侧重于思考性报道,而非猎奇型报道,与非专业传播媒介差异化竞争,这既是媒体责任的要求,也是当下媒体竞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