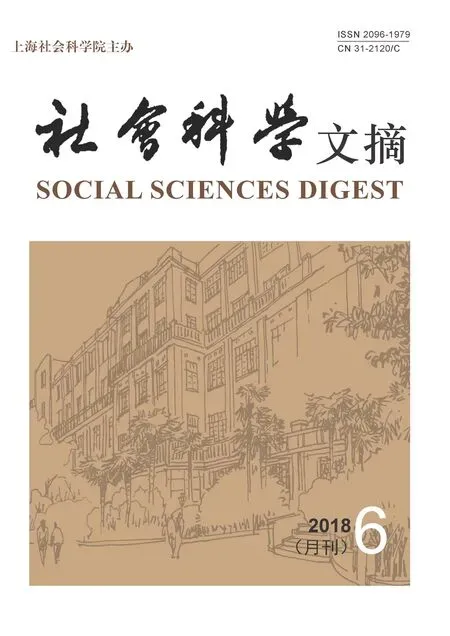中国经济实践何以产生重要的经济学贡献?
文/李稻葵 李雨纱 张驰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根据这一目标,我们还需努力保持33年的可持续的增长。如果得以实现,中国连续70年的平稳的增长将成为人类经济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否能够催生中国的经济学贡献?这是摆在当代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课题。一个似乎被大家认可的回答是肯定的。比如说,很多学者反复强调两个理由:一是中国越来越重要,二是很多中国现象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由此得出中国一定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我们不妨把目光放长远,试图回答一个更宏观的问题,那就是伟大的经济实践是否一定能够产生流传久远的经济学思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选取过去300年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经济事件,如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崛起、美国崛起、日本现代化等,结合这些实践所处时代及其之后一段时间的重要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梳理,尝试总结一些基本规律。换言之,本文试图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两个学问都非常博大精深,本文的梳理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希望从整体上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思想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第二,殖民扩张;第三,贸易政策调整与资本输出,1840年前后,英国开始由贸易保护政策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第四,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第五,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实践的确催生出了一批流芳千古的经济学思想家。亚当·斯密是其中最声名显赫的一位。但斯密的经济学远比“看不见的手”复杂,比如他认为垄断殖民地贸易可以获利,但不利于完成资本快速周转。再如他提出高关税限制了分工与市场拓展,认为除了国防的和国内被征税的行业,其他行业的高关税应该被逐步取消。
大卫·李嘉图的风格与斯密不同。他坚持劳动价值论;他提出级差地租理论,抨击地主;他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同时,李嘉图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自我均衡,这构成了他与同时代的马尔萨斯最大的不同。
卡尔·马克思也是那个时代产生的思想巨人,不过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的思考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是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制度形态上;第二,他认为英国模式存在本质性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社会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第三,他认为人的行为与所处的阶级有关,因此没有绝对的、抽象的理性。他完善劳动价值论、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等都基于上述三条经济思想。
不同学者观察经济实践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业革命的积极影响,倡导自由经济。大卫·李嘉图注意到了工人的悲惨,但将其归因于地主阶级的剥削。斯密和李嘉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乐观主义者,而马克思主要思考的是经济危机与工人悲惨的深层次原因。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思想家,而这些经济思想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英国后续的经济实践,包括战后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
德国的崛起与德国经济思想
德国经济在1871年完成国家统一后快速发展时期的特点总结如下:第一,快速工业化;第二,逐步形成统一市场;第三,政府干预色彩浓厚,在贸易政策方面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扶持垄断企业;第四,社会政策为国民提供保障。
德国的经济思想中最著名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其中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反对古典经济学思想,认为其只适用于英国;他认为落后国家不应该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也不应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同时,他强调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国家的重要性。
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冯·施莫勒也很有影响力。他认为研究经济问题用抽象演绎方法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强调用历史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和考察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曾说“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新时代就要到来,但光荣属于整个历史的统计的材料,而不属于对古老的抽象教条的进一步蒸馏,因为这些教条已经蒸馏过一百次了”。
二战后德国又有一个重要人物出现——路德维希·艾哈德。艾哈德是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思想,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要与国家的适度干预相结合,这一主张到今天还在指导实践,艾哈德本人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
不难看出,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与德国当年的经济实践之间也有着紧密关联。作为后发国家,德国经济的政府干预色彩浓厚。历史学派在理论上与研究方法上都不同于古典学派,他们背书政府干预,反对教条,倡导从实践出发进行经济研究。然而,这些观点没有成为流传久远的经济学思想。即便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为二战后德国的再次崛起奠定基础,如今也很少被德国经济学家提及。
此外,意大利也值得关注。意大利1870年统一后发展迅速,这与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不无关系,一方面他取消了房产税、遗产税,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他推行国家合作主义和农业集体化。意大利的帕累托是我们熟悉的经济学家,他在政策主张层面上其实是个社会主义者。
美国内战后到二战前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思想
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1894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1913年其人均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一时期,封闭统一大市场是美国经济最主要的特点。美国国债市场发达、银行数量众多,金融政策强力支持制造业发展。
这一时期,有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值得提及。第一位是约翰·罗杰斯·康芒斯。他是陈岱孙先生的论文导师,是NBER的创始人之一。康芒斯认为法治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利益和谐理论等,但现在已很少被青年学生知晓。
第二位是芝加哥大学的托尔斯坦·凡勃伦,著有《有闲阶级论》。他反对理性人假设,认为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等非理性因素都影响人类的消费;他强调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强调经济学分析要关注制度的变革而不是经济移向静态均衡的方式。然而,今天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对他的观点知之甚少。
第三位值得提及的学者是约翰·贝茨·克拉克。他是美国经济学会(AEA)的创办人之一与第三任会长。他提出了边际生产率学说,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的报酬。
总体而言,内战后至二战前的美国经济发展与英国、欧洲大陆相比特点明显。美国反对自由贸易,但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集体“失声”,没有人对这些独特的经济政策此进行解释或辩护。今天我们熟悉的美国学者,如哈耶克、科斯、熊彼得等都来自欧洲,其他有影响力的学者也大都是传承了源自欧洲的思想。比如,弗里德曼宣传哈耶克的自由经济思想。萨缪尔森师从阿尔文·汉森,宣传凯恩斯的思想。概括地讲,从内战到二战的时期,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美国本土没有产生基于其当时经济实践的伟大经济思想。
日本现代化经济实践与思想
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实践也同样令人瞩目。明治维新初始,日本货币体系混乱,财政赤字剧增,1876年后恶性通货膨胀。为此,日本政府削减财政支出、改革税收、出售政府企业、建立日本银行。随着日本实现货币发行的垄断和发行货币的自由流通,日本开始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通货膨胀也得到遏制。
政府与财团相勾结是二战前日本经济的一大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进行了全面改革,解散了在日本对外扩张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财阀,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在经济思想上,日本早期以介绍西方思想为主,如斯密《国富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从19世纪后期开始,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国家主义在日本成为思想主流。二战后,美国经济学逐渐建立起在日本的主导地位。近年来,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如提出“雁阵理论”的赤松要、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货币主义清泷信宏和宏观经济学林文夫等,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与思想都深受美国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经济改革是在学习西方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现代银行和财政体制的建立,基本仿效了西方国家的制度。日本早期经济学思想也以介绍西方经济学思想为主,随后国家主义建立起在日本的主流地位。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学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没有自发地对日本经济实践进行总结,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在汇率等问题上没有自己的理论解释与支撑,也就没有了话语权。
奥地利学派以及“维也纳现象”
奥地利学派诞生并发展于哈布斯堡王朝末期。进入19世纪后,随着哈布斯堡王朝在拿破仑战争、意大利独立战争和普奥战争中的一系列失败,以及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经济政治实力迅速增加,奥地利在欧洲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与经济实践上的“凋敝”相反,彼时的维也纳音乐、绘画、哲学百花齐放,自由主义思想盛行,是欧洲的思想和艺术中心。
然而,即使奥地利艺术与思想发展如此迅猛,却依然得不到德国主流学界的认可。以经济学为例,德国历史学派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影响,认为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庸俗的,对其抽象演绎的方法也不以为然。
奥地利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包括门格尔及其学生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等人。他们应用边际分析工具,主张需求导向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由个人的主观观点决定而非成本决定;他们坚持个人主义,认为理论应当从个人行为与个人理性出发;他们推崇抽象演绎而非历史归纳的研究方法,进而倡导自由市场。米塞斯和哈耶克则是奥地利学派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倡导自由主义,哈耶克认为只有经由自由市场发展起来的自然秩序,制度才会完好运转,其观点对战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文化、艺术、思想丰富多彩。奥地利学派形成并发展于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置身于于世界工业化大浪潮之中,面对着迅速崛起的普鲁士和后来德意志帝国的威胁,以自由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为基石,形成了独特的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这样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的互动关系有其历史特殊性,我们将之称为“维也纳现象”。
分析与总结
通过梳理上述各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大事件,我们可以归纳如下几个基本思考。
第一,重要的经济思想产生于重要的经济实践,但伟大的经济实践却不一定产生相应的经济思想。如果没有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实践,不可能产生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但是,尽管德国的经济实践很成功,如今德国历史学派也很少被提及,意大利更是如此;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其经济思想领域的成果却乏善可陈;同理,美国在二战以前也没有产生与其当时经济实践影响力相匹配的经济思想,其通过贸易保护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至今无人总结,而面对“大萧条”也没有人出来开药方,反而求助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第二,一个伟大的经济实践最终产生出伟大经济学贡献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不仅经济本身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且其经济实践应当致力于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造福人类。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以及军国主义日本走向侵略道路,这就丧失了产生广为流传的经济思想的道德基础。与之类似,英国的殖民地扩张政策导致了印度等前殖民地在独立以后,原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对宗主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在独立后纷纷被计划经济思想所吸引。第二,政治上的自主独立必不可少。二战后的日本、西德经济发展的确令人瞩目,但日本、西德政治上均未能实现完全的独立,日本的战后改造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西德战后长期主权不完备。这种环境下很难提出独立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反观中国,我们政治上完全独立,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国情办,这是不争的事实。第三,需要有一定的文明沉淀。日本擅长学习,但缺乏自身精神文明的沉淀,很难有思想领域的原创动力。同理,美国作为一个包括独立前历程仅有4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传承的主要是欧洲文明,其自身精神文明的沉淀时间相对短暂。欧洲与中国的文明都是长期历史沉淀的产物。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和两千年儒家思想传统,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非常的不同。
第三,回到现实问题——中国的经济的伟大实践何以在经济学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有两个有利的基本条件。第一,中国经济有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如果中国未来32年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发展,到2050年中国人均发展水平能够进入全球前列,届时来自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学的贡献将具有极大的说服力。第二,中国的发展正在惠及其他国家。当前,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带动一批国家共同发展,推动第三世界对中国的认同。如此,中国的经济思想将会有巨大的传播力。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践正在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受益。中国基本具备了以上两大有利条件,但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最终产生重大的经济学贡献,还必须具备第三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有高度的理论创新的自觉性、需要把握学科发展的规律、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虽然我们不一定认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但彼时的奥地利学术环境宽松,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值得学习借鉴。